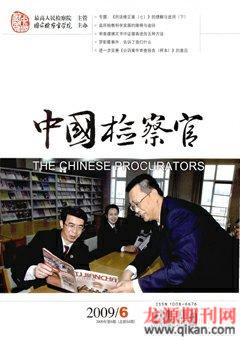逃避檢查強行推人下車致人死亡之行為定性
楊俊超
基本案情
被告人孫某,男,28歲,2005年年初購置一輛二手貨車從事個體運輸。孫某沒有辦理貨車駕駛證,只是套用他人的證件辦了一個假證,隨后就一直持此假證從事短途運輸。2005年10月份的一天,孫某在送完貨返回家的途中,被縣交警部門的巡查車輛截住。進行檢查過程中,孫某自知駕駛證是假的,害怕被交警查出后進行嚴厲處罰,想伺機開車逃離躲避檢查。巡查交警張某見孫某遲遲不下車,就踏上孫某貨車駕駛位置外的上車板,手抓車門向孫某索要相關證件,孫某假意應付,故作翻找證件拖延時間,隨后乘張某不注意,猛力將張某從車上推下,張某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從車上摔下,倒在孫某的車下。孫某在此種情況下,仍快速倒車躲開前面阻擋的交警巡查車后,加速開車向前逃離,孫某倒車和向前逃逸時所駕車輛兩度從張某身上軋過,造成張某當即死亡。后孫某被抓捕歸案。
分歧意見
第一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孫某應構成交通肇事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孫某應構成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孫某應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
第四種觀點認為:被告人孫某應構成故意殺人罪。
評析意見
筆者同意第四種意見。
首先,孫某的行為不應構成交通肇事罪和過失致人死亡罪。從刑法罪狀表述來看,交通肇事罪是指從事交通運輸和非交通運輸的人員,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而過失致人死亡罪是指由于過失而致人死亡的行為。兩罪的共同之處均為過失型犯罪,即行為人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危害結果。
本案中被告人孫某的犯罪行為雖然是發生在交通運輸過程中,并且也造成了致人死亡的重大后果,但分析孫某當時的犯罪心態和犯罪行為,我們認為,孫某的犯罪行為不應定性為過失犯罪。過失犯罪分為疏忽大意的過失和過于自信的過失兩種。第一,孫某的行為不構成疏忽大意的過失,疏忽大意的過失要求行為人應當預見到危害結果但因為疏忽大意卻沒有預見到。本案中,孫某面對踏上上車板向其索要證件的交警張某,車不熄火,人不下車,故意拖延時間假做翻找證件,期間有一定的犯罪時間準備。從車位較高的大貨車大力推下張某,張某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遭到猛力推送從較高位置掉下,可能會摔倒在車下,此時貨車倒車或行進勢必會給其造成傷亡的結果。這點孫某有充足的時間可以考慮到,也應該預料和估計到。整個過程孫某從預謀到實施有一定的時間間隔,其不會因為疏忽大意而導致沒有預見到此危害結果,所以說孫某根本不可能構成疏忽大意的過失。第二,孫某的行為也不構成過于自信的過失,過于自信的過失要求行為人已經預見到危害結果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危害結果。本案中,作為從事交通運輸的駕駛人員孫某來說,車輛作業的高度危險性他應該深知,其從事多半年的道路運輸都是本縣內的短途運輸,而且自己也沒有通過正規考試途徑取得駕駛證,駕駛技能和駕駛經驗都相對缺乏,再加上剛才所述猛力從車上推下張某并最終導致張某摔入車輪之下的現實情況,其隨后實施的快速倒車和加速逃離復雜作業帶來的危險性,基于這幾方面的不利因素,孫某還敢于實施其冒險行為,很大程度上是抱著一種僥幸心理,而并非輕信能夠避免的自信心理。綜合當時各種情況,孫某根本就不具備自信避免危害結果發生的條件和基礎。也就是說,孫某當時看到張某已經倒在車輪之下并沒有脫離危險位置,在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會給張某造成傷亡的結果的情況下,為了躲避檢查、逃避處罰,抱著一種非常僥幸的心理,仍然實施了其犯罪行為。所以說,被告人孫某的行為不構成過于自信的過失。
鑒于以上的分析,孫某的行為不夠成過失犯罪,所以我們認為,被告人孫某的行為不應構成過失型犯罪中的交通肇事罪和過失致人死亡罪。
其次,孫某的行為不應構成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法》第114條和第115條規定了“以其他危險方法”實施的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是指行為人使用防火、決水、爆炸、投毒以外的、且能造成不特定多人傷亡或公私財產重大損失的危險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此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侵犯的客體為社會公共安全,主觀方面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本案中,孫某的行為雖然造成了張某的死亡結果,但分析其犯罪過程和犯罪行為,犯罪對象相對特定,只是針對張某個人,因其在逃避檢查過程中,面對前方其他的巡查交警及車輛采取了倒車后加速逃跑的措施和行為,避免對這些不特定人員及車輛的傷亡和損害,最終也有效地杜絕了對這些不特定人員及車輛的傷害,事實上孫某的犯罪行為也并沒有造成對公共安全的侵害,不符合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體構成要件,所以我們認為孫某的犯罪行為不應構成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最后,孫某的行為應構成間接故意的故意殺人罪。故意或過失是一切犯罪的必備要件,而我國刑法中又將故意犯罪分為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刑法》第14條明文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和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是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的統一,其中“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是犯罪行為人的認識因素,而“希望”或“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則是犯罪行為人的意志因素。當犯罪行為人的意志因素是希望發生時,就構成直接故意;當犯罪行為人的意志因素是放任發生時,就構成間接故意。就兩種故意犯罪的認識因素而言,直接故意的行為人是認識到危害結果發生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而間接故意的行為人只是認識到危害結果發生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間接故意犯罪的認識因素不要求自己行為導致危害結果發生的必然性,只是要求犯罪行為人在實施犯罪行為時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導致危害結果的發生就足夠了。
結合本案,被告人孫某在計劃實施犯罪并付諸實施時,衍生出一系列的犯罪行為:人不下車,車不熄火,假意翻找證件迷惑張某,蓄意將毫無防備的張某從所處位置較高的上車板上猛力退下,不等張某有所反應脫離危險位置,就隨即當場在狹小的范圍內高速倒車,加速逃離。其在計劃和準備這些犯罪行為之時,對被害人張某所處環境的危險性和會導致張某傷亡的可能性必然有一個很清醒的認識。也就是說,孫某此時“明知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張某的傷亡結果”,完全符合故意犯罪的認識因素要求。事實上,本案中孫某雖然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會導致被害人張某的傷亡結果,但究其出發點和目的并不希望這個結果發生,其最終目的只是為了躲避檢查、逃避交警部門的處罰。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其實施了隨后一系列較為連貫的犯罪行為,對可能造成被害人張某傷亡結果沒有采取任何的防范和應對措施,完全是聽之任之,采取的是一種嚴重不負責的放任態度,這一點則完全符合間接故意犯罪的意志因素。本案中,孫某的犯罪心態和犯罪行為完全符合間接故意犯罪的犯罪表述,其間接故意犯罪的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相互統一,明知會發生導致張某死亡的結果而放任了這種結果的發生,最終導致了被害人張某的死亡結果。所以,我們認為對被告人孫某應當以間接故意的故意殺人罪定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