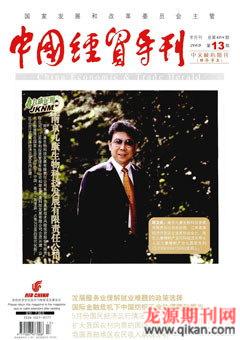從廣義視覺透視司法誠信的重構
武蘭芳 陳 燾
司法誠信,是指司法機關在司法適用過程中必須嚴格誠實地適用法律,忠于憲法和法律的司法行為準則。誠信是司法存在的道德基礎和制度規范。司法誠信代表了國家司法機關在廣大公民心目中的公信力。司法信用不足,也將使社會信用體系進一步惡化。
那么,司法誠信的內涵究竟是什么?在程序法領域是否有必要確立司法誠信原則?怎樣構筑司法誠信以維護法律的威嚴?本文通過對司法誠信內涵的深刻全面分析,進而對司法誠信的重構提出客觀可行的建議。
一、司法誠信內涵的擴展
從語詞的解析上來講,“司法誠信”包含“司法”和“誠信”兩方面內容,而前者是對后者的限定,即司法活動過程中應樹立誠信理念并堅持誠信原則。因此,對“司法”內涵的界定直接決定了“司法誠信”原則的適用范圍。
(一)狹義上,“司法誠信”在民事實體法上的內涵
一般意義上認為,誠實信用原則在民事實體法中被稱為“帝王條款”,其終極意義是因法律本身的局限性而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用以彌補法律的漏洞和限制私權的濫用。在司法領域中,誠信原則的確立實質上是在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對法官的一種授權。即承認司法活動的創造性和能動性。當然,誠信原則在司法領域的確立,最根本的出發點還是期望法官們在司法活動中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秉承對法律精神的深刻領悟,最大限度地實現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以維護法律的尊嚴。也就是說。“司法”狹義上主要是指法官行使審判權的過程,司法誠信則是法官在行使審判權過程中應遵循的基本原則。以此從實體法的角度審視法官行使審判權則存在兩種可能:第一,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法官理所當然應該嚴格“以法律為準繩”;第二,在法律無明確規定的情況下,為了確保個案實體公正,法官應基于法律原理和基本精神創造性地確定裁判依據,而這種創造性則受到誠信原則的約束,也就是堅持誠信原則自由裁量。從裁判依據角度來看,由于第一種情況下,既然已有明確的裁判依據,則法官應然地毫無商量地依法裁判。因而不涉及誠信原則的適用問題。所以,學者們在從狹義角度探討“司法誠信”往往導向于對第二種情形的研究。這一點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角度審視都是勿庸置疑的。
(二)廣義上“司法誠信”原則在程序法上的擴展
從程序法的角度來看,因程序法有其獨立的價值,在通向實體公正的道路上,程序正義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而相比實體正義,程序正義受到侵害往往具有更大的隱蔽性。
因此,從廣義的角度理解“司法”,不僅包括法官行使審判權的過程,而且應該包括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以及監獄等在內進行司法活動的全過程。因為,尤其刑事案件從偵查到執行結束,上述機關尤其是前三機關均參與其中,而且既有分工又有協作,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程序。而程序是否合法不僅直接影響到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是否受到侵害,而且決定著法律在當事人乃至社會民眾心中的權威。因此,在程序法領域,無論從理念上還是司法實踐中,在適用“司法誠信”原則時對“司法”的理解有必要做廣義解釋,而且無論法律是否有明文規定,“誠信”這一原則應當貫徹于整個程序的始末。
對“司法誠信”內涵的認識,不應局限于民事實體法領域,其確立于程序法而言具有更重要的現實意義。事實上,“司法誠信”原則在程序法領域的研究尚處于空白狀態,或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從一定層面可以看出程序法價值的錯位或嚴重缺失。因此,“司法誠信”原則向程序法方向的擴展,以及適用范圍的擴大,本質上是“司法誠信”面對司法現狀的一次應然回歸。
二、重構司法誠信的幾點思考
一部紙上的法律要對某一對象產生法律效力,必然需要經過法律司法化這一中間環節。因此重構司法誠信,首先需要樹立正確的司法誠信理念,當然也需要更進一步建立健全相關機制和制度。
(一)司法誠信理念的正確歸位
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是從法律層面上對基于公平、正義、效率、安全等價值形成的、維系社會秩序的規則的最終確認。面對違法犯罪行為,國家機關應采取制止或制裁措施對其予以否定性評價,從理論上恢復既定的社會秩序。國家對違法犯罪進行否定性評價以及制止或制裁的過程,即為廣義上的“司法”。在對涉案當事人進行“司法”的過程中,任何侵害當事人權益的行為都是違背“司法”精神的。基于這一邏輯,司法活動必須在最大的善意和合理的程序中進行。只有這樣,司法過程才是“誠信”的,司法結果才是可信的。由于“司法”活動不能白行完成,必須由司法人員予以實施,這就要求司法人員面對違法犯罪時應該本著最大善意的心態。嚴格按照法律程序履行法律賦予的職責,而不得采取任何情緒化行動,也不得采用非常手段侵犯涉案當事人的權利,更不得擅自剝奪其生命權利。因此,司法誠信的重構,要求司法人員必須樹立正確的司法誠信理念,深刻領悟其行使司法職責的深層意蘊和最終效用。
(二)建立司法人員信用動態評估制度
重構司法誠信不僅需要理念上的正確歸位,更需要建立起切實可行的評估制度。對司法人員的評估,應該注意以下幾個基本問題。第一,應該讓社會公眾至少是當事人充分參與。尤其對當事人而言,司法全過程與其利益息息相關,其體會是最深切的,他們也有權利對司法人員的司法行為發表自己的看法,在評價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歪曲事實等不正常狀況應屬個例。第二,對司法人員信用評價應該是動態的。通過動態評價建立起長效機制,并對一定時期內的評價情況進行分析匯總,可以比較客觀地反映該司法人員的信用狀況。第三,應建立起完整科學的信用評價體系。該評價制度應由一系列必要內容構成,對這些內容進行分項設計,并分配不同的權重,最后進行加權分析,分析結果應是比較客觀公正的。第四,建立信用公示制度。信用公示,不僅是對評估過程的監督,更重要的是對司法人員司法行為的監督。通過建立司法人員信用動態評估制度,能夠督促司法人員形成內心警示,并自覺地遵守司法誠信原則依法履行職責。
(三)健全司琺監督機制
與司法人員信用動態評估制度不同,司法監督機制重心在于外部監督。這是重構司法誠信的第三個層次。“躲貓貓”事件發生后。兩會代表針對司法監督紛紛諫言獻策,諸如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副檢察長周光權在兩會上提出“由檢察機關參與日常對看守所的巡視”、“檢察機關可獨立與犯罪嫌疑人進行談話”以及“看守所由第三方看管”等監管舉措,還有監控設備損壞等一些細節問題的落實等等,這些對防范司法違法犯罪行為措施的積極探討,反映了健全司法監督機制的拓展思維。另外,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不僅要肩負起實體法落實情況的監督職能。也要積極履行監督司法程序是否合法的職責,這一職責的行使,要求我們應從小處著眼進一步對相關機制的確立進行探索,為檢察機關行使監督職權提供法律依據。
綜上所述,司法誠信已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重構司法誠信,首先應當將司法誠信原則引入程序法領域。并通過樹立正確的理念、建立司法人員信用動態評估制度以及健全司法監督機制等措施,使司法活動在法律軌道上正當進行,以避免因司法權的行使而侵害社會民眾的基本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