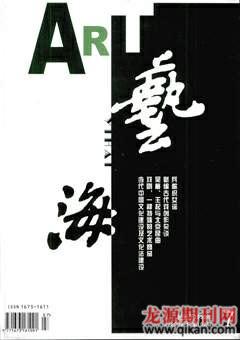笑在燈火闌珊處
朱依依
《三笑》是陳其鋼先生于1995至1996年間為華夏室內樂團創作的一首民樂四重奏作品。《三笑》是作者少有的帶有幽默色彩的作品,它向聽者展示了作者憂郁、深沉內心的另一面。從陳其鋼早期作品《回憶》、《易》、《源》等作品中流露出的一種法國音樂特性中不難發現陳其鋼似乎一直著重于對音色的追求。但是,《三笑》中漸漸顯示出的五聲旋律似乎預示著作曲家中國意識的“回歸”。
對應音樂之標題,全曲大致分為三個部分,即一部分代表“一笑”。每一部分均由笛子主題引入,隨之進入四個樂器的重奏。三弦聲部則承擔著“笑”這一主要任務——多次以同一節奏彈奏下行音高模仿笑聲。琵琶和箏聲部零星散落在笛子聲部之間作為笑聲的陪襯。隨著主題的發展,每一部分的和聲織體愈來愈密集,每一件樂器的旋律也隨之加長、愈發清晰。第三部分是全曲的高潮所在,在多段類似于意識流的零碎片段相互交錯之后第三部分迎來了一支完整的五聲旋律:笛子與琵琶交替演奏主旋律、三弦與箏襯托以琶音,“空山新雨后”之氣韻生動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尾聲琵琶三弦掃弦而入,劃破五聲旋律 靜謐安逸之感。笛子在同一音型上反復吹奏出一個主題,箏、琵琶、三弦聲部隨之層層漸入又逐漸消失,全曲在笛子主題的漸行漸遠中結束,同時也留給了聽者無數的遐想。
柔弱中蘊涵剛毅,不羈里富含哀愁是我初聽《三笑》之感。陳其鋼本人亦散發出一種中國文人所特有的儒雅溫婉的氣質。因此,他的音符中總是顯現出文人音樂的特性。與生俱來的中國式感性與法國音樂的浪漫在陳其鋼的音樂中渾然一體:既保持了儒釋道合一的東方神秘之感又融入了印象主義光色具象描繪的特性。“亦隱亦現、低回側轉”似乎是對于這種特性的最佳描繪,正如陳其鋼自己所說:他是一顆移植到法國多年的“中國樹”。《三笑》中笛子可以說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聲部,笛子幽怨的主題貫穿全曲,時而浮于整體音響之上明亮高亢,時而潛伏在這各個聲部之間來回穿梭、若隱若現,營造出哀婉清幽而又神秘的氛圍,宛若娓娓道來的回憶。點點滴滴的往事悄然爬上心頭之時突然一笑打斷了思緒,縱然時光逝去那一笑仍舊帶著絲絲苦澀。是進取亦或隱逸?是狂放亦或適意?是曠達亦或忍讓?這不正是作者青年時期的心境嗎,特殊的政治環境給與了他更為豐富的內心世界。走向未來的迷茫與面對紛繁復雜世界的困惑交雜,當年意氣風發與默默無聞的青年遣愁索笑。“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之感充斥在這第一笑之中。這又何嘗不是每一個正處在人生探索之路上的年輕人所特有的狂妄之感呢,人生的第一境界——探索也凝聚在了這漠然一視的笑中。
苦笑是人生經歷茫然無序、求索無門的困惑與痛苦的終極表達。經歷此番痛楚之后便是以苦作舟、以勤為徑、上下求索的執著與忍耐,我想這也是作者遠赴重洋求學之心境吧。一笑戛然而止,回憶仍在綿延。探尋之路崎嶇而又矛盾,面對截然不同的生活環境與文化氛圍之時,如何堅守自身的文化根基,這是一個遠在海外的文藝創作者必須思考的問題。在 “獨善其身”還是“兼濟天下”的十字路口,這位內心孤寂的藝術家莞爾一笑。但這人生路上第二笑與青年之第一笑確是迥然不同的。冥冥之中,這種矛盾似乎與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心里矛盾是相吻合的:徘徊于儒的入世與道的出世之間,時而左右逢源,時而如置夾縫。此時,作曲家不禁疑問何謂“中”,何謂“西”?該向誰學?前路為何還是如此迷茫?詩人的狂妄過后是文人騷客的憂慮!唯有淡然處之,漠然一笑能夠理清思緒,追求更高的精神世界。
王國維先生曾在《人間詞話》中提到人生之三境界:第一境為“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第二境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在經歷過前兩境方能入“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之第三境。《三笑》所現作者之心路歷程又何嘗不是這樣一個過程呢,樂曲中前兩段的簡約寧靜是對人生前兩鏡的輕描淡寫:第一笑是“望盡天涯路”的期待之苦,第二笑則是“消得人憔悴”的求索之痛,而真正的點睛之筆正是蘊含在第三笑之中。雜亂無章、跌宕起伏、清雅溫婉弦歌一堂,恰如色彩漸變一般流暢自然。第三部分四件樂器奏出緊張混亂之感,力度達到全曲最高峰,笛子的“回憶”主題悄然漸入,剛被激蕩的心境又被拉回到一片寂靜之中,隨之全曲最為精彩的五聲旋律由笛子與琵琶交替奏出,始終彌漫在樂曲之中的哀怨此刻銷聲匿跡,充斥著的是空靈秀麗的氣息,聽者更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這便是“燈火闌珊處”的笑,更是進入第三境的“悟”。
傳統文化的根基賦予作曲家以中華民族特有的審美心理結構,進一步滲透在其作品之中。千年以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帶給了千萬士子以前進的動力,但是這動力背后隱含的是無以言喻的苦澀和辛酸,于是文人士大夫又鐘情于老莊哲學的“知其不可為而不為”。在這兩條路中穿行必定是一個漫長而又痛苦的過程,在這痛楚之中最終凝聚了一種介乎于兩者之間的哲學理念——禪。與其說第三笑是醒悟,不如說這一笑是禪意的升華。這里的禪不是佛教的禪宗,更多的是隱含在作曲家內心的一種亞宗教情感,禪意不是宗教,但作為中華民族智慧的一種結晶,作為一種精神寄托,卻具有濃厚的宗教情感。它既執著,又超脫;既進取,又隱逸,這是深深根植在中國士大夫潛意識之中的。經歷了風風雨雨,走過了坎坷崎嶇之后,作者在驀然回首間找到了自身最準確的定位:“聚天地萬物之精華于己一身,建立一個獨具尊嚴、獨具特色的我”(陳其鋼)。兩千年前,釋迦摩尼在靈鷲山拈花一笑,從此以心傳法的禪深入人間。作曲家筆下這會心一笑直抒胸臆、無所顧忌、融狂放與適意于一爐,音樂本體背后文化、風格、技法之間的對立消解了,禪意不覺間融入了音樂。作者筆下的樂曲變成了一杯清茶,冷暖唯有飲者自知。作曲家經歷了傳統文人士大夫的心路歷程之后,安靜適意的心境上升為了“空靈”的意蘊,這種中國藝術所獨具的氣質自然而然滲入到每一個音符之中,空靈與幽默躍然紙上,一同去尋求生命的超越。這種超越在此既包含了儒家“天人同構”之意又兼具了道家“逍遙游”式的人生審美態度。升華了的禪意,是一種更具透明度的審美心態,這種藝術文化心態在《三笑》這部作品中超越了其自身的局限,顯示出更為豁達的“游心太虛”式的人生觀和宇宙觀,這一切方顯其最高的藝術價值。在作者筆下,《三笑》中的妙悟更確切地說是作者對其人生、生活、機遇的偶然性的深沉點發,作者無需再從社會人際關系中尋求自身價值,物我同一的境界在作品本題中得到了實現。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音樂系06級本科)
責任編輯: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