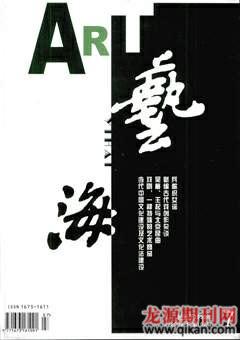從數字“三”體驗西歐音樂之和諧美
胡紅霞 謝黎華
數字“三”在西歐人們的心目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也與歐洲的藝術有著緊密聯系。早在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把音樂的和諧美與數聯系在一起。而中世紀和19世紀的浪漫主義時期的音樂藝術在旋律、節奏、體裁上凸顯了音樂與數字“三”的密切關系。宗教音樂是中世紀音樂的主要音樂形式,圣詠在中世紀音樂中占統治地位。圣詠音樂主要是歌頌上帝,表達對上帝的無限崇敬與熱愛。因為是表達對神的感情,所以這種音樂比較其他的音樂而言,顯出一種獨特的莊嚴與肅穆,并且在節奏、音程、旋律中都與數字“三”有著緊密聯系。
“拱形”旋律是歐洲中世紀音樂的基本旋律形態,旋律從一個基本音級出發,上行或下行然后再回到原來的出發音級(或與出發音相鄰的音級)形成一個拱形的形狀。

這是中世紀一個典型的第斯康特(圣詠音樂發展到12、13世紀的一種重要復調形式)旋律片段,我們對“拱形”旋律試進行剖析,第一個單位的“拱形”旋律,從小字一組的g出發上行至小字一組的b,然后又下行回到小字一組的g,如果我們把g—b—g三個音符用直線連接起來,可以得出一個三角形的框架。以同樣的方式用直線連接第二個“拱形”旋律單位的出發音級小字一組的d、最低音級c、最后的回歸音級d,第三個“拱形旋律”單位出發音級小字一組的f,最高音級g、最后的回歸音級f,得到的都是是三角形的框架,可見,以“拱形”旋律為主要旋律形態的音樂旋律的框架結構其實就是幾何圖形中的多個三角形。
從辯證法的角度來看,這種“拱形旋律”也孕育著矛盾雙方的發生、發展、統一的過程。波埃修斯對和諧下了一個在中世紀得到廣泛傳播的定義:由對立面組成的一切事物聯合和交織成某種和諧,因為和諧是多樣性的統一和不協調的協調。若我們把從基本音級上行至“拱形旋律”頂點視為矛盾的一方,而從頂點下行至原來的音級視為矛盾的另一方,那么這一過程就是矛盾的發生、發展、過程,最后音樂又回到原點,視為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一個“拱形旋律”的展開就是一對矛盾的整個發生、發展、對立、解決的一個完整過程。
由此可知,圣詠音樂就是在以幾何圖形“三角形”為主要框架結構的拱形旋律中,展現其莊嚴、肅穆的同時,更展現其“對立與統一”之和諧美。這種和諧美與圣奧古斯丁所稱的心靈的目的是統一和穩定是一致的。
寧靜、莊嚴的圣詠以級進和三度進行為主。圣詠采用“三”度的音程,這個恰到好處的音程關系,既避開了大跳,沒有形成太大的起伏,又讓音樂在寧靜中有所流動,也正是由于這個恰到好處的三度音程關系,使圣詠音樂在寧靜中有所起伏,但起伏又不顯得是一種突兀的起伏,而是在整個寧靜中的流動。用一句哲學語言來說就是:“靜中有動,動中又有靜”這樣的音樂,不僅表達了對上帝的虔誠,而且還營造了一種與世隔絕的寧靜、莊嚴與肅穆的氛圍。
19世紀浪漫主義時期的音樂凸顯了數字“三”的和諧美,這主要體現在音樂體裁上,一種風靡整個歐洲社會的音樂——舞曲。19世紀隨著宮廷生活的興起,宮廷舞會成為貴族們社交的一種重要的社交活動,而在眾多的舞曲體裁中,以三拍子為主的舞曲占據統治地位,“舞曲之王”華爾茲風行于整個歐洲社會。早期的圓舞曲,不能登大雅之堂,自16世紀后為宮廷所采用后,舞蹈風格演變成高貴典雅、端莊、彬彬有禮,直至17、18世紀風靡于歐洲宮廷,壓倒一切舞會舞蹈,被稱為“舞蹈之王”;瑪祖卡是16世紀起源于波蘭的民間舞蹈,其風格活潑、熱烈,從中速的3/4拍為主,節奏重音變化較多,18世紀瑪祖卡傳入德國,19世紀傳入法國,英國,其后便在歐洲廣泛流行;塔蘭泰拉廣泛流行于意大利南部的民間舞蹈。是一種以對舞為基礎的集體舞蹈,采用3/8拍式,6/8拍子,其特點是速度快,節奏強烈,急促,從“三”連音構成的節奏貫穿全曲。
三拍子的音樂之所以會在眾多的節拍類型的音樂中獨具魅力。首先是因為它具有流暢性。“強——弱——弱”是三拍子的節奏特點,而二拍子(四拍子)是“強——弱——強(次強)——弱”,若我們把每分鐘60拍的三拍子與二拍子或四拍子的音樂放在一起,那么在一分鐘之內,三拍子完成20次強拍,二拍子完成30次強拍,四拍子完成15次強拍,15次次強拍。若我們把每一次強拍(次強拍)看作是一次呼吸點,那么,相同的時間內,音樂呼吸點次數越多的話,它的流暢性勢必會受到一定的影響,固三拍子節奏在二拍子具有更好的流暢性。由于舞蹈是以渲泄和釋放情緒為目的,因此,流暢性強的三拍子舞曲更適合其他拍子的舞曲。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西歐音樂寫作的重要原則也是按照一個“三”部性原則,呈示、展開、結束來完成的,這與我們中國的多段聯綴的發展音樂手法截然不同。
(作者單位: 湖南師范大學 邵陽學院音樂系)
責任編輯:李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