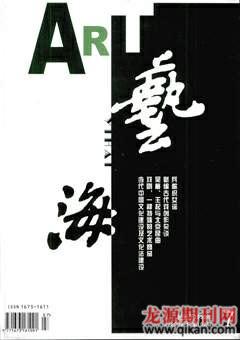困境與機遇
何 謇
中國油畫百年的發展史,其實主要是寫實油畫的發展史。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歐洲發明攝影,注定寫實油畫將陷入困境。十九世紀末,畫家們意識到攝影將逐步促使寫實油畫日益邊緣。技術與文化思潮的發展,促使裝置、行為、攝影、多媒體等紛雜的后現代藝術逐漸失去了其可供衡量的評判標準,導致幸存于中國的寫實油畫四面楚歌。
置身于裝置、行為與圖像的陷阱中,寫實油畫只是西方當代藝術格局中的一小塊。中國幾乎是與西方同時進入圖像時代,與之寫實油畫相比較,雖然寫實油畫引入中國近百年,但仍然是遠遠滯后于西方。在民國時期,攝影、電影、油畫不可能短期內象西方一樣形成一個視覺藝術的有機整體。而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中西文化藝術中斷交流三十年。建國后,毛澤東提出藝術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的社會主義寫實油畫,則天時地利的在中國長期處于優勢地位,隨之學院體系、畫家群,包括行政結構,免于受西方裝置行為與多媒體的洪水的侵蝕,而形成了當今世界最大的寫實油畫群體。在如此強大的群體的時下,中國寫實油畫早已實現了“中國化”、“本土化”理想。中國寫實油畫目前真正的現實是“立足本土”,而不是“走出國門”、“與國際接軌”。當下西方寫實油畫的土壤已極端困窘與邊緣。
攝影、裝置、行為與觀念藝術使中國寫實油畫陷入困境的同時,又戲劇性地帶來了外部環境與內在思潮的特殊機遇。
中國油畫面臨的困境之一是膠片攝影與數碼影像的發展。
1839年,法國巴黎歌劇院布景畫家達蓋爾制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臺真正的照相機。那個時代,畫家追求的是如何最接近真實地畫出眼前的景物。當達蓋爾發明攝影術后,許多畫家,特別是肖像畫家的生活無以為計。照相機的誕生轟動了世界,同時也為寫實油畫的發展埋下了禍根。19世紀末,畫家們意識到:攝影將逐步取代寫實油畫“紀錄”與“傳播”的那部分社會功能。到20世紀至21世紀,膠片攝影及數碼影像等多媒體技術已成為一門成熟的視覺藝術。20世紀70年代末,羅蘭·巴特在他談論攝影的專著中說:“攝影以其霸權鎮壓了其他類型的圖像,不再有版畫,不再有具象繪畫,只有一種以攝影為模式的具象繪畫,因受迷惑而順從攝影。”特別是21世紀以來,充斥著受眾的眼睛與耳朵的是洪水猛獸般鋪天蓋地而來的多媒體影像,寫實油畫被逼入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是扔掉苦苦練就的技術,順從觀念與攝影,還是繼續扛著寫實油畫的大旗尋求突破與發展?在攝影的逼迫下,西方視覺藝術主要發展為兩大方向,一是后印象主義,以及由此引出的立體主義、表現主義、野獸派和抽象畫。這幾派畫家與攝影照片勢不兩立,是二維的平面架上繪畫的一種固守與突破,竭力拓展繪畫自身的種種可能性。另一支是現代主義,其中最叛逆者,乃是達達主義顛覆傳統,杜桑告別繪畫的標志性“圣杯”——尿壺。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波譜藝術徹底把寫實油畫逼入了絕境。以安迪·沃霍為代表的波譜藝術快速大量無限復制的圖像,給寫實油畫以沉重的打擊,其后果,就是加速傳統繪畫的邊緣化。這一后果,又影響到藝術教學,使西方傳統繪畫課程開始沒落、解體。
困境之二,視覺藝術失去了可供參考的評判標準。
攝影與多媒體技術的發展,催化了裝置與行為以及觀念藝術的發展。隨著錄像機、攝像機、刻錄機、傻瓜照相機、個人計算機相繼誕生,圖像的制作與無限復制技術進入了藝術領域。大量攝影家、平面設計家、影像制作者被納入過去只有畫家與藝術家組成的重要展覽。于是,多元的視覺藝術產生多元的評判標準,進一步的結果是導致寫實油畫評判標準的不確定性。各類的視覺藝術成了沒有教皇的宗教,人人都是上帝!人人都不是上帝!每個人都成為自己的上帝。上帝成為尋寶游戲的裁判,誰找到屬于自己的形式資源與符號資源誰就成功。寫實油畫更是如此,找到屬于自己的形式資源與符號資源,就如偶得一個新奇玩具的孩童,成為眾伙伴們羨慕的對象。且不管這玩具的獲得是必然還是偶然,也不管這玩具是否真的好玩,玩具的質地、成色,制作得是否精美,顏色是否協調,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此前沒人有這種玩具,它新奇!于是眾孩童爭相效仿,為了“新奇”不顧其它。因為新奇所以特殊,因為特殊所以失去了可比性,因為失去了可比性所以每個孩子都可以說自己的玩具是最好的,這正是大多數孩子需要的。
中國寫實油畫陷入困境日益邊緣的同時,也面臨新的機遇。
油畫引入中國100多年后,在西方已經衰敗的寫實油畫何以能在古老的中國煥發生機?這是很多人都頗感意外的。歸納起來,我認為有三方面的原因為中國寫實油畫帶來“可持續發展”的機遇。第一,特殊的外在環境使中國寫實油畫的“可持續發展”成為必然;第二,技術與材料的拓展為中國寫實油畫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第三,觀念與思潮的介入為中國寫實油畫的突破提供了內在動力。
第一,為什么說特殊的外在環境使中國寫實油畫的“可持續發展”成為必然?
首先,在時間上,千年封建禮教壓制,儒家文化熏陶,空間上,西方霸權經濟與霸權文化的強權壓力下,中國本土民眾,在很多時候失去話語表達權。在被剝奪了種種權利之后,最后我們手中僅存的權力一定是觀看權。而中國寫實油畫,符合領導者同時也符合“沉默的大多數”的觀看習慣。“1949年以后的中國油畫發展主要經歷三個階段,即所謂17年美術發展時期、文革時期和新時期。中國油畫在經歷了三四十年代的矛盾和斗爭之后,逐步確定了寫實主義的主流地位……新中國成立以后,在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方針下,文藝的普及成為中國文藝界的主要任務,而油畫在此時所受的重視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畫種。這是因為在經歷了漫長的戰爭歲月后,中國的油畫家們就多形成了非常重視藝術的社會功能的觀念,他們都已經融人了寫實主義的主流當中,而美術的領導者們則認為油畫的寫實能力超過其他畫種,對描繪現實生活有較強的表現力,易于為大眾所接受。”(余丁《世紀末的回聲——新古典風藝術》P40-42,吉林美術出版社2000年版)由于反映革命現實的需要,中國寫實油畫得以普及。
其次,在國際環境中,1949年,中國作為社會主義社會,在蘇聯老大哥的帶領下全盤蘇化,照搬蘇聯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上的經驗和模式,油畫也一樣,中國寫實油畫也被同化。1949年秋,蘇聯美協副主席費洛格若夫訪華,向中國美術界傳授同資本主義社會“頹廢藝術”做斗爭的經驗。這種介紹為中國油畫向寫實方向發展定下了基調。中國美術界此后對印象派以后的西方現代藝術進行了徹底否定,并確定了寫實油畫一統天下的局面。并與西方現代“走向腐朽死亡的資產階級藝術”徹底劃清界線。在戰后冷戰的國際形勢下,政治上的分歧使得中國無法與西方油畫先進的國家進行接觸交流,而“把物體描繪成它在自然界中存在的那樣,和象我們眼睛所看見的那樣。”這是寫實油畫的藝術理想,也容易被大眾與領導者們接受。從油畫的欣賞者來說,中國人對于油畫普遍的審美認識,長期受到現實主義繪畫的熏陶,人們已經習慣了一種再現式的視覺模式,對藝術優秀的評判停留在像與不像、美與不美的層次上,這種審美標準還將長期存在于普通大眾的心目當中。另一方面,中國的教育制度在幾十年的寫實體系下培養出來的油畫家,幾乎都是寫實油畫家。
第二,技術與材料的拓展,為中國寫實油畫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隨著傻瓜照相機的普及,中國寫實油畫家人手一臺照相機,二十多年來中國寫實油畫,幾乎都用照片。泛濫的圖像資源使敏感的寫實油畫家看到了機會和出路,攝影技術的成熟與投影機的使用為中國寫實油畫向極端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持。照相寫實主義就完全是照相機與投影機催化出來的流派。
1980年,當羅中立的《父親》在中國美術館展出時,究竟震撼了多少觀者(以后還通過攝影攝像等多媒體傳媒手段),已經不可估測了。《父親》222×155cm的畫幅、極其逼真的寫實技法,毫無疑問借助攝影照片與投影儀是最好的最方便的途徑,這更有利于作者實現想表達的情感與思想。羅中立曾說:“技巧我沒想到,我只是想盡量的細,愈細愈好,我以前看過一位美國照相現實主義畫家的一些肖像畫,這個印象實際就決定了我這幅畫的形式,因為我感到這種形式最利于強有力地傳達我的全部感情和思想。東西方的藝術從來就是互相吸收借鑒的。形式、技巧等僅僅是傳達我的情感、思想等的語言,如果說這種語言能把自己想說的話說出來,那我就借鑒。”(載《美術》1981年第2期)
第三,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寫實油畫家觀念的轉變,使得中國寫實油畫多元發展。在這方面,石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石沖說:“架上繪畫能夠對當代藝術可以補充并使之產生活力的因素,應是其觀念上的當代性,當前衛藝術已逐漸喪失了其可供衡量的價值標準時,更是如此。我試圖在不丟開架上繪畫的知識和技能的同時,以當代性與這種現實的對抗,對抗的方式是觀念形態的設置,即在以具象方式呈現‘第二現實中,輸入裝置、行為藝術的創造過程和觀念形態,從而創造出所謂‘非自然的藝術摹本。在摹本轉換中,裝置、行為藝術的觀念性導入,絕對技術的極端發揮不僅增添了平面繪畫的視覺信息容量,也為架上繪畫注入了新的‘前衛性,復合性觀念和技術所構成的結構互補關系,為架上繪畫和現有藝術的意義傳達提供了新的挑戰和可能性。”(載《當代美術家》1992,第2期)
由于文化思潮與觀念的介入,中國寫實油畫結束了表達范圍貧乏、藝術觀念陳舊、表現手法雷同的局面,使中國油畫本土化、當代化、個性化。
攝影多媒體技術的發展與評判標準的喪失,使中國寫實油畫陷入困境,但同時,特殊的外部環境、技術材料的拓展、觀念與文化思潮的涌入,也給中國寫實油畫帶來了機遇。關于中國寫實油畫的現狀,有大量藝術批評家的專文評敘分析,在本文中我只是對中國寫實油畫的現狀從困境與機遇兩方面談談自己的淺見,更多的是期望中國寫實油畫在往后的路上披荊斬棘,繼續拓展未來的新空間。
(作者單位:湖南民族職業學院)
責任編輯: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