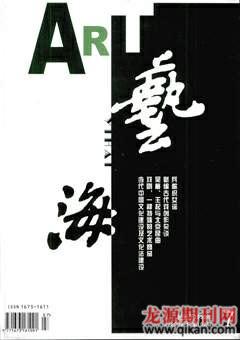意象釋義
孫慧霞
“意象”一詞是我國傳統文化中常用的一個術語。“意象”本名曰“象”,最初的涵義是指大象,后泛指各類物象。將“象”與表意的功能互相聯系起來,當始于《周易》的卦象。伏羲氏造八卦之說雖未能考證,但商代和周朝人借用卦象來占卜吉兇,則無可置疑,于是卦象也就成為表意的一種工具,這“意”自然是指天意。天意為什么要通過卦象來表述呢?《易傳》中有這樣的解釋:“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又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圣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陳鼓應、趙建偉:《周易今注今譯》P639,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這就是說,天意幽深精微,難以用普通的語言文字來表述,只有憑借虛擬的“象”,采用比擬、象征的手法,才能加以領會和傳達。這樣“象”便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立象盡意”也就成了“意象”說的導源。
先秦時期,是中國古代各種文化思想開始萌芽的階段,哲學觀、美學觀也開始了一體化的演進。其中“象”雜糅在哲學家們的哲思論著之中。《老子》則將“象”提升到形而上的哲學范疇。以“道”為世界的本原,如其所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道”自身不能等同于任何一種實物,它必然是無形無質、無可名狀的。老子認為:“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情;其情甚真,其中有信”。 (孫以楷:《老子通論》P355,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道”雖無形無質,但它能化生出天地萬物,其中定然蘊含著化育萬物的功能與信息,也就是這段話里所說的“有象”、“有物”、“有情”、“有信”,不過這些功能與信息并不以實物的形態展現,而只能通過人的意念和想象來加以把握的,所以見得“惚恍”、“窈冥”,似有若無。“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同上P432)。
莊子在意象說上頗具影響的是《外物》篇中的一段論述:“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這里并沒有出現“象”這一詞,但事實上,莊子的所謂“意”不作意思解,而是指通過“象”體悟天地之道的過程和結果,即之后宗炳所言“澄懷味象”、“澄懷觀道”。“言”乃是對“意”的描述,“意”的境界就是與道相適合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而魏晉時期劉勰的《文心雕龍·神思》的出現,才真正從審美意義上熔鑄成了“意象”這一范疇。《神思》篇中:“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則從藝術的角度來探討意象。在《體性》篇中說:“意象是在創作儲備過程中出現的內在的、具有高度凝聚性的心理存在,藝術創作的關鍵就是對其的關照與直覺。”《文心雕龍》標志著中國古典美學意象理論的肇始。
唐宋時期的“意象”觀出現兩個特點。其一,“象”與其他藝術范疇結合,逐步向意象靠攏。其二,“象”向“境”轉移,“意象”向“意境”演化。“意境”范疇是意象說發展到唐代的特殊表現。
清代葉燮《原詩》則更深一步:“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詩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事,又安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墨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于前者也。”又說:“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入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為至也。”葉燮從四個方面對意象的審美特征進行把握。首先,意象不粘連藝術形象;其次,邏輯思維不慣穿于意象中;再次,意象介于可言說與不可言說之間,帶有鮮明的個體性與主體性;第四,意象是知覺、體驗式的藝術至境,具有表情達意敘事的獨特功能。可以這么說,葉燮在意象審美特征問題上的審識,是中國古代的最高水平的總結形態,直接啟示著后人。
西方的意象說則在20世紀初才伴隨著詩歌運動的產生得到了發展。
當今人們談論的“意象”,實際上已經是把我國古代哲學概念、古代文論、美學與當代文化觀念相融合的意象了。
(作者單位:濮陽職業技術學院)
責任編輯: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