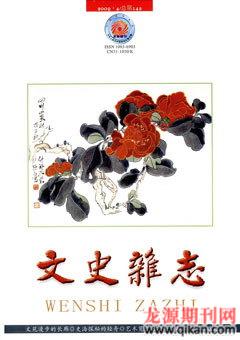梁武帝才藝略說
陳德弟
梁武帝蕭衍(464-549)在位48年(502~549年),壽齡86歲,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在位久、享高壽的帝王之一。他不僅是位皇帝,同時還是個大學者和詩人。少年至青年,他受過良好教育;執政后,依然熱衷學術文化研究。他涉獵甚廣,精通經學、史學、佛學、詩賦,對風靡魏晉的玄學、道學亦較通曉。除此之外,他在軍事、醫學、書法、音律、棋藝、騎射等領域也造詣頗深,甚至對陰陽卜筮也有研究。他一生酷愛學習,藏書豐富,筆耕不輟,著述等身,其才藝在歷代帝王中是罕有匹敵的。
梁武帝少年向儒,《金樓子·興王篇》云其“始在髫發,便愛琴書,容止進退,自然合禮”。他青年師從儒宗劉讞,為儒雅之士;而立之年,即為名彥。《梁書》本紀記其在南齊時,雅愛才俊的競陵王蕭子良開西邸學館,招納碩學,研討學術;梁武帝則以文士身份和另外七人“并游焉,號日八友”,其中包括當時著名學者沈約、謝朓、范云、任昉等人。他為帝后自稱:“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閉戶自精,開卷獨得。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墻面。雖一日萬機,早朝晏罷,聽覽之暇,三馀靡失。”此乃實話。
梁武帝對經學頗有研究。據《梁書》、《南史》本紀和《隋書·經籍志》記載,他所著經書有《周易大義》21卷,《周易講疏》35卷,《周易系辭義疏》1卷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義,《尚書大義》20卷,《毛詩發題序義》1卷,《毛詩大義》11卷,《禮記大義》10卷,《中庸講疏》1卷,《制旨革牲大義》3卷,《樂社大義》10卷,《樂論》3卷,《鐘律緯》6卷,《孝經義疏》18卷,《孔子正言》20卷,《金策》30卷和《春秋答問》等,凡200余卷。另外,梁朝建立初期,他親自參預修訂了按照儒家體系構建的國家各種禮儀制度,即所謂的“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在此期間,每有疑惑紛爭,他都能引經據典,親自裁決,說明他在禮學方面修養甚高。天監四年(505),太學成立。他數幸之,親授經義,射策生徒,凡明經者,即行獎擢。時或聞某人研經有長,他輒召入宮,親自測試。《梁書·賀琛傳》載:琛尤精《三禮》,“高祖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又《陳書·岑之敬傳》載:之敬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為高第。梁武帝“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座,敕中書舍人朱異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他還常于宮中向左右文臣及特邀碩儒,闡釋自己所悟經書要義。《陳書·張譏傳》載:“梁武帝嘗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受時風影響,他所研經學,已被玄化;在其經學論著中,包含許多玄學內容。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八“六朝清談之習”條有云:“至梁武帝始崇尚經學,儒術由之稍振,然談義之習已成,所謂經學者,亦皆以為談辯之資。”可見,梁武帝經學、玄學皆通達。(他除著《周易講疏》外,還有《老子講疏》,“三玄”已有二。)正是在梁武帝尊經重儒倡導下,已式微的經學在梁朝才得以重振。
中國古代帝王皆重歷史,梁武帝也不例外。他不僅“博通前載”,而且注意借鑒資治。在他撰寫的贊序、詔誥、詩賦、尺牘、銘、誄、箴等不同體裁的文章中,引史用典,比比皆是。《隋書·經籍志》“史部”著錄有梁武帝撰《通史》。《梁書·武帝紀下》載,武帝“又造《通史》,躬制贊序,凡六百卷。”同書《吳均傳》則載:“使(均)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顯然吳均是主修者,但梁武帝寫了部分贊、序。梁武帝對此書價值很自信,曾謂史學家蕭子顯:“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從梁武帝對史書編纂諸要求看,他的修史主張是實錄和會通。他還領修了類書《華林遍略》凡700卷。此外,《隋志》“史部”還登錄《梁武帝總集境內十八州譜》690卷,這說明他對譜牒學也感興趣。由此來看,梁武帝熟悉文獻,精通史學。
梁武帝在佛教上的精深造詣,則是史家公認的。他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佞佛皇帝,于藏佛籍、探佛學方面頗為用力,甚至多次舍身寺院。他每每身披法衣,布道說法,儼然成了菩薩皇帝。他的佛學論文主要有《立神明成佛義記》、《注解大品經序》、《寶亮法師《<涅槃義疏)序》、《敕答臣下神滅論》、《斷酒肉文》、《摩訶般若懺文》、《金剛般若懺文》、《凈業賦并序》(據《全梁文·武帝》)等。其主要佛學觀點是“三教同源”和“真神佛性”。
梁武帝喜文好作,能詩會賦,其文學才能在南朝堪稱一家。《南史·文學傳序》云:“時主(指梁武帝)儒雅,篤好文章。”著文賦詩是梁武帝生活中的一件快事。《梁書》本紀說他“天情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皆文質彬彬,超邁今古”,雖有過譽,確含實情。在《梁書》中,多處載其即興賦詩事。如《武帝紀下》載:大同十年(544)三月,他巡省故里,“因作《還舊鄉》詩。”又《張率傳》載:“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為盛。率奉詔往返數首。”《江革傳》又載:“時高祖盛于佛教,朝賢多啟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強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游。”在梁武帝身邊聚集了許多彥俊之士,他常與之詩賦往來。他常召集這些文人墨客游宴。其間,為了營造娛樂氛圍,他不僅自己作詩,同時還限時、限韻要他們成篇,如違規則罰酒共歡。《梁書·蕭介傳》載:“高祖招延后進二十余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日:‘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同書《到洽傳》載:“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宴,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匹。”又《王規傳》載:“高祖于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群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褚翔傳》又載:“高祖宴群臣樂游苑,別詔翔與王訓為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于坐立奏,高祖異焉。”《謝征傳》亦載:“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于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征二刻便就,其辭甚美。”《梁書》本紀記梁武帝“凡諸文集,又百二十卷”。據《隋志》著錄,梁武帝有《梁武帝集》26卷,《梁武帝詩賦集》20卷,《梁武帝雜文集》9卷,《梁武帝別集目錄》2卷,《歷代賦》10卷,《梁武帝凈業賦》3卷,《圍棋賦》1卷,《梁武帝制旨連珠》10卷。現存梁武帝所作詩有106首(據《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內容多為情感、述懷、寫景,另有詠物、佛理、游仙等數首。其實,梁武帝對文學最大的貢獻是,作為人君,他身體力行,并大力提倡文教,從而推動了梁朝學術文化的全面發展,使全社會普遍提高了文化素質。(參見拙作《梁武帝與梁朝的藏書事業述論》,載《天一閣文叢》第六輯)正如唐
代史學家李延壽在《南史·梁武帝紀論》中云:“及據圖篆,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
梁武帝在軍事上也有突出才能。《梁書》本紀載:“帝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干,時流名輩咸推許焉。”北魏孝文帝亦云:“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禽此人,則江東吾有也。”這是史家記錄和敵手評判,應當確鑿。從梁武帝稱帝前戰魏滅齊、稱帝后數次謀劃北伐的軍事生涯以及所寫的軍事著作看,其堪稱一位軍事家。他熟讀《孫子兵法》,每臨戰事,頻用“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韜略,多以智計創奇跡。譬如,在滅齊爭取荊州倒戈時,他憑的是“兩空函”取勝。當時,他對手下說:“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接下來的郢州攻堅戰、加湖阻擊戰、江州突襲戰,乃至京城奪取戰,他均以“心戰”與實戰相結合取勝。梁武帝在奪取江州前,對麾下說:“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弭服。陳虎牙即伯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當忷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可見他對自己的軍事才能頗為自信。在伐魏戰爭中,他水淹火攻,出奇設伏,一時曾取得重大勝利。據《隋志》著錄,他著有《梁主兵法》、《梁武帝兵書鈔》、《梁武帝兵書要鈔》各一卷。
中華醫藥,累積千載,自成體系,診治獨特。梁武帝深好之:據《周書·姚僧垣傳》載:僧垣父菩提任梁高平令,對醫藥有研究,“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梁武帝自謂:“朕常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是以每叵留情,頗識治體。”由此可知,他政務之余,常探究醫學。時稱“山中宰相”的陶弘景,醫學世家,著有多種醫藥、養生著作。梁武帝與之有舊,“及即位后,恩禮逾篤,書問不絕”…。醫學不同佛學,它需理論,更要實踐,梁武帝為己、為子、為臣皆醫過疾患。《梁書·元帝紀》載:元帝“初生患眼,高祖自下意治之。”同書《謝舉傳》載:“舉雖居端揆,未嘗肯預時務,多因疾陳解,敕輒賜假,并手敕處方,加給上藥。”又《周興嗣傳》載:“興嗣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疽方以賜之。”《隋書·經籍志》載有《梁武帝所服雜藥方》1卷。
梁武帝在書法領域亦可謂行家里手。《梁書·劉孝綽傳》載:“高祖雅好蟲篆。”梁武帝不僅能書;而且還是書法理論大家,著有《觀鐘繇書法十二意》、《草書狀》、《觀鐘繇書法》等書法論文,其書跡《異趣帖》、《數朝帖》、《眾軍帖》流傳至今。我們截取其兩篇書論,以觀其對書法的領悟。其一《答陶弘景書》曰:“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撇短則法擁腫,點撇長則法離澌,畫促則字橫,畫疏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元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并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連斷,觸勢峰郁,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暖暖,視之不足;棱棱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眾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由習耳。”其二《草書狀》日:“疾苦驚蛇之失道,遲若綠水之徘徊,緩則鴨行,急則鵲厲,抽如雉啄,點如兔擲。乍駐乍引,任意所為;或粗或細,隨態運奇,云集水散,風回電馳。及其成也,粗而有筋,似葡萄之蔓延,女蘿之繁縈,澤蛇之相絞,山熊之對爭。若舉翅而飛,欲走而還停,狀云山之有玄玉,河漢之有列星。厥體難窮,其類多容,婀娜如削弱柳,聳拔如裊長松,婆娑而飛舞鳳,宛轉而起蟠龍。縱橫如結,纏綿如繩,流離似繡,磊落如陵。(日韋)(日韋)曄曄,奕奕翩翩,或臥而似倒,或立而似顛,斜而復止,斷而還連。若白水之游群魚,叢林之掛騰猿,狀眾獸之逸原陸,飛鳥之戲晴天,象烏云之罩恒岳,紫霧之出衡山,巉巖若嶺,脈脈如泉,文不謝于波瀾,義不愧于深淵,傳志意于君子,報款曲于人間。”
《隋書·音樂志上》又載稱:梁武帝“既素善鐘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他不僅懂音律,并且創制了許多新歌。是志又載:“鼓吹,宋、齊并用漢曲,又充庭用十六曲。高祖(指梁武帝)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創新歌,以述功德……初,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白銅蹄謂馬也。白,金色也。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即位之后,更造新聲,帝自為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為三曲,以被弦管。”他崇佛之后,創作了許多頌揚佛法的正樂,如“《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為正樂,皆述佛法。”他深知,音樂可以化民,移風易俗,以助統治。
梁武帝精力過人,棋技高超,常與臣下徹夜對弈。《梁書·陳慶之傳》載:“高祖性好棋,每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他自信棋藝一流,故與臣下時或以物相賭。同書《到溉傳》載:“溉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棋,從夕達旦。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并輸焉。”他著有《圍棋品》和《棋法》各一卷。
《梁書》本紀稱:武帝“六藝備閑,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并悉稱善……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南史》本紀云其“為兒時,能蹈空而行。”《金樓子·興王篇》也說他“始在髫發……常與兒童斗技,手無所持,躡空而立,觀者擊節,咸共稱神”。成年后,盡管他已成名士,但時局和志向需要他保有騎射技藝。齊明帝建武五年(498)三月,他帶兵與北魏軍隊在鄧城遭遇,主帥崔慧景怕死而狼狽自拔。他則憑借膽識和高超騎射,帥眾拒戰,雖寡不敵眾,但最終全師而歸。《梁書·任防傳》載:“始高祖與昉遇競陵王西邸,從容謂防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謂高祖善騎也。”晚年,梁武帝對騎馬舞矛猶很眷戀,心常向往。《南史·羊侃傳》載:一日,少府新造兩刃稍成,他賜武臣羊侃戰馬一匹令試之。羊侃于馬上執稍擊刺表演后,武帝謂:“朕少時捉稍,形勢似卿。”不久,他與孫兒蕭大臨、蕭大連兄弟倆出巡,首先問道:“‘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望著他們馳騁的身影,他感慨良多,“即賜所乘馬”。
梁武帝下筆成章,立馬可待。雖然上列諸多著述或為領修,或可能由其僚佐輔助完成,但親筆為之者仍占相當數量;而他的多才多藝則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梁書》作者姚思廉在《武帝本紀》末所評論的那樣:“歷觀古昔帝王人君,恭儉莊敬,藝能博學,罕或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