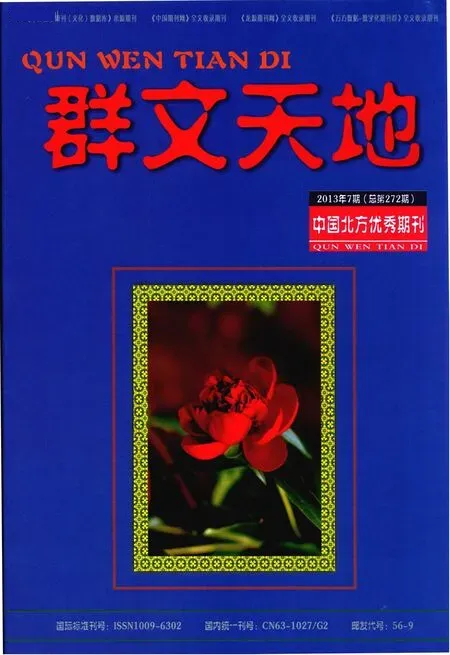悠然見南山于胸中
劉會彬
《回憶我的師兄曾福慶》,最初是在《陶瓷研究》上發表的。但我讀到它,卻是在網上,這使我改變了一些對網上文字的看法。我一向對網上的東西懷有戒心,認為既然不論什么樣的人都可以在上面發表議論,就難免泥沙混雜,那么它的嚴肅性就會打折扣。自從我讀了這篇文章,看法有了些改變,覺得有選擇有分析地去讀一點,也行。文章的作者是王錫良。王錫良是從民國時期過來的至今還健在的少數幾位瓷繪家之一。民國時期,景德鎮瓷繪藝人最有成就的,時下流行的觀點是“珠山八友”,王錫良是“八友”之一王大凡的侄子,也跟隨叔父學藝。而他又稱曾福慶為師兄,可見曾福慶也是王大凡的弟子。師兄這個稱呼,是帶有尊敬色彩的,所以以王錫良在瓷繪界的聲望和他的高超藝術成就而用尊敬的口吻來稱呼曾福慶,又可見曾福慶的藝術水平和為人,應該都為人們所認可。
2005年11月,我在北京潘家園古玩市場,見到了一件曾福慶繪的筆筒。因為通過書刊資料,事前對曾氏有所了解,所以見到這件筆筒,首先就覺得真是幸運,有喜出望外之感。
依照我見過的曾福慶繪畫的另一件實物,也是筆筒所得來的經驗,和王錫良先生的介紹,我以為在當今幾乎全民玩收藏的情況下,見到曾福慶的作品是很不容易的,所以當我見到他繪畫的筆筒時,就順理成章、合乎情理地產生了喜出望外的心情。
這個筆筒所繪的紋飾題材,是傳統繪畫中常見的“淵明采菊”。“淵明采菊”我國傳統繪畫,不論是瓷本還是紙絹本中,都是一個常見的題材。原因,當是中國傳統文人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對“出世”持贊美、歌頌的態度,表現出心向往之的姿態,甚至根本就是身體力行。而陶淵明,幾乎就是這樣生活態的代表,是具有楷模性質的人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詩句,又幾乎是陶淵明的代表,是一種生活態度的象征。所以,歷代文人,吟誦或者表現或者欣賞這兩句詩,就是在宣揚一種人生態度,就是宣示一種處世原則。這種人生態度和處世原則的背后,所蘊涵著的是文人們所要表白的自己的氣節,這種氣節是不以名利、權錢為誘,不懼怕來自達官顯貴的權威,也不屑于與官場的傾軋、世俗的粗陋相沆瀣,而是要保持自己的高風亮節。
但文人們普遍的對“出世”的贊美,并不說明他們完全的就不入世。實際上,掌握著文化,因此對世事能夠產生清晰影響的文人們,他們不僅入世,而且還向往入仕,以此來實現自己修齊治平的人生理想。只是他們在入世、入仕的同時,還期望保持自己的氣節,期望魚與熊掌二者兼得。比如陶淵明雖自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但他還是不止一次入世為官。也因此,自宋代周敦頤的《愛蓮說》以來,歷代文人們便對蓮的品行夸贊不已,以贊美蓮的方式來贊美自己。因為蓮花出自淤泥,而又不被沾染,正與自己的雖入世俗官場,而又潔身自好相對應。陶淵明本人也是如此,他并不要求自己為了表現清高,就真的將心靈的追求與物質的生活機械地統一起來,隱居到山林中去。他是“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居所就在市井俗世之中,耳朵卻可以對車馬的喧鬧之聲聽而不聞。為什么能夠達到這樣的境界?這要靠修煉,修煉到心能安靜,身居在何處也就不必計較了。就像蓮花那樣,出自于污濁的淤泥又何妨,我自依然心閑身凈。
孔孟老莊,對于中國文人來說,真是做了天大的好事。他們的學說主張,可以使文人們入有理論依據,有哲學基礎,也有怎樣行事的準則。還可以根據自己在世俗中、仕途上所處的具體位置,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選擇一個適宜于自己所做事情的類別: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出也可以左右逢源,心安理得。總之是在出與入這一對相對立的范疇中,無論怎樣選擇,文人們都可以無須擔負心理上的責任,都可以安然處之,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追求與理想,都可以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儒道兩家,真是一個大智慧者的統一的整體。它們是水火,卻能夠相容。這種水與火的相容,在中國古代文人身上得到了真實的體現。
在美術作品中表現“淵明采菊”這個題材,畫面比較多的處理成陶氏扶杖而行,所采到的菊花,由童子執著。我在潘家園市場見到的筆筒上的瓷畫,也是。同時,這類繪畫還比較多的將采菊的地點,設置在一座山中,這座山,應當是南山吧。但這樣處理,像是與陶淵明詩的愿意,有所不相符合。陶詩本意采菊的地點,未必是在山中,盡管有“悠然見南山”的句子,但應該是結廬在人境的庭院里。并且,當采菊之時所悠然見的南山,實際上不見得是見在詩人的眼里,而是見在詩人的心里;甚至南山具體的形影,在詩人的心里也未見得就見了,在他心里所見的,只是山的含義。正像詩人實際上并沒有真的見到過一個叫做“桃花源”的地方一樣。詩人只是以此來表現自己“出世”、也就是保持氣節與清高的情懷。畫家們那樣處理畫面,可能是繪畫這樣一種藝術形式在技術上的需求。
我說的這件筆筒,畫法與歷來的畫法總體上相同。畫面上的老者,也就是陶淵明手拄一根藤杖,藤杖上系著一個葫蘆。他正扭轉身軀,看著童子向畫面深處的方向走去。童子則?著一只籃子,籃子里裝著剛剛采摘來的菊花。兩個人物互相呼應,動感很強。陶淵明身體略向前傾,身體單薄。少有一點老態。而童子的身形步法則歡快輕盈。繪者曾福慶對不同年齡的人的身法動靜都表現得非常準確而又傳神。陶淵明有七八分臉轉出,而童子則完全是背影,可見曾氏在對畫面人物的擺布上,也頗動了一番心思。陶淵明上身著藍衣,下身淡黃色,在玻璃白地上,都洗染得非常精細。童子的下身所著,亦是黃色,但比陶淵明下身的黃色鮮亮些,這對表現孩童的天真活潑頗有益處,可見曾福慶在色料的使用上,也有算計,并不隨意草率。童子上身所著的,是珊瑚紅襟衣,并且用料講究,是用傳統方法制的,不是當時已經有了的從西方進口的化學法色料,所以其紅醒目而不俗艷,既進一步有助于表現孩童的天性,又使整體畫面的色彩顯得豐富而不單調,-冷暖協調。陶淵明的鞋履,用藕荷色,這是清代嘉慶年間出現的一種色料。他黑色的頭幘頗有油亮感,并不如常見的黑料那樣枯澀。眼眉和胡須間以黑白,白色的部分用純玻璃白,不摻色料。面部不用線勾,而是直接染出,對光的運用很有心得,有明暗向背之分,表明曾福慶應有學習西畫的經歷。就兩個人物的整體繪畫風格來看,我們似能夠體會到清代康乾年間“揚州八怪”之一黃慎的味道,或者曾經臨習,也未可知。兩個人物所處的位置是一面草坡,用水綠染出,點以簇狀草叢。坡邊的山石后面有樹二株,前景為松,樹干老勁,皴筆粗礪。松樹側后斜出的另一株樹,則樹干圓潤,形成對比。畫面上不見樹杪,惟有松枝倒掛下來。在瓷繪中如此表現,我們至少在元代青花中已經能夠看到。松針敷以藍綠兩種色料,以表現陰陽遠近。總之是一幅非常好的瓷畫,有相當高的藝術水準,且又繪畫精細,一絲不茍。
筆筒的另一面,題有詩句和落款。詩句為“不愿持韁為五斗,一生只是為花忙”,用含蓄的筆法,點明了畫面人物的身份,也點明了畫意。書法的筆力頗為深厚。在滑硬的瓷胎上書寫,與在紙絹上書寫相比較,尤為不易。能將筆力、筆意表現到那般程度,沒有深入的練習是不能做到的。他的字用筆柔勁,雖字體尚規整,頗有行書體勢,而又筆意勾連,流露出草書的意趣。整體上品味,亦有黃慎的味道。因此,如果我們做曾福慶曾對黃慎的寫法畫法均做過細心揣摩的估計,當無大差。
這件筆筒,體量在同類器物中數大的一類,行內有將此類筆筒叫做筆海的。足端打磨得很圓潤,屬泥鰍背一類。胎質不甚潔白,也欠致密,但淘洗精細。釉質細潔,但釉層稀薄,光亮而不滋潤,閃青。這種胎釉的特征,表明此時已經開始用機器來制坯料和釉料,反映了我國到民國時期,制瓷業已經有了現代工商業的特征:降低成本,增加產量,追求利潤。而所標榜的提高質量,不論是真的提高還是陽奉陰違,說到底都是商賈逐利的一種手段,并不是他們內心真正的追求。
曾福慶的這件瓷畫,繪制的時間,是“時在辛巳年秋月”,那是1941年。曾福慶1937年離開景德鎮外出謀生,1943年又回到景德鎮,因此這件作品當不是他在景德鎮之作。我們想,曾氏這個時期的作品,與他的其他作品,在風格上可能有所不同。
筆筒是文人用的。古時候用毛筆書寫,所以置放毛筆的筆筒,就成了書案畫案上的必備用具。而如果在文人的用具上繪以文人喜愛的題材,就順理成章了。因為此類題材表現了他們的情懷,表現了他們的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