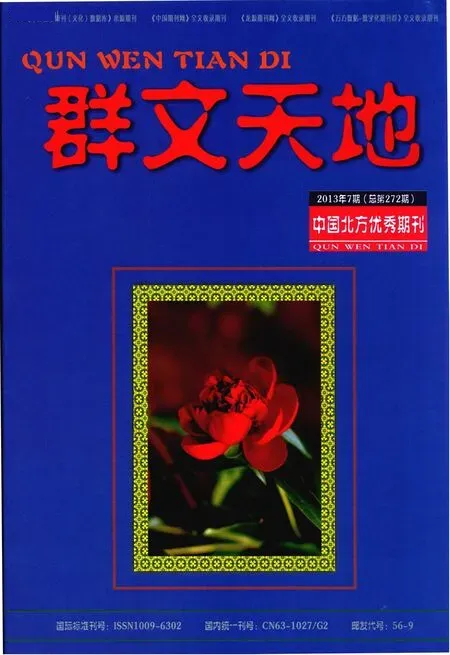痛感中的精神振奮
中國古代神話有相當一部分常常是悲劇性的或帶有悲劇色彩的,這些故事以其特有的形式和內容反映著原始時代人類面臨的主要矛盾——人與自然界的矛盾。它一方面寫出了自然界的強大和恐怖,寫出了人們遭受的苦難和悲慘的結局;另一方面又借助這種悲慘的結局寫出了人們在改造自然中的悲壯的自我犧牲精神,以及最終會戰勝自然、取得勝利的無窮力量和信心,從而顯示出人類本身的偉大和崇高。也就是說,在這些故事中體現了美學意義上的悲劇美和崇高美,從而開辟了我國悲劇主義文學的先河。
一、神話的起源
神話起源于遠古人們對自然想象的解釋。馬克思認為神話是“在人民幻想中經過不自覺的藝術方式所加工過的自然界和社會形態”。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昔者初民,見天地萬物,變異不常,其諸現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則自造眾說以解釋之:凡所解釋,今謂之神話。”
知識未開化的原始人類,不可能解釋自然,更無從談及控制自然,于是把自然神化,并借助想象企圖解說它、征服它、支配它,他們相信所有的自然現象,都像他們自己一般具有人類的一切屬性。有生命、有思想、有人格。太陽具有人一般的性情,蒼天借風雷電雨而表現他的震怒,天與地、日與月,是一對夫婦……總之,他們按照自己的樣子創造神。
二、中國古代著名神話中的悲劇美和崇高美
我國歷史悠久,古代神話是非常豐富和瑰麗多彩的,研究一下中國古代神話,就會發現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常常是悲劇性的或帶有悲劇色彩的。也就是說,在那些表現人與強大自然力相沖突、相搏斗的故事中,那些體現人類善良品德、表現人類意志愿望的英雄主人公經常是悲劇性的形象。他們或者在為創造美好世界的曲折經歷中犧牲;或者在與強大的自然力做斗爭的過程中而死亡;或者為不可抗拒的自然力所吞沒;或者遭到某些非正義的、邪惡勢力的殘害等等。
悲劇是以具有正面價值的人的不幸、毀滅為特征的審美形態;崇高是側重于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矛盾對立的審美形態,具有沖突、無限、模糊、神秘、粗礪、動蕩等特征。我國古代神話中的鯀禹治水的故事、精衛填海的故事、夸父逐日的故事以及刑天的故事等,它們無不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種悲劇美和崇高美。
鯀禹治水的故事,載于《山海經·海內經》,它在我國是流傳得比較廣、也是極有影響的一個激動人心的故事,它表現了上古人民與洪水的斗爭。這個故事的悲劇性充分體現在鯀這一英雄的自我犧牲精神上。傳說中,當時“洪水滔天”,淹沒了整個世界,鯀為了治平洪水,曾企圖“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但由于他“不待帝命”,觸犯了天帝的權威,從而身遭不幸。鯀是為了解救人類的災難,在與強大的自然力做斗爭中犧牲的。他的智慧及膽量令人欽佩,他的不幸和犧牲令人同情。這一形象,不由使人聯想起古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形象,普羅米修斯不畏強暴、敢于為人類的生存和幸福而斗爭,為了給人類從天庭盜火,他不惜觸犯宙斯的權威,以至最終被釘在高加索懸崖上。普羅米修斯的英雄行為和自我犧牲精神,受到世世代代人們的稱誦。所以馬克斯稱他為“哲學的日歷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鯀的形象和普羅米修斯的形象具有同樣感人的光輝和力量,他們交相輝映,各自成為東西方神話中的耀眼明珠。
我們知道,悲劇主人公是為了維護新生事物或為了實現崇高的理想,與比自己強大的社會惡勢力(或強大的自然力)進行斗爭的主體。悲劇主體本身的感性生命雖遭受摧殘與毀滅,但在精神上卻具有不朽的意義,充分體現著悲壯激越的情調。正如著名美學家朱光潛所說:“悲劇有不幸、有死亡,但它更本質的東西卻是崇高性、壯麗性、英雄性”。更有意義的是,鯀治水的故事在這里并沒有結束,后面還續接了大禹的故事。“鯀腹生禹”,他的兒子繼承父志,“親自操稿耜,而九雜天下之川,……沐甚雨,櫛疾風”,禹治水三十年,劈山開地,決通九江三河,疏大川三百小川三千,十年沒有見著妻子,三過家門而不入,殺九首蛇身的水怪相柳,消滅危害人類的鳥獸害蟲,憑著百折不撓的精神,終于平息了洪水。如果說鯀治水的始末是一首為人民而犧牲的悲劇英雄的贊歌的話,那么大禹治水的過程則表現出一種勁健的、激越的、心潮澎湃的陽剛之美,亦即崇高美。
精衛填海、夸父逐日的故事,都表現了同樣的內涵和性質。精衛填海的故事見于《山海經·北山經》。故事寫精衛“其狀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她本是炎帝的女兒,到東海去玩不幸溺水而死,但她卻死不甘休,變成一只美麗的小鳥,“常銜西山之木石,以湮于東海。”這則神話通過少女變鳥,誓向大海復仇的悲壯故事,反映了遠古人民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英勇不屈的堅毅精神。晉代著名田園詩人陶淵明在其《讀山海經》一詩寫道:“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表現出無限悲壯贊頌之情。夸父逐日的故事,見于《山海經·海外北經》,這是一則影響甚大的神話。英雄夸父,竟敢與日逐走。夸父在接近成功之時的死顯然是一個悲劇。故事寫他在臨死之前,“棄其杖,化為鄧林”,也就是為“逐日”的后繼者開拓一條成功之路。夸父的犧牲是一個令人同情的悲劇,但他至死不忘為后人造福,特別是他那種自我犧牲為后繼者開路的精神,卻又是極其偉大而崇高的。
在《山海經·海外西經》中,還記敘了一位“刑天”的故事。“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刑天敢于反抗天帝,雖然被天帝砍了頭,但是這位英雄卻沒有屈服,而是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揮舞著盾和斧又繼續斗爭了起來,絲毫不氣餒,絲毫不悲觀,這正如陶淵明《讀山海經》寫的那樣:“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從以上的這些中國古代著名神話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它們共同的主題是描寫了主人公在與外界做斗爭時的悲劇性沖突,而在這些沖突的過程中,往往最終會導致英雄人物或代表正義的人物死亡。因此凝重的悲劇色彩是這些神話故事的特色。但它們也表現出另一方面帶有共同性的特色,那就是肉體的毀滅、生命的結束往往又不是斗爭的結束。鯀腹生禹、人死化鳥、棄杖化林、斷首舞干戚,都表現出至死而不屈的精神,從而表現出斗爭必然取得勝利的信心。從這方面講,它們又都是樂觀主義的。英雄人物的不幸和死亡,構成了這些故事激動人心的悲劇美,而他們最終不屈地壓倒對方的氣概,更顯示出他們的偉大和崇高,這就是這類神話故事表現出來的共同美學特征。
“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這是悲劇的重要特征,沒有沖突就沒有悲劇。在原始社會,當時人類為了維持生存和改善生存條件,就需要運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以大無畏的精神,與大自然進行不懈的爭斗。在當時生產力極為低下、甚至缺乏必要的科學知識的情況下,這種斗爭無疑是極其困苦和艱難的。在最初階段,處于弱者地位的人類經常要遭到失敗、不幸和死亡,這正是構成人類最初生活中的悲劇原因。
我們知道,任何悲劇都是由于對立面一方的強大或暫時強大以及它的殘酷性造成的,但任何真正藝術中的悲劇又絕不只是向我們展示苦難、恐怖或死亡,而是要通過“悲”反射出美,通過苦難顯示出崇高,通過“毀滅”展示出希望,從而歌頌光明、鞭撻黑暗、掃除污穢、預見未來,這才是悲劇美的靈魂。崇高和悲劇使人的心靈得到激勵,使人的精神得到振奮。因此,人的心靈需要用痛苦來刺激,使之在驚訝之中醒悟。崇高和悲劇使人體驗到一種激情,用這種激情更能讓人感受到生命的活力。從理論上說,悲劇之所以獲得藝術的“最高階段和冠冕”的殊榮,其重要原因就是其中體現著哲人們津津樂道、苦苦求索的理性意蘊。
當然,我們回過頭來看,這些古代神話故事中所表現出來的勝利和為取得勝利而采取的某些方式都帶有幻想的形式,這是因為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擴大并加深了人同自然做斗爭的范圍和方式,自然力的危害對生產生活的影響也就日益明顯。面對著強大的自然力,他們還完全缺乏科學知識和強有力的斗爭手段,但可貴的是在這些神話故事中表現出了偉大的理想和偉大的精神力量。無論是鯀、禹、夸父和精衛、還是刑天,他們的形象之所以是崇高的,就是在于他們敢于戰勝困難、面對苦難,不畏恐怖以至蔑視死亡,正是這種可貴的素質和精神力量,使之表現出崇高偉大之美。
三、中國古代神話中的崇高風格和悲劇藝術對后世文學的影響
神話是“原始的哲學、原始的科學、原始的宗教、歷史及社會的生活……,神話又是最古老的文學,其藝術是永遠不朽的。它們至今仍是詩歌、音樂、繪畫、雕刻、建筑以及一切藝術作品的感發物。”中國古代神話的這種崇高風格和悲劇藝術,對后世的文學創作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中國文學史上,悲劇文學乃至悲劇藝術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偉大愛國詩人屈原在黑暗、孤獨、冰涼的現實中奮斗,并以極大的不幸和最后的死亡構成了他的悲劇的一生。他的一生是極為不幸和可悲的,但洋溢在作品中的整個感情卻不是悲觀的,它表現的是莊嚴壓倒恐懼、正義壓倒邪惡、美壓倒丑;它所表現的是“伏清白以死直”、“九死而不悔”的不屈精神;是探索,是苦苦的追求。這種正直的悲劇美和崇高美,是與古代神話所體現出來的美學精神相一致的。不僅如此,作為開創了我國傳記文學先河、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也明顯繼承了古代神話中的這種悲劇藝術和崇高精神。劉鶚在《老殘游記》序中說:“《離騷》為屈大夫之哭泣,《史記》為太史公之哭泣”。這種說法確實有一定的道理。《史記》全書130篇,其中有57篇專寫悲劇人物,如項羽、商鞅、陳涉等,他們身上體現著真理的價值,閃耀著正義的光芒,所激起的是人們對崇高的贊美。縱觀《史記》,其風格激越高亢、慷慨悲壯,謳歌豪邁壯闊的生活、推崇建功立業的生命價值是其悲劇審美的重要特征。作品中的悲劇主人公雖然失敗或者被毀滅,但并不給人以失敗的沒落或者被毀滅的頹廢,它始終涌動著昂揚向上的精神力量。再如著名的《孔雀東南飛》、《竇娥冤》等等,無不是偉大的悲劇藝術。他們既表現“悲”,又通過悲來表現崇高、展示希望、預見光明。我國文學中的這種悲劇美,具有巨大的感人力量,中國古代神話開辟了中國悲劇主義文學的先河。
參考文獻:
[1]朱光潛.悲劇心理學[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魯迅.再論雷鋒塔的倒掉[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3]袁行霈.中國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褚斌杰.中國文學史綱要[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5]王朝聞.美學概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杜衛.美育學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7]啟良.中國文明史[M].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簡介:何莉麗(1978.8—)女,甘肅定西人,定西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教師,西北師范大學文史學院2007級在讀碩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