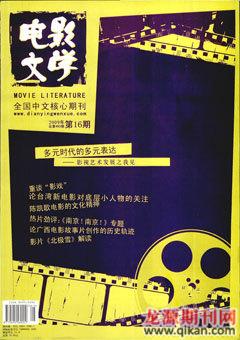糾結的《南京!南京!》,糾結的人性觀、歷史觀
20世紀注定是人類悲劇的歷史。從一戰到二戰,從二戰到冷戰,伴隨著世界各國經濟、政治、文化的關聯性或它們全球化屬性的顯現,人類在好奇地打量過彼此之后,終于劍拔弩張,繼而大打出手。或許我們今天在享受著全球化與科技進步帶來的便利與利潤的時候,抱怨17世紀發端于英國的工業革命有點忘恩負義,可誰也無法否認,正是從那場變革開始,人類的生活方式發生了徹底的改變。生活方式還只是問題的冰山之一角,真正的挑戰來自于生產力進步帶來的生產關系的戲劇性的變化:原來神圣的來自于天堂的權利被連根拔起,脫落的、得到解放的泥土翻身成了主人。人是有慣性的,人群的慣性往往大到非理性的地步。只要國家這個反映階級關系的實體存在一天。人們就需要一個頭領。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英、美的頭領在權力分立的制約下至少在形式上成為多數人的代言人,德、意、日的頭領在群氓的哄抬聲中成為一個小集團的君主,而這個小集團卻聲明為大眾服務。在服務國內大眾甚至服務整個亞洲大眾的幌子下,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
對于發生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大地上的那場戰爭,有人在反思的時候往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或者看見了森林,卻出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裝作沒有看見。明明拉貝是德國納粹在中國的主要代表之一,而納粹德國是日本的盟國,《南京!南京!》卻裝作沒有看見,一味向《辛德勒的名單》看齊,唯恐別人不把自己看做是可憐巴巴的受害者,唯恐那個好不容易從故紙堆里翻出的英雄被人識破從而令自己好不容易抓到手的精神上的救命稻草被口水淹沒。對于日本大兵角川的描寫,《南京!南京!》一味將視角對準他的人性,描寫他對慰安婦的愛,他對俘虜的愛。一瞬間,我們仿佛從炮聲隆隆、刀起刀落的血腥之地進入到了神圣的教堂,一個神父念念有詞地引導著我們去看敵人的柔情、仁慈、脆弱以及寬恕他們的重要性。實際上,人從來不曾作為嚴格意義上的個體存在,自從我們的祖先在樹林里合作獵取野獸以來,每個人的行為就和群體息息相關,群體的行為也和每個人息息相關。找出歷史人物人性化的一面然后堂而皇之甚至大言不慚地以“新解”之名演繹,是對歷史的背叛。這種在今天頗為流行的翻云覆雨的學術手法、藝術手法頗有幾分人緣。或許這是一個以新為榮、以舊為恥的時代,有人好像在憋著一股勁找人比試誰更代表潮流,誰更標新立異。這種做法一方面讓角川和《色·戒》里的易先生之流獲得了當下大眾的認可。從而嘲弄了殉難于歷史事件之中的悲劇人物,也就嘲弄了我們自己的歷史;一方面以戲說或紅色經典為名讓歷史英雄或開國元勛走媚俗路線,談情說愛兼顧指點河山,從而丑化了歷史事件之中的英雄人物,也就丑化了我們自己的歷史。于是我們不再看到好人和壞人,我們只看到人;不再看到英雄和惡徒,我們只看到平凡的人性。這也正是現代文學、后現代文學的軟肋所在:鼓吹價值虛無,一切皆被抹平,缺乏反思現實的深度,缺乏反思歷史的厚度。
歷史屬于特定的年代,在研究、表現歷史的時候應該尊重歷史,“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觀點只是對于當下研究者的權利的高度肯定,任何嚴謹的歷史學家都不曾真的企圖以這樣的態度去做研究。在眾聲喧嘩里暫時奪取話語權的往往是激進的言論。作為二戰重要組成部分的抗日戰爭是中國人民浴血八年的苦難史、抗爭史,是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史、丑惡史。在這場中日民族之間的生死較量中,中國軍隊共進行大規模和較大規模的會戰22次,重要戰役200余次,大小戰斗近20萬次,總計殲滅日軍150余萬人、偽軍118萬人。戰爭結束時,接收投降日軍128萬余人,接收投降偽軍146萬余人。據統計,“淪陷區有26省1500余縣市,面積600余萬平方千米,人民受戰爭損害者至少在2億人以上。自1937年7月7日至戰爭結束,我軍傷亡331萬多人,人民傷亡842萬多人,其他因逃避戰火,流離顛沛,凍餓疾病而死傷者更不可勝計。直接財產損失313億美元,間接財產損失204億美元,此數尚不包括東北、臺灣、海外華僑所受損失及41.6億美元的軍費損失和1000多萬軍民傷亡損害。此外,七七事變以前中國的損失未予計算,中共敵后抗日所受損失也不在內。經過中國歷史學家多年研究考證、計算得出,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共3 500多萬人,中國損失財產及戰爭消耗達5 600多億美元。”兩個國家、兩個民族之間的一場浩劫造成了如此大的損失僅僅過去60余年之后,在加害的一方未做出徹底反思的時候,《南京!南京!》意圖通過挖掘、表現人性抹平傷痛的做法有失歷史的公允。不管日籍演員中泉英雄強調自身對于這段歷史的認識有多深刻,并努力在影片中按照導演的意圖去表現這種深刻,但中泉英雄和導演不能輕易地代替兩個民族做出根本性的判斷,特別是當題材涉及中日兩國極為敏感的“南京大屠殺”并且傳媒對于民眾的影響又是如此強烈和密集時。對于日本死傷的150余萬軍人和中國傷亡的3 500多萬軍民,以及巨大數字背后更為巨大的受到傷害的兩代甚至三代人而言,需要的不是處心積慮的提防,也不是對于歷史基本事實的忘卻。牢記歷史并反思歷史,避免歷史的悲劇重演,是文藝作品涉及這段歷史時應有的基本態度。
個體的人性、個體的情欲根本不該被抹殺,也根本不應該被放大。加入到那場戰爭中去的兩國人民、士兵、軍官、政府首腦以及他們那段歷史的繼承者——我們,都是能思考的血肉之軀,都有親朋好友、七情六欲,但又都是被編織到社會歷史大網絡上的一個小環。以角川為代表的日本軍人有其基本的人性并不奇怪,沒有才奇怪。但是如果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中格外凸顯個體的人性,就會有意無意地掩蓋、淡化群體的行為。個體是群體的個體,個體的偶然性作為不能改變群體作為的性質。況且,個體,不管是真有其人還是藝術虛構,之所以來表現他,是因為想通過這個個體來說明群體的、一般的情況。在《南京!南京!》中用大量篇幅一味渲染角川的愛人之心、仁慈之心,容易誤導受眾,容易造成“日本軍隊是在被蒙蔽的、不知情的情況下犯下了罪行”的印象。實際上,在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指引下,在覬覦他國的土地、資源的野心再也按捺不住的時候,一些日本民眾的確配合甚至慫恿政府邁出了侵略的關鍵步伐。只不過,當角川等個體面對自己親自參與發動的侵略機器碾壓過的血肉模糊、人倫盡喪的事實時+產生了反觀自身后產生的“惡心”的感覺。這種早已被薩特解讀透徹的感覺是在人面對現實的荒誕時產生的無聊感、無力感。以角川為代表的參與侵略戰爭的日本軍人不遠萬里、遠涉重洋來到中國,拋妻離子、背井離鄉,來到一個陌生的國度,和另一個民族完全陌生的一群鮮活的無冤無仇的生命廝殺在一起,一些具有反思精神的個體就會對自己參與發動的群體事件產生厭倦的感覺:相對于“自己”這一個體所放棄的親情、社會關系網絡而言、重復的殺人放火行為是無聊的,一切是沒有意義、不值得的:的確如此,角川和慰安婦的畸形的愛情其結局注定是痛苦的——甚至連痛苦的感覺都在不斷的重復中消磨了、
消失了,留下的只是麻木、惡心。但是,群體的行為不因為個體的反思而自動被糾正或被抵消,群體行為方式的巨大慣性將會在輕輕壓倒少數個體的自由意志后繼續前行,直到有一種更巨大的群體行為將其阻止。
在群體這個大機器里,個體是渺小的,個體的意志是脆弱的。當一些個體因為客觀上參與了對于群體而言意義重大的非人性事件時,產生動搖和恍惚是可以想見的。相對于群體對于目標的堅持,個體往往容易在具體問題上同群休之間產生離心力,但是,歷史是個體的合力——群體的力量寫就的。《南京!南京!》以南京大屠殺這一群體事件為題材和背景全面演繹從歷史資料里找到的以角川為代表的某些日本軍人個體行為相對于群體的不協調,是典型的“一葉障目”的行為,是對歷史的不公允的演繹。有人會說,電影是一種藝術品,表現歷史的時候應該允許適當的演繹、局部的放大,如此才能出新,才能吸引觀眾。表現一段與當下社會人生關系不大的歷史,也許可以采取演繹的手法,但是日本侵華、八年抗戰、南京大屠殺等歷史題材太過于沉重,與現實的中國社會、日本社會仍舊存在緊密的互動關系,處理有關這段歷史的題材應本著尊重、謹慎的原則,本著照顧到當下兩國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感情的原則。近年來,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應該學會原諒,應該走出悲情,不應該再繼續強調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如此才能真正平等地和他者對話,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大國。實際上,我們從不缺乏寬容的精神,只不過,我們不希望別人利用這種寬容。在深刻的反思、真誠的懺悔還沒有到來的時候,一味地寬容、諒解甚至忘記在某種意義上是對殘暴行為的鼓勵。這種做法。不僅有礙于后人全面理解歷史,而且有害于當下的和平。當我們對于這段歷史不再爭議的時候,當雙方都表現出大國氣度的時候,我們才能以平和的心態反思歷史,觀照現實,一廂情愿的做法無益于長久的和平。同理,在表現紅色題材、開國英雄題材時,也要考慮到歷史與現實的緊密互動關系。
相對于侵略的一方,陸建雄、唐先生、姜淑云、小豆子等所代表的被侵略的、被蹂躪的一方的人性更應該被著重表現。他們的親情、愛情、愛國之情,他們對于國土淪喪、家破人亡的感受,相對于角川等人而言,應該更具有普遍性,更深刻。也許有人會說,關于這段歷史的宏大敘事,已經進行了半個多世紀,是時候換一種視角、換一種思維方式來進行更全面的思考了。的確有大量的關于這段歷史的影視作品站在被加害者的視角進行了反思,但是這些作品往往從國家、民族的宏觀尺度出發,缺少對于被加害的個體的微觀的、人性的觀照。當題材涉及南京大屠殺時,如果是出于創新思維、創新藝術表現手法的考慮,我們更有理由采取被加害者這一角度而不是相反。而在本片中,開場幾十分鐘的戰爭場景,完全站在相反的角度,讓人恍惚間會產生這樣一種想法:怎么抵抗力量還設有被消滅?難道這就是影片要達到的效果?
人性是豐富的,豐富的人性特質是普遍的。一種被群體裹挾、激發的惡和一種反思群體行為產生的善共存于一個個體是矛盾規律所允許的。意圖張揚善行、隱藏惡行和意圖夸大惡行、隱藏善行一樣都是片面的。人性中的愛、仁慈普遍存在于具有正常情感的個體當中,這些特質不因戰爭的來臨而消失,也不因戰爭的來臨而產生。表現角川等人的愛、仁慈,換一個場景、換一個時代同樣可以達到目的,沒有必要劍走偏鋒,非得在民族的傷口和人性的豐富之間狹窄的如同刀刃一般的小路上跳舞。這種舞蹈,因其新穎別樣以及對度的巧妙把握,往往可以得到不明就里的大眾和媒體的雙重表揚,就像導演的某些其他作品一樣。
注釋:
①1946年底國民政府之《中國責令日本賠償損失之說貼》。
[作者簡介] 孫云寬(1976—),男,山東即墨人,青島農業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講師,文藝學博士,研究方向:戲劇理論、影視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