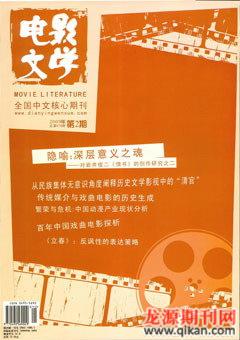人類(lèi)精神生存困境的洞察
苗珍虎
[摘要]本文主要從藝術(shù)品質(zhì)、道德評(píng)判和人生信仰等三個(gè)方面,對(duì)卡夫卡的《饑餓藝術(shù)家》、《判決》和《鄉(xiāng)村醫(yī)生》等幾部短篇小說(shuō)進(jìn)行了分析,闡述了卡夫卡對(duì)人類(lèi)精神生存困境的洞察。
[關(guān)鍵詞]精神;藝術(shù);道德,信仰
卡夫卡在他的《致父親》的長(zhǎng)信中,曾經(jīng)很明確地表述了對(duì)于人類(lèi)精神生存境況的思考:“自我有思考能力以來(lái),我就對(duì)精神存在的維護(hù)問(wèn)題懷著極深的憂(yōu)慮,以致其他一切于我全是無(wú)所謂的。”本文主要圍繞卡夫卡的《饑餓藝術(shù)家》、《判決》和《鄉(xiāng)村醫(yī)生》等幾部短篇小說(shuō),來(lái)闡述卡夫卡對(duì)人類(lèi)精神生存困境的洞察。
在《饑餓藝術(shù)家》中,作者關(guān)注的是關(guān)于藝術(shù)品質(zhì)方面的精神困境問(wèn)題。小說(shuō)描述了經(jīng)理把饑餓藝術(shù)家關(guān)在鐵籠內(nèi)進(jìn)行表演,時(shí)間長(zhǎng)達(dá)四十天。表演結(jié)束時(shí),饑餓藝術(shù)家已經(jīng)“處于昏厥狀態(tài)、半醒半睡”,“虛弱不堪,奄奄一息”。后來(lái),饑餓藝術(shù)家被一個(gè)馬戲團(tuán)聘去,人們把他和籠子安插在一個(gè)交通路口,為的是游客去看野獸時(shí)能順便看到他。可是人們忘了更換記日期數(shù)的牌子,饑餓藝術(shù)家無(wú)限期地絕食下去,終于餓死。在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上,卡夫卡對(duì)于人類(lèi)精神生存困境采用了鮮明的對(duì)比。
一、饑餓與藝術(shù)家
饑餓本是人生迫不得已的生存狀況,饑餓卻用來(lái)表演本身存在著荒誕的對(duì)比組合,這固然說(shuō)明藝術(shù)門(mén)類(lèi)有其獨(dú)特性的一面和藝術(shù)家的“異化”,但同時(shí)也體現(xiàn)了藝術(shù)家生存境況的窘迫以及對(duì)于藝術(shù)信仰的堅(jiān)持精神,另一方面,結(jié)合作者一生對(duì)寫(xiě)作的追求精神:“在我身上最容易看得出一種朝著寫(xiě)作的集中,當(dāng)我的肌體中清楚地顯示出寫(xiě)作是我本質(zhì)中最有效的方向時(shí),一切都朝它涌去,撇下了獲得性生活、吃、喝、哲學(xué)思考,尤其是音樂(lè)的快樂(lè)的一切能力。我在所有這些方面都萎縮了。這是必要的,因?yàn)槲业牧α烤推湔w而言少得可憐,只有集中起來(lái)才能捉襟見(jiàn)肘地為寫(xiě)作這一目的服務(wù)。”挑戰(zhàn)物質(zhì)制約的極限而獻(xiàn)身于饑餓藝術(shù)的藝術(shù)家,正是作者艱苦而堅(jiān)韌的寫(xiě)作生活的隱喻寫(xiě)照。
二、觀眾與藝術(shù)家
人世間價(jià)值判斷的標(biāo)準(zhǔn)多是出于好奇而非對(duì)藝術(shù)的真正熱愛(ài)與尊重,藝術(shù)家的表演卻是為了真誠(chéng)地捍衛(wèi)藝術(shù)的尊嚴(yán),正如吳曉東先生所說(shuō)“饑餓構(gòu)成的是饑餓藝術(shù)家的榮譽(yù),他正是為饑餓而生存的人,饑餓甚至是他的生存目的和信仰。”因而饑餓藝術(shù)家的表演可謂盡心盡力:“他時(shí)而有禮貌地向大家點(diǎn)頭打個(gè)招呼,時(shí)而用力微笑著回答大家的問(wèn)題。他還時(shí)不時(shí)把胳膊伸出柵欄,讓人摸摸瞧瞧,以感覺(jué)到他是多么干瘦。隨后又深深陷入沉思,任何人對(duì)他都變得不復(fù)存在,連籠子里那對(duì)他至關(guān)重要的鐘表(籠子里惟一的東西)發(fā)出的響聲也充耳不聞,只是那雙幾乎閉著的眼睛愣神地看著前方,偶爾呷一口小玻璃杯里的水潤(rùn)一潤(rùn)嘴唇。”這樣現(xiàn)實(shí)的功利性與藝術(shù)的圣潔性之間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饑餓表演本身是違反人性、違反藝術(shù)規(guī)律的行為,而觀眾的欣賞卻一度艋況空前:“當(dāng)時(shí),壘城的人都在為饑餓表演忙忙碌碌,觀眾與日俱增,人人都渴望每天至少觀看一次饑餓藝術(shù)家的表演。臨近表演后期,不少人買(mǎi)了長(zhǎng)期票,天天坐在小鐵籠子跟前,就是晚上,觀眾也絡(luò)繹不絕。”這種盛況說(shuō)明了觀眾審美趣味的庸俗與低下,同時(shí)藝術(shù)一旦淪為作秀的表演,便不可避免地會(huì)降低藝術(shù)本身對(duì)真善美的導(dǎo)向作用和藝術(shù)感召力。另一方面,以觀眾為代表的蕓蕓眾生并不相信藝術(shù)家的藝術(shù)耐力,“他們總認(rèn)為,饑餓藝術(shù)家絕對(duì)有妙招搞點(diǎn)存貨填填肚子。”他們只相信藝術(shù)家一定克服不了食物的誘惑而放棄持續(xù)的表演,顯然觀眾更愿意追求感官的刺激而不是精神的塑造與靈魂的升華,因此也就更難以理解藝術(shù)家的藝術(shù)人格。“只有饑餓藝術(shù)家自己心里最清楚,只有他才算得上是對(duì)自己的饑餓表演最為滿(mǎn)意的觀眾。”
三、藝術(shù)家與美洲豹子
當(dāng)饑餓藝術(shù)家被馬戲團(tuán)聘去,無(wú)限期地絕食下去而終于餓死后,“籠子里放進(jìn)了一只年輕的美洲豹子”。人是有思想的社會(huì)個(gè)體,雖然同樣是在籠子里,藝術(shù)家表演饑餓是對(duì)藝術(shù)的追求,而美洲豹子則無(wú)所謂自由,填飽肚子就行,美洲豹子作為動(dòng)物的行為完全是基于本能,然而有思想的饑餓藝術(shù)家忠于自己的事業(yè)卻獻(xiàn)出了生命,小豹子卻生活得很自在:“失去自由對(duì)它似乎都無(wú)所謂,這個(gè)高貴的軀體應(yīng)有盡有,不僅帶著利爪,而且連自由好像也帶在身邊,自由似乎就藏在它利齒的某個(gè)地方”,這種對(duì)比真正彰顯出人類(lèi)精神生存的困境與荒誕,即作為社會(huì)存在的主體越是深入思考生活的意義、藝術(shù)的價(jià)值、人身的自由,越是堅(jiān)持藝術(shù)的純粹品質(zhì),卻還是“找不到適合胃口的食物”,最終只能“以‘肉的毀滅(餓到死亡)換來(lái)‘靈的至美(達(dá)到最高的藝術(shù)境界)”。
《饑餓藝術(shù)家》用荒誕的形式、真誠(chéng)的行為和悲慘的結(jié)局,演繹了人類(lèi)精神生存的困境,同時(shí)也說(shuō)明藝術(shù)如果不能貼近生活做到與時(shí)俱進(jìn),就會(huì)被時(shí)代被社會(huì)所遺棄,但藝術(shù)的純粹品質(zhì)與社會(huì)大眾的審美趣味之間一旦存在著鮮明的對(duì)立,兩者之間又是很難調(diào)和的。
《饑餓藝術(shù)家》所反映出的這種對(duì)人類(lèi)精神生存的困境的寓言,顯示了卡夫卡在灰暗的場(chǎng)景和消極的世界觀背,后對(duì)人類(lèi)生存狀況的深刻洞察,這種洞察體現(xiàn)在《判決》中,則是作家從道德評(píng)判的角度對(duì)人類(lèi)生存精神困境所作的詮釋。
結(jié)合作者的生活背景來(lái)看,《判決》也是卡夫卡真實(shí)生活的一個(gè)縮影。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的一個(gè)猶太商人家庭,他的父親粗暴、專(zhuān)制,卡夫卡在《致父親》的長(zhǎng)信中不止一次地表述過(guò)父子之間的緊張關(guān)系:“只需我對(duì)一個(gè)人有一點(diǎn)興趣(就我的天性而言,這種情況并不多),你就會(huì)毫不考慮我的感情、毫不尊重我的評(píng)價(jià)地對(duì)這個(gè)人破口大罵、污蔑、丑化。”父親想把兒子培養(yǎng)成為性格堅(jiān)強(qiáng)而又能干的年輕人,但結(jié)果是適得其反:“你的教育對(duì)一個(gè)像你注重類(lèi)型的人很可能會(huì)是有效的……你在我身上可以說(shuō)是完全失敗了。”卡夫卡內(nèi)心中一直對(duì)父親存有無(wú)法消除的畏懼心理。文中父親對(duì)兒子的言行正是卡夫卡本人現(xiàn)實(shí)狀況的寫(xiě)照:“我寫(xiě)的是關(guān)于你的事,我在那里發(fā)泄的僅僅是在你懷里不能發(fā)泄的。”
人生信仰是人類(lèi)生存的精神支柱,是生命質(zhì)量提升的關(guān)鍵,《鄉(xiāng)村醫(yī)生》中馬的出場(chǎng)體現(xiàn)了卡夫卡特有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即以介于真實(shí)與荒誕之間的情節(jié)描寫(xiě)來(lái)展示人類(lèi)精神生存的困境,法國(guó)作家紀(jì)德就認(rèn)為卡夫卡的作品有兩個(gè)世界:“一是對(duì)夢(mèng)幻世界‘自然主義式的再現(xiàn)(通過(guò)精致入微的畫(huà)面使之可信),二是大膽地向神秘主義的轉(zhuǎn)換”。通過(guò)這兩個(gè)世界的展示,卡夫卡闡述了人生信仰與生存價(jià)值的沖突:馬車(chē)夫決定幫忙的實(shí)質(zhì)卻是別有企圖的陷害,醫(yī)生出于醫(yī)德醫(yī)治孩子卻違反了孩子自由選擇生死的權(quán)利,當(dāng)醫(yī)生堅(jiān)定信念去救人時(shí)卻又無(wú)力拯救自己的侍女蒙受馬車(chē)夫的羞辱,表面上是別人在傷害自己,實(shí)際上卻是要治病救人的信念和社會(huì)責(zé)任感騙了他自己,或者說(shuō)是他過(guò)于忠誠(chéng)于自己的信念而導(dǎo)致了自身的尷尬處境。人若沒(méi)有信念、責(zé)任感和公德心,便沒(méi)有精神方面的存在價(jià)值,但如果有精神引領(lǐng)作用的信念會(huì)摧毀人性的話(huà),那么信念和現(xiàn)實(shí)存在秩序之間的矛盾就會(huì)造成無(wú)法融合的脫節(jié),于是人只能成為精神與肉體分裂的動(dòng)物。
卡夫卡很重視精神世界的富足:“除了一個(gè)精神世界外,別的都不存在,我們所稱(chēng)之為感性世界的東西,不過(guò)是精神世界中的惡而已,而我們稱(chēng)之為惡者,不過(guò)是我們永恒發(fā)展中的一個(gè)瞬間的必然。”從卡夫卡的短篇小說(shuō)中,讀者可以感受到卡夫卡對(duì)人類(lèi)精神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