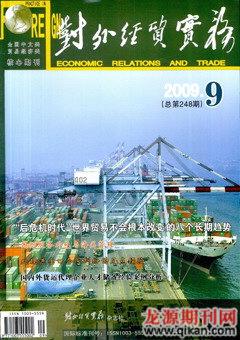處理進出口合同糾紛的幾點經驗
王正華
國際貨物買賣中,雙方在合同商訂時都會對合同履行中貿易糾紛的解決方式以條款形式予以約定,以求爭議、糾紛的順利解決。常見合同爭議、糾紛解決方式的約定多在仲裁條款中描述為:“本合同所引起的一切爭議,雙方應采取友好協商的方式解決,若友好協商不能達成一致時,則該爭議案應提交……仲裁解決(All disputes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Contract or the execution thereof shall be settled friendly through negotiations. In case no settlement can be reached, the case may then be submitted for arbitration to…)”。實際業務中,當合同履行過程中產生爭議、發生糾紛時,當事人首先采取的解決方式一定是協商,而貿易糾紛處理的協商過程卻往往是艱難的,費時費力甚至是需要投入財力的。在協商不能達成一致時,受損害一方當事人則會考慮采用約定的仲裁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筆者在多年的外經貿實踐中,經歷和參與了一些國際貿易爭議、糾紛的處理工作,現將一些體會歸結如下,供讀者參考。
一、盡最大努力,友好協商將爭議消除在萌芽階段
友好協商解決貿易合同糾紛是最好的選擇,但前提建立在買賣雙方重合同,守信用,并且通過協商能夠對違約責任及損失的程度達成一致認識的基礎上。在一方不能很好的信守合同,或者是對于損害補償的認定不能達成一致時,協商就變成又一次復雜和艱難的商務談判。此時由于合同一方的違約已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損害,雙方的談判地位優劣分明:往往是受損害的一方處于被動地位,違約一方反而主動。當違約方信用差或是備嘗能力有限時,協商就很容易陷入僵局。面對這種情況,受損害方審時度勢和打破僵局的談判能力就受到考驗。實踐中若能注意到下述幾點,則會有利于爭議的協商解決:
法理上講,貿易合同糾紛中受損害一方有向對方請求損害補償的權利,但能否使自身的利益損失真正得到補償,卻取決于違約方的態度。違約損害一旦發生,受損害方所主張的補償的實行權往往百分之百地掌握在違約的一方,受損害方可能因已完成交貨(或付款)而完全失去了對違約方的控制。
買賣合同履行中,許多違約事件在初始階段是有可能通過雙方努力來消除的,或是通過調整各方的履約行為以減少違約損害。例如遲期開證、遲期交貨、遲期付款等,若當事人能隨時關注合同的執行過程,保持聯系、及時溝通,及早發現問題,提出異議,將違約及損害控制在初期,一方面通過協商使違約方盡快實施補救,同時調整己方的履約步驟,控制損害的擴大,除非主觀故意,違約方就會及時采取措施予以補救。例如;出口業務中及早發現買方貨款支付的違約,賣方就可調整己方的備貨時間;機電設備進口業務中,及早發現賣方交貨違約,買方就可在提示賣方的同時,調整己方配套設施建設工程進度及其它配套設備采購合同的執行等等,這樣就可降低對方違約造成的損害,減少爭議索賠金額,異議的處理協商就較容易達成一致,使損害得以及時補救,使雙方合同的履行重新回歸到正常軌道。
即使遇到有故意違約意圖的合作伙伴,早期發現也有利于當事人在采取防范措施的同時向對方發出警示,告知違約的嚴重后果等,迫使其改變想法,繼續履約。
二、講究洽商策略,協助違約方尋求補償措施
作為受損害的一方,要實現自身利益的補償,需耐心與對方進行充分交流,有時甚至需站在對方立場上思考、理解對方,給對方以信任感,替其出主意,想辦法,解決交貨或付款的困難,誠心加耐心往往會得到較好的結果。而受損方過激的則往往會使協商陷入僵局。
曾有這樣的案例:某公司一筆玻璃器皿出口業務,合同額10萬美元;價格條件CIF HONGKONG;支付條件:D/A 60天遠期。買方在辦理了承兌交單并提貨后,卻未能在60天匯票到期時付款。對此,我方業務員保持冷靜的態度,經與對方溝通及側面了解,得知對方逾期不付確是由于經營困難導致資金周轉不靈所致,在對買方信用進行分析后,我方對其表示理解,主動提出給買方30天的寬限。結果,在第31天,買方向我全額匯付了此項貨款,問題得到了解決。我方雖然損失了30天的銀行利息,但卻由此得到了買方的極大信賴,于是雙方的合作日益擴大,穩定發展,取得了很好的長期利益。
有些情況下,違約一方既有客觀原因,亦有主觀故意,受損害一方就需要花費更大的氣力去解決,如給對方一些更優惠的承諾,甚至犧牲部分利益來滿足對方的不合理要求,如允許違約方在一定時期內分批償付的方式,以取得損害的補償。例:我某公司出口歐洲一批玻璃器皿,憑賣方樣品成交,合同總價為3萬美元;付款方式為裝船后20天T/T支付,我方裝船交貨并交單20天后,外方卻以種種借口拖延付款。經多次協商,外方再三推諉不付,同時又要求繼續向我訂貨。經了解得知,買方為一新設立經營玻璃制品業務的公司,資金周轉不靈,經慎重考慮,我方提出由外方在后續一年的業務中分批攤付此項貨款的建議,外方即表示接受。這樣我們不僅在一年多的業務中陸續收回了此筆款項,還使得其與我方玻璃器皿業務繼續開展多年,業務量也不斷擴大。此例說明只要受損害一方利益能有所補償,則協商妥協都應是首選的路徑。但對這樣的客戶,在后續合同的支付條款約定及執行中務必嚴格防范和控制新的違約發生。
三、申請國際仲裁必須謹慎行事
如前所述,國際貨物買賣合同通常都會約定仲裁協議(條款),當協商無法解決爭議時,受損害的一方必然會想到將爭議提交仲裁。此時須注意到,選擇仲裁(訴訟)方式解決糾紛時,仲裁案的申請人(原告)即受損害方是需要先行投入財力(仲裁費、律師費等)、人力的,而這些投入只有在仲裁案取得勝訴并順利執行后才能得到部分補償。
一定要研究仲裁(訴訟)條款,重新審視其中約定對己方的利弊,主要是分析仲裁機構、仲裁地點(訴訟的法律管轄地)是否有利于己方的仲裁活動。如:地點關系到費用投入的大小;使用的語言文字關系到資料的準確性,陳述答辯抗辯的效果;人際關系則直接影響仲裁的結果。
筆者曾經歷過違約性質相同的兩例仲裁案,同一賣方不同買方的兩項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均由于買方違反支付條件協商無果,賣方將爭議案提交仲裁。結果斯德哥爾摩的國際商會仲裁院與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的裁決結果大相徑庭,前者利于賣方,后者卻明顯有利于買方。所以,一定要認真研究造成損害的大小及勝訴可能得到補償的數額,計算仲裁須投入的費用成本等,仔細權衡,謹慎行事。
還要研究被申請方的商業信用及賠償能力,這一點直接關系到仲裁(訴訟)裁(判)決的執行問題。受損害一方所希望得到的當然是實際的利益補償,而不止是一紙裁(判)決書,而敗訴方主動執行裁決的可能性大小,是受損害一方必須考慮的問題。當對方為重商業信用的大公司,具有賠償能力,雙方協商未果的原因
是對違約補償的責任、利益不能達成一致時,則通過仲裁來解決是最為合適的。公平公正的裁決一經做出,對方會主動執行,使受損害一方得到補償。反之,若違約方是商業信用差的小公司,賠償能力有限,則一定要慎重考慮,更不可輕易將爭議案提起仲裁或訴訟。
四、申請強制執行裁決不能盲目行事
在對方不主動執行仲裁裁決時,勝訴的受損害方只能通過敗訴方所在國家(地區)的司法機構強制執行。此時有兩個問題必須考慮:
1.違約方所在國是否為相關國際公約(1958年紐約公約)的成員國。只有違約方所在國家為公約的締約國時,強制執行國外做出的仲裁裁決才有可能。否則,執行幾乎沒有可能。
2.受損害一方在違約方所在國的訴訟能力。申請執行仲裁裁決是需按法律程序進行的,雖然按公約法院承認國外仲裁裁決,但其有權對仲裁的程序的呵護規則予以審查,以決定接受執行申請,這就需要申請人再做工作。是否有能力在對方所在國家(地區)打一場執行官司,受損方要有自知之明。筆者曾自任律師,訴美國某公司的仲裁案就是很好的例證:一項進口業務,外方提交的設備存在嚴重的設計缺陷,造成我方巨大損失。雙方協商一年多未果后,我進口商將此爭議案提交仲裁(仲裁費為12萬元人民幣),后經中國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合議庭裁定:美方應補償我方損失計約40萬美元。由于外方拒不執行裁決,我方便投入兩萬多美元在新澤西州申請執行,美國法院根據“紐約公約”對該案的仲裁程序進行審理,結果一方面由于費用原因,代理律師不力,又由于在國外執行,我方法律文件的補交難能及時,導致執行案初審敗訴。而上訴的困難更大,此項裁決終未能執行。此案中,我方委托人雖贏得了仲裁裁決,但卻不僅沒有拿到任何損害補償,反而又增加國內仲裁費、律師費、資產調查、差旅費等支出計約二十五萬元人民幣;國外執行申請花費兩萬美元。
另一則案例:2002年,筆者曾得到韓國某知名企業請求:協助其仲裁裁決在中國某地的執行,得知該韓國企業作為原告,歷時一年多取得中國國際貿易仲裁委員會裁決:裁定我內地某企業應償還其貨款余額及利息等費用等計約270萬美元。但拿到勝訴裁決的韓國企業委托了當地知名的律師申請裁決的執行時,卻發現由于被申請人的地方政治、經濟背景原因,使得裁決執行申請困難重重。據了解,該韓國企業最終放棄了該項270萬美元勝訴裁決的執行申請。國際仲裁裁決的執行難由此可見一斑。
對商業信用極差且再無合作可能的違約方,仲裁的后果很可能會是受損害方損失的加重或是得不償失,這時放棄索賠也許是一種更明智的選擇。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爭議、糾紛發生時,協商解決是最好的途徑,尤其是損害金額不大的爭議案,應盡量通過協商解決,補償方式也應靈活。而選擇訴訟則應是不得已的選擇,務必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