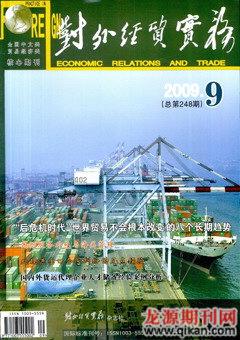解析美國工會及其對中國企業的影響
李惠先 王嗣杰
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的背景下,美國汽車的三巨頭: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也陷入了破產的危機,不得不向美國政府請求救濟。誠然,導致汽車三巨頭的沒落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為引人注意的莫過于三巨頭高額的人力成本。
據美國密歇根州的汽車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通用汽車工人的小時工資(包括福利在內)為70-78美元,比豐田和本田等日本企業美國工廠的人力成本高出近30美元。來自美國科爾尼管理咨詢公司的數據顯示,通用每輛車上分擔的醫療保險成本為1500美元,大眾為418美元,豐田只有97美元。在通用工作的工人們每年的薪金有固定漲幅,享受著優厚的退休金和醫療福利,雇員的家屬也包括在公司支付的醫療福利范圍之內,工人們在工作中也頗為自由,可以在流水線上吸煙,可以為沒有干活的“加班”領取加班費,不能輕易地被解雇……。
工人們能夠有如此“過分”的優厚待遇與一個組織密切相關,這就是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美國最大的獨立工會,簡稱UAW。
一、 UAW與美國三大汽車公司
UAW成立于1936年,目的是將汽車工人聯合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1936-1937年間,UAW組織了一系列罷工、靜坐、破壞以及其他的一些手段,最終迫使三大汽車公司承認其代表工人談判的合法地位,成為汽車工人利益的代言人。UAW也因此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戰斗力的工會”。UAW在其高峰時期,在整個北美多達150萬人。1948年,VAW與通用汽車公司達成協議,公司承諾每年都要增加工人的工資,時至今日;通用汽車公司工人年薪平均達17萬美元,而美國一般的教授、工程師也只有10萬美元;同時,工人被解雇可以得到95%的工資,而且可以無限期待業。由于工人捧著“鐵飯碗”,生產效率低下就成為通用的致命傷,這也是通用汽車公司這次不得不選擇破產的重要原因之一。
通過與美國三大汽車公司的談判,UAW不斷為工人爭取了一系列的權力,如加班工資、帶薪假期、申訴程序、醫療保險等。20世紀50年代三大汽車公司的慷慨解囊,使工會工人們享受著豐厚的福利待遇,也為三巨頭沉重的人力負擔埋下了伏筆。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的爆發,使三大汽車公司熱衷的大車型失去吸引力,以日本為代表的國外車型占據了美國國內汽車市場的50%,三大汽車公司業績迅速滑坡,汽車工人們工資和福利待遇的提高與美國汽車制造商的財富和收益的下降產生了矛盾。而且,勞動成本問題也使三大公司與外國品牌的競爭中明顯處于劣勢。大多數外國品牌的美國工廠成功抵制了UAW的侵蝕,有助于保持較低的人工成本。
美國三大汽車公司為了設法爬出這個成本黑洞,在與UAW談判妥協的同時,又不得不進行艱難的抗爭。盡管采取的員工買斷、建立醫療信托基金等方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UAW做出的一些讓步并不能使三大汽車公司發生根本的改變,歷史的沉積使三大公司距離輕裝上陣依然遙遠。三大汽車巨頭正被UAW這個被稱為“最霸道的工會”慢慢消耗和吞噬。
二、 美國工會扮演的角色
除了UAW,在美國還有很多其他的工會組織。勞工聯合會和產業組織聯合會(AFL-CIO)是美國最大的勞工組織,它是美國約100個全國工會和國際工會自愿的聯合組織。美國工會是美國社會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它的角色可以概括為以下4個方面:
1.工人利益的代言人。工會代表雇員的利益在一些重大的企業決策問題上出面與資方進行談判。工會為吸引更多的會員就要為員工謀利益,一旦工會認為員工利益受損,就會采取行動對資方,甚至政府施加壓力。罷工是美國工會達到目的主要手段,也是要挾資方的有利武器。通過與三大汽車公司的談判,UAW為工人爭取了一系列的權力,并努力保住工人的飯碗。不過,從UAW與美國汽車公司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工會的戰斗力會如此強大,甚至會拼命地擴大自己的利益而將工廠吞噬。
2.政治活動的熱心人。美國工會十分清楚,在美國這樣一個法制社會,要爭取利益就需要一定的政黨在議會中充當其代言人,以影響立法和政治決策。每次美國大選,美國的勞工組織都會投入大量的金錢和人力來支持民主黨,據統計在2008年的選舉中,各個工會組織在本次選舉中的投入加起來,有可能達到4億。可以說,奧巴馬的上臺,美國工會功不可沒。多年以來,美國的勞工組織一直在試圖沖破《塔夫脫一哈特萊法案》設下的限制,奧巴馬的上臺能否為美國勞工組織的發展帶來機遇,還要拭目以待。
3.財大氣粗的投資人。能夠加入到政治活動中,必然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支持。鮮為人知的是,超過一半的2006年美國《財富》500強企業中,工會養老基金是最大股東。工會養老基金已取代投資銀行和共同基金成為最大的機構投資人。工會擁有的巨額養老金完全能夠沖擊投資市場以及工大企業的經營決策。工會養老基金可以通過股東身份,要求公司管理層改變公司的勞資關系和海外采購策略,要求公司的行為滿足SA8000等勞工標準。如果公司拒絕改變,工會養老基金可能威脅拋售公司股票或提起股東訴訟,對公司管理層造成壓力。在金融危機中,摩根士丹利、美國銀行和華盛頓互惠銀行等多家銀行都受到工會類型的機構投資者沖擊。
4.經濟政策的影響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美國工會的財大氣粗使得它成為美國社會重要的利益集團之一,它可以用自己的強勢地位為自己的集團謀福利,最主要的就體現在對經濟政策的影響上。在奧巴馬的對外貿易政策中,即可以看到工會的影響。例如,美國工會組織認為哥倫比亞在確保工會領導人免受暴力威脅方面做得不夠,哥美貿易協定就會在國會面臨阻力。而奧巴馬政府對中美貿易的強硬立場,也部分來源于美國工會的支持,因為美國工會始終視中國為“頭號勁敵”,把美國制造業萎縮歸咎于美國企業到中國設廠及中國制造對美國市場的巨大威脅。
三、 美國工會對中國企業的影響
在歷史上,美國最大的勞工組織勞聯-產聯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稱不與“官辦工會”發生關系,對中國頗為仇視。而且,隨著中國加入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試圖走進美國,無論是通過商品出口還是海外直接投資設廠的方式,都不可避免的會受到美國工會的影響。
1999年,中美之間在西雅圖就中國加入WTO展開關鍵性談判期間,美國勞聯-產聯組織大批產業工人前往會場示威游行,并采取說服,甚至恐嚇的手段要求議員們反對中國加入世貿。而在中美紡織品貿易摩擦中,工會是促使政府出臺紡織品貿易保護政策的主要力量。美國工會認為大量中國紡織品的進口造成了紡織品工人的失業而給政府施壓。在2009年初,北美鋼鐵工人聯合會(USWA)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提出請愿書,要求限制從中國進口輪胎。他們認為近年中國進口輪胎數量的增加,使得原本萎縮的輪胎市場正面臨崩潰,是美國制造業裁員的主要原因。現階段,工會的阻撓成為貿易保護的武器。
美國工會不但為中國商品進口美國設置種種障礙,頻發的工人罷工也會給中國的
企業帶來巨大影響。如2006年美國西海岸港口工人長達10多天的罷工就給中國企業帶來了巨大損失。中遠集團的7艘船滯留在西海岸,每船每日的費用共計24000美元,而船只滯留又延誤了下一班貨物的運輸,不但影響了運輸收入,大量貨物的積壓又增加了保管費用。受影響的不但是航運公司,外貿企業由于貨物無法運出造成損失,國內的企業由于原材料無法運達而造成了停工。這場罷工給中國企業上了沉重一課,在全球化背景下,哪怕是國內企業都會或多或少地受到國外政治環境的影響,這是商務決策中必須要考慮的。
對于并購或直接投資美國公司的中國企業來說,更要考慮美國工會這一重要的利益相關人。工會因素成為影響并購決策的重要因素之一。上世紀90年代,海爾集團投資美國選擇制造基地時,曾考慮過美國北方的工業重鎮,但是鑒于那里工會力量強大,最后將工廠設在工會力量比較薄弱的南卡羅來那州,因為該州法律并無企業必須成立工會的規定。2005年,海爾曾參與美國老牌家電巨頭美泰的競購,除了要得到董事會和股東大會的許可,美泰的任何買家都必須和其工會達成一致意見,否則任何并購交易都很難成功。2007年3月,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出于戰略考慮曾意欲收購處于困境中的克萊斯勒公司,然而,最終這個計劃還是沒有實施,主要原因并不在錢上,而在于缺乏應對強大的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的經驗。從三大汽車巨頭的遭遇來看,終止這項并購計劃是明智的。
四、 應對美國工會的建議
1.充分調研。首先要了解美國的法律框架,關注和研究美國工會知識和運行模式。如前分析,國外工會與中國的工會是截然不同的,計劃體制下的工會是企業和員工聯系的紐帶,能促進企業的和諧;而市場經濟下的工會,是企業的對手,完全代表工人的利益。沿用看待我國工會的慣用思維對待美國工會,必然是“水土不服”的。中國企業的前期調研往往很草率,或依賴國外中介,或迷信蜻蜓點水式的“商務考察團”,這無疑增加了海外投資的風險。而日、美公司在進入境外市場之前,會組織人力、邀請學者對市場趨勢、投資國文化和政治環境進行深入分析,甚至邀請國際問題專家、國際觀察家的咨詢或全程參與,這是中國企業很需要學習借鑒的。
2.策略應對。對于已在外設廠的中國企業,當遭遇勞工麻煩時,要采取策略性的應對方式,而不是“硬碰硬”。這點經驗來自于中國企業在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當年首鋼秘魯公司的勞資糾紛讓首鋼痛苦不堪。由于缺乏對秘魯工會狀況的了解,中方沿用了國內工會思維對待秘魯工人,使得秘魯工人“得寸進尺”,要求不斷升級。而面對工人罷工,剛開始派去的中方管理層,處理方式“特別強硬”,與工會水火不容,不但激化了矛盾,而且給工廠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首鋼于2006年才最終結束了這項不堪回首的合作。而上汽集團自從2005年斥資5億美元收購韓國雙龍汽車以來,也遭遇了雙龍工會的挑戰。在工會罷工初期,上汽管理人員采取了單方面強硬態度,在裁員等實質性問題上并沒有與工會做充分溝通而采取了凍結工資、稅金等方式以牙還牙。這加劇了罷工的激烈性和雙方矛盾,從而使罷工造成的損失不斷擴大。后來,上汽集團改變了策略,邀請雙龍工會代表參觀上海總部以增加他們的信心,并與工會代表反復溝通交流,最終,雙方都做出了讓步并達成了協議。不過,在今年年初,韓國雙龍工會以“技術外泄”為名扣押中方技術人員,并到中國駐韓大使館示威,雙方的沖突又顯,看來上汽要徹底解決工會勞資問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也是諸多“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要修煉的基本功之一。
此番經濟危機激發了中國企業的并購熱情,尤其最近中國民企收購美國“悍馬”,更引發了國人的大討論。而對于尋求國際化的中國企業來說,國外勞資關系早已成為他們前行的一個重要障礙。對于要走進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中國公司來講,僅僅在資金、技術方面準備好是不夠的,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和東道國的工會打交道也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