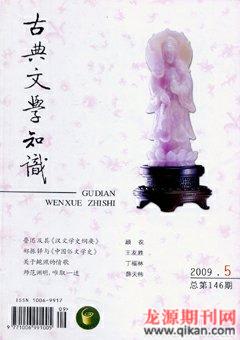有無(wú)之境
丁小明
唐代詩(shī)人白居易以李、楊故事為題材而創(chuàng)作的七言抒情歌行體長(zhǎng)詩(shī)《長(zhǎng)恨歌》,在中國(guó)古代詩(shī)歌史上閃耀著別樣的光彩。白居易這個(gè)高中“才識(shí)兼茂,明于體用”科的大才子,以他的緣情之筆,借李、楊情事寫(xiě)風(fēng)情之懷,為后世留下一首華美絢爛、婉轉(zhuǎn)多情而千古詠嘆的情愛(ài)悲歌。
可以說(shuō),自《長(zhǎng)恨歌》始,美贍的形制結(jié)構(gòu)與華美而感傷的氣調(diào)風(fēng)氣才成了七言歌行的正宗與本色。同時(shí),也正是這首傳詠千載的歌行長(zhǎng)詩(shī)在后人的接受理解下,引申出若干個(gè)帶有迷惘與困惑的問(wèn)題。特別是千余年來(lái)文人學(xué)者們對(duì)其猜測(cè)紛紛、聚訟不休的問(wèn)題——《長(zhǎng)恨歌》的創(chuàng)作主題是什么?可以說(shuō),探討《長(zhǎng)恨歌》的創(chuàng)作主題是個(gè)亦舊亦新的話題。說(shuō)它舊,是因?yàn)樽詮摹堕L(zhǎng)恨歌》問(wèn)世以來(lái)就有關(guān)于它主題的申明,白氏本人曾有“長(zhǎng)恨一篇有風(fēng)情”的詩(shī)句,盡管后人對(duì)于風(fēng)情的理解雖然差異較大,不過(guò)從他親自編輯集子時(shí)將《長(zhǎng)恨歌》歸入“感傷詩(shī)”一類(lèi)的做法,顯然是標(biāo)明與他集中的“諷喻詩(shī)”相區(qū)別的。與白居易同時(shí)的陳鴻在他所著的《長(zhǎng)恨歌傳》中也曾言及白氏的創(chuàng)作主題,他說(shuō):“意者,不但感其事,意欲懲尤物,窒亂階,垂于將來(lái)者也。”其持意顯然,為后世主“諷諭說(shuō)”之祖。說(shuō)它新,是因?yàn)殛P(guān)于其主題的探討就一直沒(méi)有停止過(guò)。除了與“諷諭說(shuō)”所見(jiàn)相同者外,俞平伯先生在20世紀(jì)20年代末提出“隱事說(shuō)”,褚斌杰先生在20世紀(jì)50年代后半期提出“愛(ài)情說(shuō)”。王運(yùn)熙先生提出調(diào)和“諷諭說(shuō)”與“愛(ài)情說(shuō)”兩者矛盾的“兩重主題說(shuō)”和由此引申而出的“多重主題說(shuō)”,以及出現(xiàn)較晚的“感傷主題說(shuō)”與黃永年先生在20世紀(jì)80年代中期提出的“無(wú)主題思┫胨怠薄*┆
由此可以看到,《長(zhǎng)恨歌》主題及其相關(guān)研究蔚為大觀。就《長(zhǎng)恨歌》主題之爭(zhēng)而言,其聚訟不休,竊以為其實(shí)是對(duì)其文學(xué)創(chuàng)作理解困境的標(biāo)志。而新的學(xué)術(shù)生長(zhǎng)點(diǎn)則在突破舊的思維范式之后才會(huì)產(chǎn)生。從新的視角來(lái)觀照《長(zhǎng)恨歌》,來(lái)理解白居易的創(chuàng)作,才可能使我們從舊的主題說(shuō)中突圍而出。
王國(guó)維先生在其著名文學(xué)評(píng)論著作《人間詞話》中有一段名言云:“有造境,有寫(xiě)境,此理想與寫(xiě)實(shí)兩派之所由分,然兩者頗難分別,因大詩(shī)人所造之境必合于自然,所寫(xiě)之境亦必鄰于理想故也。”以此段內(nèi)容來(lái)比對(duì)白居易的《長(zhǎng)恨歌》,我們就會(huì)發(fā)現(xiàn)他在傳世名著《長(zhǎng)恨歌》中為后人描寫(xiě)了兩個(gè)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者是所寫(xiě)境,再者是所造境。前者相對(duì)應(yīng)的是具有相對(duì)客觀性的開(kāi)元、天寶間這一特定的歷史時(shí)空與李、楊情事的梗概,白居易所寫(xiě)的是近于現(xiàn)實(shí)的存在之境。后者相對(duì)應(yīng)的是詩(shī)中楊玉環(huán)在馬嵬自盡之后民間傳說(shuō)中所幻出的一段李、楊雖陰陽(yáng)相隔而人鬼情未了的天地悲情。白居易所造的是近于想象的虛構(gòu)之境。
白居易所寫(xiě)與所造的這個(gè)悲歡兩重天的世界是如此鮮明,而得到愛(ài)情的歡喜與痛失愛(ài)侶的悲傷的對(duì)比又是如此的強(qiáng)烈。從來(lái)的研究者與讀者或多或少、或深或淺地會(huì)意識(shí)到它們的存在。可是研究者或執(zhí)著于其中的一個(gè)世界而求其主題,或?qū)烧吆?jiǎn)單疊加而不去體味文本內(nèi)外更深層的意蘊(yùn)。
我以為白居易在《長(zhǎng)恨歌》中所寫(xiě)與所造的兩個(gè)世界,是極其復(fù)雜深?yuàn)W的文學(xué)世界。這兩個(gè)世界是作者所構(gòu)造的、以情感感受為核心的知、情、意相結(jié)合的立體空間。這個(gè)立體空間中既有部分歷史之實(shí),又有更多創(chuàng)造之虛,是存在與烏有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完美結(jié)合。
具體來(lái)說(shuō),《長(zhǎng)恨歌》的兩個(gè)世界表達(dá)了三重意義上的有無(wú)之境。
第一重意義的有無(wú)之境,是從《長(zhǎng)恨歌》的內(nèi)容上看。《長(zhǎng)恨歌》的內(nèi)容可分為前后兩段,前半段從開(kāi)始到楊氏馬嵬自盡,是依據(jù)現(xiàn)實(shí)的所寫(xiě)之境,后半段從楊氏自盡到結(jié)局,是依據(jù)想象的所造之境。就主題爭(zhēng)論的“諷諭說(shuō)”與“愛(ài)情說(shuō)”兩大派而言,他們分別依據(jù)的是《長(zhǎng)恨歌》的前半段與后半段,由此各執(zhí)一端,聚訟不已。
第二重意義的有無(wú)之境,是就《長(zhǎng)恨歌》的前半段而言。上面之所以說(shuō)白居易所寫(xiě)境寫(xiě)的是近于現(xiàn)實(shí)的存在之境,而不是完全寫(xiě)實(shí)的秉筆直書(shū),是因?yàn)榘资显谠?shī)中的確有所不寫(xiě)。為何有所不寫(xiě),此處有兩層意義。第一層的意義正如王國(guó)維《人間詞話》所云:“大詩(shī)人所寫(xiě)之境必鄰于理想。”此理想為何物,自然不是作為史家的求真的理想,而是詩(shī)家構(gòu)造一個(gè)愛(ài)情故事的理想。為了這個(gè)理想,白居易自然會(huì)有所寫(xiě)與有所不寫(xiě),其不寫(xiě)處比如楊玉環(huán)曾為壽王妃,楊也曾幾次被李趕出內(nèi)宮,之所以不寫(xiě)是因?yàn)檫@些枝蔓之筆會(huì)影響白居易心中所要表達(dá)的李、楊?lèi)?ài)情故事,所以前半亦有一個(gè)有無(wú)之境,有者李、楊故事的原型,無(wú)者白氏心中之李、楊故事。所以,此處必須申明的是:再寫(xiě)實(shí)的敘事詩(shī)畢竟也是詩(shī),而不是記錄歷史的實(shí)錄。雖然這兩者在古代有時(shí)不易截然分清此疆彼域,有時(shí)詩(shī)歌確實(shí)能補(bǔ)歷史之缺失,但二者又畢竟是有著本質(zhì)區(qū)別的兩種東西,詩(shī)者求美,史者求真。從詩(shī)者之美中而執(zhí)著以求史之真,多半是因?yàn)榭床磺灏拙右姿鶎?xiě)之境中只是近于現(xiàn)實(shí),是有所寫(xiě)與有所不寫(xiě)的。進(jìn)而得出《長(zhǎng)恨歌》是以史實(shí)為依據(jù)、以諷諭為主旨,批評(píng)唐明皇的重色誤國(guó),導(dǎo)致安史之亂,借李、楊故事提醒后世的統(tǒng)治者應(yīng)躬親朝政,勵(lì)精圖治,不要重蹈舊轍,再釀禍端的結(jié)論。在“詩(shī)載道”的理念下屏蔽了“詩(shī)緣情”眼睛,這可能是“諷諭說(shuō)”的最大不足之處。更有甚者,試圖以詩(shī)來(lái)還原真實(shí)的李、楊之事,試圖把《長(zhǎng)恨歌》的研究還原成一種史學(xué)研究。所以一些史學(xué)家的興趣自然會(huì)集中在與《長(zhǎng)恨歌》有關(guān)的史實(shí)世界中。他們非但不理會(huì)《長(zhǎng)恨歌》后半部分所構(gòu)造的“空中樓閣”——《長(zhǎng)恨歌》中的陰陽(yáng)相通的理想世界,相反他們的工作主要是要拆除這個(gè)空中樓閣,把它還原成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的一磚一瓦。比如歷史學(xué)家陳寅恪先生與黃永年先生曾先后發(fā)表了關(guān)于《長(zhǎng)恨歌》研究的論文,雖然兩者最后得出《長(zhǎng)恨歌》的主題有異,陳主諷諭說(shuō),黃提出無(wú)主題說(shuō),但兩者“以史證詩(shī)”的方法是一致的,兩者都以杜甫的“詩(shī)史”觀來(lái)比對(duì)《長(zhǎng)恨歌》的創(chuàng)作,借《長(zhǎng)恨歌》的酒杯,澆唐史研究之塊壘。這樣的做法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是考據(jù)派的研究者往往執(zhí)著于李、楊故事之有者,去指正白居易所說(shuō)李、楊故事之無(wú)者,其弊端是執(zhí)詩(shī)美以求史真,其實(shí)還是不理解詩(shī)、史之別,不理解所寫(xiě)之境必鄰于理想的意思。由此也可以看出,方法的失誤往往會(huì)導(dǎo)致學(xué)術(shù)研究的誤操作。“以史證詩(shī)”可以作為文學(xué)研究的輔助方法,但不應(yīng)是主導(dǎo)和基本方法。
第三重意義上的有無(wú)之境,是就詩(shī)的后半段而言。《長(zhǎng)恨歌》中的故事在上半段沿著天寶史實(shí)的跑道滑行了一段距離之后,就離開(kāi)事實(shí)的地平面起飛了。從歷史的事實(shí)來(lái)看,其后半段所云李、楊陰陽(yáng)相通之事顯然屬于子虛烏有。但這樣的文學(xué)虛構(gòu)是否就是完全的虛無(wú)之思,蹈空之筆呢?細(xì)細(xì)品味,也不盡然。
正如王國(guó)維在《人間詞話》中所云:“大詩(shī)人所造之境必近于自然。”大詩(shī)人所造之境為何能必近于自然,我們可以用白居易在《長(zhǎng)恨歌》中的創(chuàng)作來(lái)加以說(shuō)明。首先陳鴻的《長(zhǎng)恨歌傳》曾言及《長(zhǎng)恨歌》的緣起:“元和年冬十二月,太原白居易尉于盩厔,予與瑯邪王質(zhì)夫家仙游谷,因暇日攜手入山,質(zhì)夫于道中語(yǔ)及于是。白樂(lè)天,深于思者也,有出世之才,以為往事多情而感人也深,故為《長(zhǎng)恨詞》以歌之,使鴻傳焉。世所隱者,鴻非史官,不知;所知者,有《玄宗內(nèi)傳》今在。予所據(jù),王質(zhì)夫說(shuō)之爾。”從陳的后序中可以知道,陳鴻與白居易分別以詩(shī)與文的形式來(lái)寫(xiě)李、楊故事,其題材提供者是王質(zhì)夫,而王質(zhì)夫當(dāng)時(shí)為隱居仙游谷的道人。李健章與張中宇兩位先生在他們的論文中提出,王質(zhì)夫與白居易、陳鴻所“話及此事”,絕不是僅僅提及簡(jiǎn)單的唐玄宗、楊貴妃故事。當(dāng)時(shí)生活在盩厔一帶的王質(zhì)夫很可能綜合了當(dāng)?shù)卮罅控S富的民間傳說(shuō),向白居易、陳鴻提供了相當(dāng)完整、細(xì)致的故事情節(jié)和細(xì)節(jié),包括仙界傳說(shuō)等,為白居易、陳鴻創(chuàng)作《長(zhǎng)恨歌》及《長(zhǎng)恨歌傳》提供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在由民間素材、史實(shí)到文人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橋梁”作用。由此可見(jiàn),《長(zhǎng)恨歌》后半段李、楊的陰陽(yáng)相通之事仍是當(dāng)時(shí)的民間傳說(shuō),從李、楊故事演變的過(guò)程來(lái)說(shuō),是實(shí)有之事,并非白氏向壁虛造,只不過(guò)此段情節(jié)在白居易的筆下更加凄婉感人。此為后半段第一個(gè)層面的有無(wú)之境。
- 古典文學(xué)知識(shí)的其它文章
- 也說(shuō)花木蘭為什么姓花
- 古代文人年齡的秘密
- 祝禱類(lèi)文體
- 師范淵明,唯取一適
- 真情真性 率爾自然
- 手抄本《袁枚日記》(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