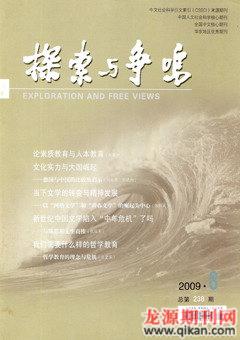孫中山與宋嘉樹首次接觸考辨
沈渭濱
內容摘要孫中山與宋嘉樹首次接觸于何時?居間介紹人是誰?接觸的地點在哪里?這些都是研究孫中山與宋嘉樹關系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經過考辨,1892年宋嘉樹在陸皓東陪同下,在香港和孫中山首次接觸,奠定了孫宋日后關系的基礎。
關鍵詞孫中山宋嘉樹陸皓東香港
孫中山與宋嘉樹,既是志同道合、終身不渝的革命同志,又是結秦晉之好的翁婿。孫宋關系是辛亥革命史、宋氏家族史研究的重要篇章。其中,孫宋的首次接觸,不僅奠定了孫宋關系的基礎,而且對宋氏家族的爾后影響和發展至關重大。以往由于資料限制,對此研究很不充分。本文擬在現有史料基礎上加以梳理,試作分析。
孫中山和宋嘉樹的第一次接觸始于何時?至今仍撲朔迷離。一般都認為是1894年孫中山偕陸皓東北上天津上書李鴻章時,途經上海留寓于宋宅,是兩個人的首次會面。但是這一說法有以下幾點難以解釋:一、孫、宋人分南北、地隔千里,在素無謀面的情況下,孫中山怎么會貿然下榻于宋家?二、宋嘉樹為什么在毫無思想交流、不知對方思想底細的情況下,能在自己家里接納孫中山?三、兩個人為什么在相處中能一見如故,如此投緣地暢談?由此可知,1894年之說有很多難以說通的疑點。從情理上分析,只能在雙方相互了解、溝通的情況下,才會有下榻宋家之舉。所以斷定兩人首次接觸于1894年,不合情理。
其實,根據孫中山自述,兩人的第一次接觸,是在1892年。這是孫中山于1912年4月17日致友人李曉生信中提到的。原文如下:“曉生兄:宋君嘉樹者,二十年前曾與陸烈士皓東及弟初談革命者,二十年來始終不變,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結果,此公不無力。然彼從事于教會及實業,而隱則傳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隱君子也。弟今解職來上海,得再見故人,不禁感慨當年與陸皓東三人屢作終夕之談。今宋君堅留弟住其家以話舊,亦得以追思陸皓東之事也……弟孫文謹啟,即晚。”
這是一件研究孫、宋關系的重要史料,也是出自孫中山手書的第一手資料。信寫于1912年4月,所稱“二十年前”,上推應是1892年,又日“初革命者”,當屬首次接觸之談,但信中沒有提及接觸的地點在哪里。信中對宋嘉樹在上海辛亥革命中的貢獻作了很高評價,并指出宋是以“從事教會及實業”的公開身份,“隱則傳革命之道”的“隱君子”,是“不求知于世”的低調者。這樣一份重要資料,沒有引起研究孫宋關系的學者重視,只有少數人有所注意,實在是很遺憾。
現在沒有史料可以說明宋嘉樹為什么在1892年會和孫中山有所接觸。比較合理的解釋,一是雙方都是基督徒,宗教救世的信仰,促使他們走到了一起。孫中山早年在檀香山就讀于意奧蘭尼學校(Iolani Sch001)時,就已被基督教教義所吸引,如果不是因為哥哥孫眉的反對,他將接受洗禮。1883年,終于在香港和陸皓東等,由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喜嘉理(charles R,Hager)牧師施洗,成了一名基督徒。1884--1885年,孫中山在香港中央書院讀書時,曾一度想做個宗教救世的傳教士。喜嘉理牧師對此有詳細記述。他說孫中山的傳教之志極為堅決,“向使當日香港或附近之地,設有完善之神學院,俾得人院授以相當之課程,更有人出資為之補助,則孫中山先生者,殆必為當代著名之宣老師矣。”在未能遂愿的情況下,轉而學醫,因為“醫亦救人苦難術”,符合當時孫中山的理想。
宋嘉樹出身于海南文昌一戶貧困的農家。1875年被舅父帶領離鄉,遠涉重洋到了美國。此行雖比孫中山1878年檀香山早了三年,但有趣的是兩人離鄉時,同是12歲的少年。宋到美國波士頓不久,即被送到古巴哈瓦那一家絲茶行當了兩年學徒,這又與孫中山剛到夏威夷時,在哥哥孫眉開設的店鋪做小伙計的經歷相類。1877年宋嘉樹回到波士頓,在舅父的絲茶行里干活。舅父正式收他作為養子。他想讀書,卻遭到養父拒絕。倔強的他,逃到美國海岸警衛隊緝私船上做了侍童。后來幾經轉移,于1880年接受了美國監理會宗教洗禮,皈依基督教。成了—名虔誠的教徒。最后,又本著宗教救世的精神到上海傳教。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和宋嘉樹不僅早年有著大略相同的經歷,而且兩人都是基督教新教的信徒。新教是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的產物,雖然宗派繁多,但它的基本教義較之以教皇為絕對權威的天主教會那種墨守舊章、思想陳舊者迥然不同,屬于革新和進步的宗教組織,在當時反對封建專制制度中起過重要作用。其中,反對教皇對各國教會的強權控制;反對教會擁有地產;反對教會享有解釋《圣經》教義的絕對權威,而以《圣經》為信仰的最高準則;強調教徒直接與上帝相通,無須由神父作中介等,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民主自由的傾向。雖然隨著時間推移,教義在各宗派的宗教傳播中有所變化和交叉,但新教上述原教旨精神仍大體相承,基本不變。正是因為宗教旨趣相同,成了促使孫、宋相聚的首決條件。
二是兩人都有改良祖國、拯救同群的共志。孫中山在檀香山讀書期間,不僅被基督教教義所吸引,而且深受夏威夷人民反美斗爭的感染,生發出救世濟人、關懷祖國命運的崇高之想。后來,他在一次演說中說:“憶吾幼年,從學村塾,僅識之無。不數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于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祖國,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當時所懷,一若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后快者。”
但是究竟如何“改良祖國”,用什么手段去“拯救同群”,孫中山還不甚了了。1883年他到香港求學,不久就經歷了中法戰爭的刺激。他受到香港愛國同胞抗議法國侵略的正義行動感染,看到清政府簽訂和約的可恥結局,思想產生了質的飛躍。他覺得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實在是中國積弱落后的根源,非除去不可,于是“決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應時而生。他曾不止一次地說過:“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余自乙酉中法戰后始,有志于革命”。“決覆清廷”,標志著孫中山原先“改良祖國,拯救同群”的理想由朦朧變得清晰,即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才能達到目的,至于“創建民國”,那要到后來參加反清革命的實踐時,才有對未來新政府模式作理性思考。撇開兩者時序上的先后,1885年后,孫中山成了一個反清革命論者是無可置疑的,他的政治覺醒時代已經到來。所以,從1887--1892年就讀于香港西醫書院即雅麗氏醫學院時,他和同學好友課余暢談反滿,放言無忌,被時人目為“四大寇”。用孫中山自己的話說,這四年的大學時代,是他的“革命言論時代”。
宋嘉樹雖然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但也是個關懷祖國命運、渴望國家富強的熱血青年。他早年生活過一段時間的波士頓,有著抗擊英國殖民統治的光榮傳統,被譽為美國革命的搖籃、獨立自由的象征。正是在波士頓革命歷史和林肯獨立精神的感召下,宋嘉樹第一次萌生了希望“國家獨立,民族革命”的朦朧意識,產生了“中國應該學習美國”的想法。從此,他一直心系祖國,有著強烈的愛國情
緒。1881年,宋嘉樹進入美國“圣三一學院”(TrinityCollege)(后來的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讀書,據《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傳》一書所記:有一個參加過1884年歐洲革命,自稱“革命軍上士伊連”的老人,向宋嘉樹介紹歐洲革命時,宋馬上聯想到中國,向他請教“中國應該怎樣革命”。1884年中法戰爭時,宋嘉樹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聽到有人發表鼓動法軍侵華演說時,立即提出抗議,責問演講者:“先生,你不感到羞恥嗎?如果你是弱者,是受侵略者,你被強者欺凌,被侵略者蹂躪,也會這樣手舞足蹈,引以為榮嗎?”法國“像當年兇殘的不列顛人侵略北美一樣,蠻不講理地侵略中國。他們這樣傷天害理、不顧廉恥、不怕輿論譴責,難道也是誦讀《圣經》的教徒,也是信奉上帝的兒女” ?義憤之下,宋嘉樹自制了一塊標語木板,上寫:“請捐款給遭受野蠻侵略的中國”。他對那些反對者說:“上帝給我的神圣使命,就是喚醒他們,激勵他們,幫助他們,指導他們。落后、愚昧、黑暗都是暫時的。強大的中國一定會誕生,到那時誰都不敢碰她!”上引宋嘉樹的這些話,由于作者都沒有注明資料來源,而且全書帶有明顯的文學描寫色彩,不足作為可靠史料予以采信。但考慮到作者原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史學工作者,自稱寫作本書前曾廣泛查閱了國內外各種報刊、檔案,力所能及地訪問了宋家親友并加以考訂核實。所以雖不可盡信,但相信不是杜撰。筆者在宋嘉樹早年資料奇缺的情況下,不得已錄而用之,借以勾勒出宋嘉樹早年思想的大體脈絡。通過上述話語的語境,說明這個根植于祖國的青年基督徒,也是一個關懷國家命運,渴望祖國富強的愛國者。如果這一判斷不錯,那么1892年兩人首次接觸,就有了大體相同的思想基礎和共同語言,如此才能出現如孫中山所說的“屢作終夕之談”之事。
在解釋了1892年宋嘉樹和孫中山首次接觸的思想基礎之后,存下的問題就是兩人接觸的居間撮合人是誰,在什么地方接觸?
撮合人毫無疑問應是陸皓東。陸皓東,名中桂,號皓東,廣東香山(今中山市)人,是孫中山的同鄉和村塾學友。兩人關系親密,都有改革弊政和改良鄉政的愿望。1883年7月,陸曾協同孫中山搗毀村中北極神廟偶像,為村民所不容,與孫中山同時離村去香港。年底,偕孫中山在香港同時接受喜嘉理牧師的洗禮,加入基督教。1884年到上海,人電報學堂學習。
上海電報學堂創立于1882年,是一所培養電報專業人才的中等技術學校。校址初在胡家宅會香里(今福州路西藏中路東南轉角處),后移到鄭家木橋(今福建中路)上海電報總局內。學生最初僅20人,主要學習收發報技術,學制不定。學優者派至上海電報總局任職,缺額陸續考補。后因急需電報人才,學堂規模擴大,先后添設測量塾、按報塾、額外塾。1910年與上海電報高等學堂合并,移至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陸皓東1884年入校學習時,學堂創辦不久,學了幾年,何時畢業,史無明文,只知畢業后派至上海電報總局充領班生。
宋嘉樹于1890年由“巡行傳道”轉為“本處傳道”后,在上海定居下來,住在虹口美租界朱家木橋(今虹口東余杭路)一帶岳父家里。其間,執教于慕爾堂的主日學校,并熱心組織“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等。
現在沒有確切資料說明陸皓東何時結識宋嘉樹。值得注意的是宋嘉樹執教的慕爾堂主日學校,恰與陸皓東供職的上海電報總局,同在鄭家木橋一帶。慕爾堂建于1874年,原為紀念美國堪薩斯州基督徒慕爾死去的8歲女兒,由當地信徒捐款,在上海建立的教堂。不久,“圣三一堂”并入,成為基督新教美國監理會在上海差會的重點教堂之一。陸皓東既是新教信徒,慕爾堂又在上海電報總局附近,他要做禮拜,很可能就在慕爾堂。那么,與執教于該堂主日學校的宋嘉樹相遇相識,并非沒有可能。這雖是推測,但合乎情理。由于兩人志趣相投,成為互可信賴的朋友。據說,陸皓東成了宋家的座上客,兩人在客廳里經常長時間晤談,主題總是圍繞著怎樣才能使中國盡快富強和如何結成中國的“自由之子”社展開。時間是在1890年宋嘉樹在虹口東有恒路建了宅第后,不過,宋何時建私宅,至今還未查明,這一說法不足以定論。但陸、宋相識交往,至遲不會遲于1892年。比較肯定的應是1890年宋嘉樹在上海定居后,到1892年陸皓東偕宋嘉樹南下和孫中山接觸之前。陸、宋交往過程中,陸皓東勢必會向宋嘉樹談到同鄉好友孫中山,激起了宋嘉樹想一見孫中山的欲望。如日本志士宮崎寅藏在1895年從陳少白處獲知孫中山革命志向后,急著要會見孫中山那樣。可以說,孫中山的思想和人格魅力,是他凝聚同志和朋友的磁力場。
陸皓東與宋嘉樹之所以選在1892年南下,沒有具體作證的史料,但可以從若干蛛絲螞跡中尋繹出比較合理的解析。據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被捕后陸皓東自撰供詞:“吾姓陸名中桂,號皓東,香山翠微鄉人,年二十九歲,向居外處,今始返粵……居滬多年,碌碌無所就,乃由滬返粵,恰遇孫君,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標,孫則主滿仇必報,思治其本,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為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這段供詞,值得注意者,一是陸皓東因自覺在滬碌碌無所就,乃由上海離職返粵;二是訪孫中山于客寓,暢談竟夕;三是雙方經“連日辯駁”后確立宗旨,成為兩人“倡行排滿之始”。根據第三點“倡行排滿之始”,可以推知兩人暢談必不在“今始返粵”的1895年,而應在此之前。若以孫中山回憶作證,兩人暢談革命排滿的時間,即陸皓東由滬返粵,至遲當在1892年。孫中山在《有志競成》一文中,回憶他在香港西醫書院求學時期(1886---1892)倡言革命時的情況說:“數年之間,每于學課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來于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和者,在香港只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
文中提及“上海歸客”陸皓東,證明陸并非如其供詞所稱,在1895年“今始返粵”,“恰遇孫君”,早在1892年前就已從上海回到廣東,并去香港孫中山寓居的楊耀記店鋪樓上,與孫中山、尤列、陳少白、楊鶴齡“四大寇”暢談革命。這就是陸皓東所說“客寓過訪,遠別故人,風雨連床,暢談竟夕”的真實歷史背景。他故意把時間延后到舉行廣州起義的1895年,顯然是為了保護尤列、陳少白、楊鶴齡等革命同志。
既然陸皓東與孫中山暢談反滿革命應發生在孫中山就讀大學期間,那么何以遽斷在1892年呢?根據就是前揭孫中山致李曉生信中稱:“宋君嘉樹者,二十年前曾與陸烈士皓東及弟初談革命者。”“二十年前”是一個明確的時間限定語,不是一個模糊的約數。在沒有其他資料可以證明其他時間的情況下,不應作為約數來解讀。如果認定宋嘉樹是在陸皓東居間介紹下與孫中山首次會面,那么,根據陸皓東供詞和孫中山致李曉生信以及孫中山自撰的《有志竟成》相互印證,可以肯定,孫、宋、陸三人“初
談革命”的時間是1892年。
孫中山、宋嘉樹、陸皓東三人首次相聚、“初談革命”的地點在哪里?有一種說法是在廣州。日本學者久保田博子在其論文《關于宋慶齡與孫中山的結合——兼論宋慶齡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中稱:“1892年陸皓東由上海到廣州,與孫文等革命同志有過來往。……宋嘉樹去廣東,通過陸皓東與孫文聯系是有可能。”應該說這個推論有一定程度的可能性。因為,據孫中山大學同學江英華回憶:1892年孫中山在西醫書院畢業后,曾經香港總督羅便臣通過英國駐華公使,向北洋大臣李鴻章推薦孫中山與江英華兩人“學識優良,能耐勞若,請予任用”。李鴻章同意兩人來京候缺。孫中山偕江英華在業師康德黎陪同下到廣州向兩廣總督衙門申請領牌,然后晉京。此事雖然未能實現,但孫中山確實到過廣州。那么孫中山在廣州恰遇陸皓東、宋嘉樹的機緣,不能說沒有可能。
但是,廣州是清政府管轄的華南重鎮,禁錮森嚴,緹騎密布,要在廣州暢談反清排滿革命,而且“屢作終夕之談”,畢竟危險太大,尤其在孫中山、江英華去廣州是為了向兩廣總督申領牌照,以便晉京就職的境遇下,與陸皓東、宋嘉樹在“客寓過訪”、“暢談競夕”,似乎不合情理。因此在廣州相聚的可能性不大。
相比之下,三人相聚很有可能是在香港。理由如下:
其一,1892年中外關系相對平靜。香港是英國殖民當局管轄之地,清政府權力所不逮,言論較內地相對自由,人員往來聚合,亦不易引人注目。這是天時、地利方面的條件。
其二,孫中山自1883年到港,至1892年大學畢業,居香港幾近十年,人際關系網絡早已形成,結交者除同學、同志外,舉凡學界如業師康德黎等,商界如輔仁文學社楊衢云等,政界如香港議員何啟等,宗教界如區鳳墀牧師等,在在皆是,比之廣州人生地不熟要優越得多。接待朋友,高談闊論,自在情理之中。這是人和方面的條件。
其三,大學時代,孫中山自稱是其“革命言論時代”,所談、所懷、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說明他與志同道合的學友間相互砥礪、盡情鼓吹,已經到了“無所忌諱”的階段,他的反滿志向已經堅定不移了。陸皓東作為“上海歸客”,宋嘉樹作為陸皓東的朋友,在香港參與倡言,正是躬逢其時。這是相聚的最佳機遇。所以才有《供辭》所云:“風雨連床,暢談競夕”,“連日辯駁,宗旨遂定,此為孫君與吾倡行排滿之始”,也使孫中山念念不忘,以致20年后仍使他“不禁感慨當年與陸皓東三人屢作終夕之談”。可知1892年在香港,孫中山、宋嘉樹、陸皓東三人“初談革命”,對孫中山印象之深。
從以上天時、地利、人和、機遇幾方面分析,筆者認為,孫中山、宋嘉樹在陸皓東居間介紹下首次相聚的地點,極有可能在香港。具體說,極有可能在香港楊耀記店鋪樓上孫中山下榻之處。這個地方,不僅是孫中山大學讀書時代常與陳少白、尤列、楊鶴齡倡言排滿,大放厥詞之所,而且也是他畢業后懸壺澳門時,仍下榻于此的寄寓所在。
還有一個問題,宋嘉樹為什么在1892年隨陸皓東南下香港?據上文分析,除了他早已渴望國家富強、改良祖國的一腔熱忱,通過陸皓東介紹,想見孫中山的愿望外,一是陸皓東恰巧在當年離職返粵,與陸同行,得以面見孫中山自在情理之中;二是宋嘉樹或許另有需要,借此機會與陸南下,顯得更加自然。“或許另有需要”,是指他為籌辦印刷廠,需要訂購有關設備之事。
眾所周知,宋嘉樹自1890年改為“本處傳道”后,便在上海定居。不久在虹口東有恒路(今東余杭路)購地建房,并在自家地下室創辦印刷所,為上海美華圣經會代印《圣經》。宋氏新宅建于何年,本文上述第二節已經說明至今尚未查明,宋嘉樹何年在其家地下室辦印刷廠也沒有確切記載。這對宋氏早期經歷的研究帶來很大困難,但也留給后人一個思考探索的空間。據宋嘉樹在美國范德比爾特神學院就讀時的同學和摯友步威廉(William Burke)的兒子詹姆斯·伯克所著/(我的父親在中國》一書所記,1896年,宋嘉樹“在虹口新居接待步威廉”,可知宋氏虹口新居,至遲在1896年已經落成。在此之前(即1890年在“本處傳道”后)應該住在岳父倪蘊山的家里。倪蘊山于1889年已經去世,倪府成了宋嘉樹及其妻子倪桂珍(倪家長女)、倪桂珍妹妹倪桂金和夫婿牛尚周共同居住處。按照長幼次序的傳統,把1890年至宋氏新宅落成前的倪府,說成宋嘉樹家,也無不可。這樣,所謂“在自家地下室里開辦小型印刷廠”一語,就成了一個模糊而不確定的說法,它既可以指新建宋宅里的地下室,也可以理解為1890后宋嘉樹夫婦居住的倪府。
在上海定居兩年后的宋嘉樹,深感執教于慕爾堂主日學校及服務于上海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的薪金微薄,又得到上海美華圣經會委托代印《圣經》的機緣,決定開設小型印刷廠。辦印刷廠需要機器,因為傳統的木板刻印,既不合委托方印制《圣經》的要求,又需要人力、資金投入,顯然勢不可行。傳統的石印技術,雖然資金投入不多,但不合委托方要求。美華圣經會印刷的《圣經》都是鉛印本。于是只有購置印刷器械才能實現辦廠目標。可是19世紀末,上海還沒有制造印刷器械的工業企業。當時,所有教會開辦的印刷出版機構如墨海書館、美華書館、土山灣印書館、益智書會、同文書館等使用的鉛字印刷機,都購自外洋。宋嘉樹要辦廠印制《圣經》,只能向國外訂購器械。香港是內地與海外溝通的要地,許多外國企業都有分支機構在此辦理業務。宋嘉樹在結識陸皓東之后,既欲一見孫中山,又得知陸皓東有離職南下的企圖,加上原有去香港訂購印刷器械的需要,于是欣然與陸皓東結伴南下了。筆者的這一分析,雖然沒有具體史料佐證,純屬推理,但由于存在無可否認的前提,即1892年他與孫中山、陸皓東首次相聚以及宋嘉樹曾在自家地下室辦小型印刷廠印制《圣經》的史實,這樣推理,也就合乎邏輯了。歷史研究在沒有確切史料,一片空白的前提下,只要有確切無誤的前提,是可以也允許進行合理推論、分析,得出結論的。這個結論,雖有待日后發現的新資料作檢驗,但它不失為試圖解析疑團的一種方法。這就是所謂形式邏輯與歷史邏輯的統一。
綜合上述分析、論證,可知1892年宋嘉樹在陸皓東陪同下,在香港與孫中山首次相聚,暢談革命,給孫中山留下了深刻印象。孫、宋首次交往,奠定了日后革命同志和親密戰友的堅實基礎。從此,宋嘉樹在“從事教會及實業”的掩護下,“隱則傳革命之道”,成為一個對上海辛亥革命作出貢獻而很少為世人所知的革命“隱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