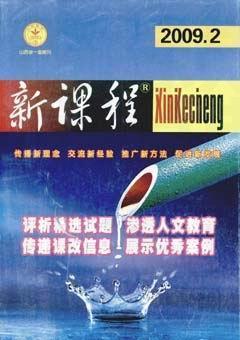“流行文化”與語文教學之我見
羅伯真
“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語文學習的外延與生活的外延相等”,在實施素質教育中,相信大多數語文教師對“大語文”觀念會達成共識。然而一旦回到現實,看到學生抄流行歌曲,看漫畫卡通,讀武俠言情等,不少老師的反應也許不僅僅是憂心忡忡,甚至于要氣急敗壞,一查二禁三收了。恐怕在我們的“詞典”里,所謂大語文、素質培養,更多的是與經典的主流文化相聯系,而不包括通常所說的這些“流行文化”。那么,在我們的語文教學中,是否應該絕對擯除這些“流行”的作品呢?
我看大可不必視其如洪水猛獸。學生沒有進入我們所期待的閱讀范圍,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從學生主觀內在的因素來看,年輕的他們理解力、鑒賞力一般相對不高,使得這些流行文化作品的介入也成為了一種自然或必然。雖然那些中外文化經典具有穿透歷史、現實和未來的深邃,更有描摹形象千姿百態、刻畫人性鞭辟入里的精細微妙,但對于涉世未深、閱歷尚淺的青少年學生來說,要讀懂、領略歌德六十年著就的《浮士德》的內蘊,曹雪芹“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中的哀思,無疑是面對一座座令人卻步的高山。經典這種高度往往使年輕學子的心跡難以與名作的軌跡熨帖一體,甚至讓他們望而生畏。經典是高雅的,它嚴肅、博大、精深;而流行卻是通俗的,它親切、好懂、貼近,單從一種親和、平視的閱讀角度來看,青少年學生閱讀選擇中的天平傾斜,也是情有可原的。
再進一步從客觀的社會背景來考察,學生也是社會的人,他們生活在信息爆炸的社會,每天面對現代化媒介,每時每刻都從各種渠道獲得信息,當然也包括著不可抗拒的流行文化,它們從不同方面影響著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學科課程實施,這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實。更何況我們的學生天天生活在為成績、為升學而心力交瘁的社會文化環境里,他們深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無奈”,于是,在時間緊、壓力重的現實下,一些學生只能偷得片刻,使“煎烤”的大腦、身心得以暫時放松,結果是讀不太費勁的卡通漫畫、言情武俠就成了流行選擇。由此看來,語文教學要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要與時俱進,就不能不顧及社會文化這個背景。任何將語文課堂、課業內容與時代、與社會對峙或間隔的語文教學,都是缺乏活氣、靈氣,沒有現實生命力的,亦往往是低效的,從這個意義講,教師應努力讓學生的各種生活閱歷,包括所涉足的流行文化,成為語文教學的幫手,而不是對手。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不把流行的作品一律拒之門外,把閱讀之門開得更大一些,未必不利于語文的教和學。從現代課程論來看,流行文化作為語文課程中的“潛在課程”,是語文課程的一個重要方面,不管你有意編制還是無意觀照,實際上它已大踏步地“顯性”在語文課程之中,參與發揮語文教學的功能與效率,并影響到學習主體的發展。事實上,金庸的作品入選高中教科書,周杰倫歌曲中體現的“中國風”,甚至三毛、瓊瑤作品中理想主人公的至善至美以及筆墨的精細生動等,對學生欣賞心理的滿足,一定程度上語言的熏陶和情操的感染,其反應未必是消極的。可以說,流行中不乏精品,無論從語言技巧的滋潤,還是人文精神的熏陶來說,流行作品對語文教學產生的作用的確不該漠視。
“流行文化”作為一種客觀存在,作為教學內容的參照,作為教學的認知、情感、心理的背景,作為傳播歷史知識、文化常識和文化精神的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小小的課堂,延伸了短短的四十五分鐘,特別是為薄薄的教材文本注入了時代氣息。并且語文課程的特性也決定了學生主體性活動中自身經驗的重要。哪怕僅是閱讀流行、時尚作品而產生的體驗、感悟、陶冶、浸染、默化等,也將可能有助于開拓學科視野,有助于教出的學生不再是“標準化”的書呆子,而是與社會有著密切聯系的“現代”的人,引起學習者在語文認知、語文應用、人格塑造、價值觀等方面的積極變化。由此可見,語文教學不能囿于教科書中,更不能絕對框死在“大一統”中,應該開放門戶,允許社會流行文化,特別是其中比較“經典”或“熱點”的流行作品介入。
誠然,像任何事物一樣,流行文化中的確有消極、負面、糟粕的東西,而且不乏粗制濫造、趨時媚俗、格調低下之類。但既然生活不是平靜的滿面春風,你又怎么能要求我們的學生在“安全無憂”的真空里生活呢?總不能因噎廢食吧!要知道人為的真空是絕對培養不出你所期待的免疫力的。我們語文教師的責任恐怕決不在于“堵”,而只在于“疏”。
當然,本文所述的目的,并非為大讀卡通、武俠、言情之類推波助瀾,也絕非冷落博大精深的高雅經典之作。我所謂“把門開得更大一些”,是希望在我們的語文教學中,能允許并引導學生:海納百川,多元接受,不要一葉障目,不見森林;讓學生在豐富的閱讀思考的實踐中,分清雅俗優劣,鍛煉辨析能力,提高鑒賞水平,深植人文底蘊。正如魏征所說:“求木之長者,必先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先浚其泉源。”本固源通,才能木長流遠,這才是最最關鍵的。
作者單位:河北省衡水市職業技術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