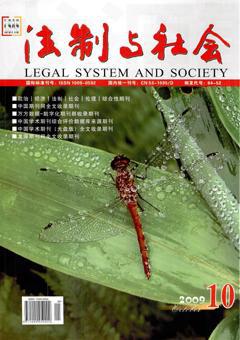論債權人代位權行使的效果
單廬輝
摘要債權人代位權制度作為債的保全措施之一,在我國已經歷了一段時期的發展與完善,經過理論和實踐的不斷深入,對于該制度的設計與完善亦不斷進行著。特別是行使代位權的效果歸屬方面,我國否認了傳統的“入庫規則說”,使得這一制度完全脫離原有債的保全軌跡,沿著債的實現方向前進。本文將通過論述債權人代位權行使的效果提出完善代位權的建議。
關鍵詞債權人代位權 行使效果 入庫規則
中圖分類號:D92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09)10-093-02
一、“入庫規則”的概述
依傳統的債權人代位權法理,代位權行使的效果,直接地歸屬于債務人;即使在債權人受領交付場合,也須作為對債務人(次債務人的債權人)的清償,而不能將它作為對債權人自己債權的清償。對于這種將行使代位權取得的財產先加入債務人責任財產的做法,即為“入庫規則”。也就是說,代位權實行的效果,并不是為了滿足債權的實現,而是準備債權的實現,因而,有學者把它稱之為強制執行的預備功能。由此,當代位債權人在保持住債務人財產后,他自己不能立即接受清償,而應把行使代位權訴訟所取得的財產先“入庫”,即歸屬于債務人,然后,再從債務人那里向債權人進行平等清償,這就是債權人代位權實行效果上的“入庫規則”。事實上,把債權人代位權稱之為強制執行的預備功能,是真實的,但不夠全面。因為從債權實現的角度講,通過代位權制度的傳統功能,債權人從債務人那里得到債權滿足的方式有三,即破產制度、債務人任意清償和強制執行。也就是說,代位權制度只有結合破產程序或任意清償或強制執行才能達到債權實現。從終級意義上講,代位權制度在于債權實現,但是,由于“入庫規則”的遮蔽,我們總感覺到代位權的終端即是“入庫”。
對“入庫規則”的解讀會發現,“入庫規則”始終堅持了這樣一個原則,即:債權人代位權制度雖然是為了讓債權人保全自己的債權,卻并非是自己債權的直接滿足,而是一種對作為全體債權人共同擔保的債務人的責任財產進行保全的制度(即共同擔保的保全),債權人代位權是要通過這種“共同擔保的保全”來實現債權人“自己債權的保全”。由于債權人代位行使的權利歸屬于債務人,其結果自然直接歸屬于債務人,成為對全體債權人的共同擔保,代位債權人并不因代位而取得直接受償權,只不過是與其它的債權人平等受償。若往前探究,則是各債權一律平等,而這是私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具體展現。從利益共享和損失分擔來講,既然各債權一律平等,當然要平等地共享利益和分擔損失。若允許代位債權人優先受償,意味著代位債權人之債權優于其它債權人之債權。由于民事實體法并無創設代位權具有優先普通債權的規定,同時在我國司法中,代位權的行使只允許以訴訟或仲裁的方式行使,這就意味著,通過訴訟或仲裁,代位權人取得了優先于其它債權人的債權(以下簡稱優先權)。為什么會產生這種優先權呢?很明顯,是債權人行使代位權之故,因而,可以得出程序已創造了實體法并未創設的優先權這一結論,也就是說,程序法在此也進行了“代位”,它代位實體法創設了實體法“怠于”創設的實體權利__優先權。當然這不是我們的創造,而是程序法學者的創意。若更換一個視角,拋開程序和實體的認定,從法理的角度講,“入庫規則”的平等觀念即是,不管各債權人在保全債務人財產時付出努力之多寡,一概從結果上進行認定,即債權人在收取自己債權時一律平等。可以說,這種平等是結果上的平等,是一種終局意義上的平等,不是機會的平等。
二、債權代位權行使效果在我國的立法歷程
在我國立法上,對債權代位權行使效果的規定,并非一路坦途。自開始統一合同法的起草研究以來,對代位權實行效果規則的采納,可謂幾多曲折。學者起草的《合同法》(建議草案)第72條第3款規定:代位權行使的效果歸于債務人。《合同法》(草案第四稿)第50條第二款也曾規定這一規則,即“行使代位權取得的財產,歸債務人后再清償債權”,1997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律工作委員會印發《合同法(征求意見稿)》,關于代位權就有意見認為,“行使代位權取得的財產,歸債務人后再清償債權”的規定不切實際,建議修改為“扣除債權人的債權份額后再歸債務人”。新合同法通過后,第73條對代位權進行了規定,但是從該規定無從看出對“入庫規則”的采用。縱觀前述背景,法律雖然在字面上沒有直接反映出來“入庫規則”,但代位權本身與代位權客體不是一回事,代位權客體是歸屬于債務人的,故其結果也應歸屬于債務人。并且從立法過程中的諸多草案上一致認為有這一規則。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合同法解釋(一)第20條規定:由次債務人向債權人履行清償義務,債權人與債務人、債務人與次債務人之間相應的債權債務關系即予消滅。可以看出,合同法解釋的精神已把代位權由單純的保全債務人財產的功能轉化成了清償債權的功能。“入庫規則”已被債權人直接受償權所取代。
三、“入庫規則”的悖離
從我國的立法選擇可以看出,在債權代位權行使的效果上,我國立法采用了代位權人“直接受償權”,已經悖離了“入庫規則”。悖離的現象還表現在日本民法中“抵銷”的規定中。從傳統的保全機能看,債權人代位受領后,由于清償的效果歸屬于債務人,代位債權人負有返還所受領標的物的義務,對此標的物,其他的債權人也可以申請執行以實現其債權。不過,如果代位受領的標的與被保全債權的標的物種類相同,發生抵銷適狀,或當債務人不配合拒絕受領標的物,在代位權的保全機能無法實現的情況下,則可以由代位債權人主張適用抵銷的規定,進而實現了事實上類似于直接受償的效果。對此,日本學者稱之為債權人代位權本來的趣旨(為全體債權人的一般財產的保全)與現實機能(代位債權人的優先的利益享受)的悖離i。可見,在這一點上,剛剛承認債權人代位權制度的我國,“悖離”的現象更為明顯,也就是說,我國債權人代位權制度已在功能上發生了質的飛躍。
四、“悖離”現象及代位權人“直接受償權”行使的合理性
(一)理論上的合理性
公平正義的理念。依照“入庫規則”,債權人行使代位權的效果只能直接歸于債務人,而不能由債權人直接受領。這就可能使其他債權人“搭便車”坐享其成,使債權人喪失提起代位權訴訟的積極性。在權利保護問題上,應該受到保護的向來是積極行使權利的人,而不是懶惰者,代位債權人最先“火中取栗”,縱沒有與他人分享,亦不悖于公道。法律規范的價值是通過實際運用、解決實際問題體現出來的,如果合同法的規定不能夠激勵債權人積極行使代位權,那么債權人更多的則會轉向最高人民法院《意見》第300條,合同法關于代位權的規定便只能停留在紙面上,成為立法者追求法律體系完美的道具。代位權設立目的是在保護債權人的利益,而讓次債務人直接向債權人清償債務,正好實現這一目的。若讓其他人共享,則不符合公平原則。而直接受償權有利于發揮債權人代位權制度對債權人的激勵集資,與公平正義這一法律總的精神相吻合。
(二)實踐上的合理性
在司法實踐中,代位債權人要想獲得次債務人的清償,必須事先證明他和債務人有了正當有效的債權債務關系,同時亦得證明債務人與次債務人之間有合法有效的權利義務關系。如果這一層的證明不算困難的話,那么要獲得債務人無支付能力的證據,要查明次債務人的財產狀況,要想辦法執行次債務人的財產(尤其是在如今執行難的情況下,次債務人想方設法頂著不執行,或者用多地多頭設戶、提供空帳號的辦法逃避執行,或者采取假抵押、假保全的方法制造假相等等。總之,次債務人逃避執行的辦法越多,債權人查報財產的難度也就越大)。即使成功了,也得花費代位債權人相當多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在這種情況下,若一味地實行“入庫規則”、一味地追求“債權平等,清償平等”,那么只會造成實質上的不平等。同時,訴訟的進行不是代位債權人付出了相當多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即能勝訴的,倘若敗訴,則須承擔失敗的訴訟費用。敗訴,損失由代位債權人個人承擔;成功了,則由全體債權人共享利益,其間是否公平,不言自明。
就實體法層面而言,我國法律賦予債權人在債務人怠于行使自己到期債權而可能在有害于自己債權時得以越過債務人,直接對次債務人提起代位權訴訟追索債務人的權利,此種權利不僅具有程序意義,而且具有實體意義。這表現為債權人行使代位權,不僅僅是對債權行使的代位,而且在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發生抵銷權,直接引發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的權利義務的消滅。多年來,我國“三角債”問題愈來愈嚴重,合同當事人之間互不信任,不積極履行自己的還款義務,也不行使自己對第三人的債權,嚴重干擾了市場的正常發展,社會誠信原則受到了威脅。在這種情況下,如不采取法律措施,沒有法律的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將會受到嚴重侵犯。基于此,我國法律設立了債權人代位權制度,并規定法院可以直接判令次債務人向債權人履行清償義務,以抵銷債權人對債務的債權,并且使債權人與債務人、債務人與次債務人之間相應的債權債務關系消滅,達到保障債權人利益,穩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最終目的,從根本上解決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的“三角債”問題。
另外,從訴訟經濟和司法效率的角度看,將債權人行使代位權獲得的利益歸屬于債務人,只能是徒增程序上的繁雜和不便而已。因為按照“入庫規則”,法院將判決債權歸債務人直接受領,債務人受領行使代位權所獲利益后,債權人還得再向債務人行使請求權以實現債權。等于說,債權人想實現自己的債權,往往要提起三個訴訟,即代位之訴,撤銷之訴和給付之訴。通過三個訴訟的疊加去實現一份債權,這顯然是人為的使程序變得復雜起來,增加當事人的訴累和訴訟成本,浪費司法資源,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采用代位權人直接受償權,完全可以避免此類不經濟訴訟的發生。債權人提起的代位之訴一旦勝訴,在次債務人所負債務范圍內,債權即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同時又能真正公平、快捷地實現債權。從現實意義上講,這較“入庫規則”更優。
五、構建代位權人“直接受償規則”
基于本文論述,鑒于我國目前社會經濟生活實際情況,筆者建議我國立法應構建代位權人“直接受償規則”,明確提出代位權人擁有“直接受償權”。
首先,應堅持合同法解釋有關規定精神(第14條——第20條),并對有關內容進行豐富細化,進一步明確規定“在代位權訴訟中,經人民法院審理后認定代位權成立的,應由次債務人直接向債權人履行清償義務,債權人與債務人、債務人與次債務人之間相應的權利義務關系即予消滅。”
其次,為從公平角度考慮,保護次債務人的合法權益不致受到過分影響,應規定并完善次債務人的各類抗辯權。
第一,基于債權人與債務人關系的抗辯。代位權的行使,須債權人有合法有效的債權存在。若債權人并不享有合法有效的債權,或者該債權已過訴訟時效,次債務人就可以此為由進行抗辯。
第二,基于債務人與次債務人關系的抗辯。對于這一關系內的抗辯,首先進入我們視野的,是次債務人在此關系內所固有的抗辯權。如債務人并無正當權利或權利已過訴訟時效或其它瑕疵抗辯權等。另外,債務人針對次債務人所為的權利處分能否作為次債務人的抗辯呢?應分兩種情況進行分析。在代位債權人提起代位之訴前,債務人已為處分的,次債務人可以以此為抗辯。但是,代位之訴提起后,次債務人就不得以此作為抗辯。
第三,債務人有支付能力抗辯。代位權行使的前提,是否需要債務人有支付能力,應區分特定債權和不特定債權而定。在特定債權下,由于不需要債務人無資力,所以,即使債務人有足以償債的財產,次債務人也不能以之為抗辯。在不特定債權下,若次債務人有證據證明債務人有財產的,則仍應區分兩種情況。其一,為債務人本身擁有的財產。此時,次債務人當然可以以此為抗辯;其二,債務人本身無資力,但是有對其它義務人財產權利的,次債務人能否以之為抗辯呢?上文已經提到,除非是債務人對代位債權人的財產,否則不得以此為抗辯。
參考文獻
[1]劉春堂.特定物債權與撤銷權.中國法學.2000(2).
[2]陳開墅,張國炎.論債權的保全制度.中國法學.1991(4).
[3]史浩明.論債權代位權制度.社會科學家.1994(1).
[4]申衛星.合同保全制度三論.中國法學.2000(2).
[5]江偉.民事訴訟法學原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