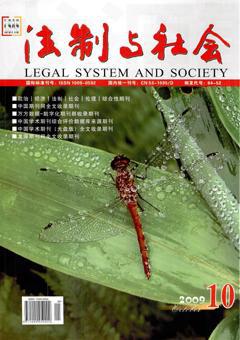也談“同命不同價”
黃卉靚
摘要目前的死亡賠償金制度中的城鄉差別招致了社會的廣泛批評,產生了“同命不同價”的質疑。但由于死亡賠償金制度是建立在繼承喪失說的基礎之上,所以目前死亡賠償金制度的主要缺陷在于定額化的死亡賠償金制度抹煞了個人之間的區別,從而違背了死亡賠償金制度原有的填平損失的功能。
關鍵詞死亡賠償金 填平損失 收入狀況 合理差別
中圖分類號:D9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09)10-117-01
“同命為什么不同價”?2005年的一個案例引發了人們對當下死亡賠償金制度的質疑:2005年12月15日,在重慶市搭乘同一輛三輪車的3名花季少女遭車禍喪生,但是其中兩個具有城市戶口的女孩家屬獲得了20多萬元的賠償,而戶口在江北區農村的女孩父母只獲得了5萬余元的賠償。結果一出,輿論嘩然,人們在發出質問的同時,矛頭直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人身損害司法解釋)第二十九條的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認為這條規定與憲法規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相違背,加劇了城鄉分化。不少學者和律師上書最高人民法院,建議消除城鄉差別待遇,制定統一的死亡賠償金標準。
對于“同命不同價”的質疑和爭論,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面談談我的一些看法:
一、死亡賠償金的性質
死亡賠償金的概念和性質,歷來就存在爭議。在《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條例》中被稱作“死亡補償費”;《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產品質量法》則首次使用了“死亡賠償金”的概念并且在解釋上,被傾向于認為具有精神損害賠償的性質;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在第九條規定,精神損害撫慰金包括致人死亡時死亡賠償金;人身損害司法解釋出臺后,又確認死亡賠償金的性質屬于財產損失賠償,而非精神損害撫慰金。最高人民法院在其編發的人身損害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一書中明確第二十九條的規定采取的是“繼承喪失說”,即認為侵害他人生命致人死亡,造成受害人余命年歲內的收入“逸失”,而這些收入本應作為受害人的財產由其法定繼承人繼承,因此,受害人提前死亡而致的“逸失利益”就成為其繼承人可繼承財產的損失,應當由賠償義務人賠償。正是由于人身損害司法解釋規定的死亡賠償金是對繼承人的預期繼承收入的賠償,而不是對個人生命價值的補償,因為生命對于任何一個人而言都是彌足珍貴和無價的。因此,“同命同價”的要求實際是建立在死亡賠償金是對人的生命的賠償,人的生命是平等的,因而死亡賠償金也應統一標準的錯誤論證的基礎之上,所以,認為人身損害司法解釋第二十九條的規定導致了“同命不同價”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更有人認為所謂“同命不同價”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
二、人身損害司法解釋第二十九條規定存在的問題
雖然以“同命不同價”來指責人身損害司法解釋第二十九條侵犯公民平等的權利是不妥當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人身損害司法解釋第二十九條的規定完全沒有問題。在我看來,這條規定至少存在兩個問題:一是既然死亡賠償金是對受害人將來收入損失的賠償,而決定個人收入多少的因素有很多,諸如地域、行業、學歷、經驗等等;而且每一個具體的個人收入也是千差萬別的,但是第二十九條僅考慮戶籍因素并以定型化賠償模式確定死亡賠償金的賠償標準,就顯得十分機械和粗糙,并不能體現每一個具體的人的收入差異,也背離了填補受害人繼承人損失的初衷。二是既然死亡賠償金是對受害人將來收入損失的賠償,為何要按照受訴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有關標準來計算?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那么同一侵權案件,當侵權行為地和被告住所地分別在不同的省份,則會因為受理法院的不同,而導致死亡賠償金的數額不同,這首先在邏輯上就是說不通的。另一方面,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也很有可能與受害人的收入狀況毫無關聯。
三、對人身損害司法解釋第二十九條規定的修改建議
200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在云南高院請示的個案答復中明確“受害人雖然是農村戶口,但在城市經商、居住,經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來源地均為城市,損害賠償費用應當根據城鎮居民的相關標準計算。”,該批復不再堅持人身損害司法解釋第二十九條簡單絕對地以城鄉戶口來區分死亡賠償金的計算標準,提出了在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應根據案件實際情況,充分考慮受害人經常居住地、主要收入來源地等因素,但是仍然堅持定型化的計算方式,不考慮個體差異。2007年8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修改人身損害司法解釋第二十九條規定的兩個方案,一是增加“同一侵權事件中,受害人既有城鎮居民也有農村居民的,根據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死亡賠償金數額。受害人住所地在農村但經常居住地城鎮的,死亡賠償金根據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的內容;二是規定死亡賠償金統一按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在我看來,這兩個方案只是順應了所謂農村人應與城市人同命同價的觀點,統一按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看起來似乎公平,而實質上沒有解決第二十九條存在問題,也與“繼承喪失說”的理論相背離。
基于上述對人身損害司法解釋存在問題的分析,我認為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并非要制定出統一的死亡賠償金標準,而是應當體現受害人作為一個具體的人而非抽象的城市人或農村人的收入狀況。在審判實務中應當允許當事人對受害人的收入狀況進行舉證,一般情形下只需根據受害人遭受人身損害前一年的收入計算,受害人無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平均收入計算。在當事人無法舉證的情況下,再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綜合考慮受害人的住所地、經常居住地、主要收入來源地等因素,參照受害人住所地、經常居住地或主要收入來源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