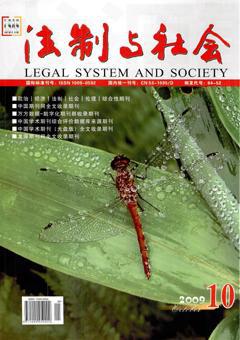精神贍養問題的道德法律化思考
鐘華龍
摘要隨著社會的轉型,傳統家庭模式的裂變,空巢老人的贍養問題愈發引人關注。本文結合我國法律的規定,對精神贍養問題提出了相關見解。
關鍵詞精神贍養 家庭模式 巢老人
中圖分類號:D9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09)10-118-01
一、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及老人贍養之現狀
我國《婚姻法》第二條規定:保護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合法權益。第二十一條規定:子女對父母有贍養扶助的義務。子女不履行贍養義務時,無勞動能力的或生活困難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給贍養費的權利。另外,《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也有老人贍養問題的相關規定。然而,在具體操作中,這一義務卻被狹義理解成物質贍養。其實,我國《婚姻法》等相關法律中關于“子女有贍養老人義務”的原則性規定并非僅指物質贍養,它還包括精神贍養在內。
子女對老人的贍養可以分為物質贍養和精神贍養兩方面的義務。老人需要吃飯穿衣睡覺,所以子女必須承擔提供老人生活必需物質的義務。在勞務方面,在老人因行動不便等原因自己承擔不了飲水、衛生打掃等勞務的情況下子女也必須予以解決,這也屬于物質贍養的范疇。此外,人的社會屬性和感情屬性決定了對老人的贍養還存在著諸如戀愛、探視子孫、和子女共同生活等精神贍養的問題。
遺憾的是現實生活中子女不承擔物質贍養義務的人為數不少,不承擔精神贍養義務的事情時有發生。物質贍養問題好辦,法律有明文規定,可以依法辦事,精神贍養的問題就不好辦了,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義務,單靠道德的力量很難得到保障。在以往的案例中,法院之所以很少理會老人的精神訴求,原因就在于沒有相關的法律依據。由此看來,道德問題法律化是很有必要的,借助法律的力量可以解決這一系列的道德問題。但問題并沒那么簡單,先來看看兩者的關系,以較二者之長短。
二、法律與道德之密切關系
(一)法律是道德教育的有效手段
法律是道德教化的有效手段,一方面積極鞏固道德教化的成果不被侵犯,另一方面又對道德教化的某些薄弱環節形成法律價值導向,幫助道德力量的成長。法院對子女給付老人贍養費的判決有助于保障子女贍養父母最低道德義務的履行,確保老人的物質贍養?,讓老人衣食無憂;同時若對探望和照顧護理等問題作出具體判決也將有利于在社會上形成對老人的精神贍養問題的正確價值導向。但道德有“最低限度的道德”和“較高要求的道德”之分。前者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是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道德內容,如老人生活費的給付;后者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子女對父母的探視。二者中,前者通常會轉化為法律,并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加以推行。而后者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因為一般來說法律過于涉足道德的領域會減弱道德的社會生活調節功能,也很容易造成法律與道德的混淆,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
(二)道德是法律制定的價值指導,對法律的實施起促進作用,可以彌補法律在調整社會關系方面的不足
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
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促進作用。孟子《離樓上》中講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道德就是一個重要的手段。良好的道德狀況有助于法律的更有效實現。
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后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
(三)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況下會相互轉化
一些道德,隨著社會的發展,逐漸凸現出來,被認為對社會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經常違反的危險,立法者就有可能將之納入法律的范疇,如隨著網絡的高度大眾化,某些網絡道德問題則很有必要用法律的手段來調整。反之,某些過去曾被視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為,則有可能退出法律領域而轉為純粹的道德調整,當代中國男女非法同居的問題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
三、道德法律化之短長
由以上對道德和法律關系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雖然,法律具有道德所不具有的優點(例如它的國家強制性、權威性、公開性、程序性等——這些都不是道德所可以取代的),而且道德法律化很多時候都是可行的,甚至是必需的,但絕對不是什么事情什么場合都是合適的。
法律調整的對象是人的行為,它調整的范圍不是無限的,它是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手段,但并不是惟一手段。在社會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問題都可以適用法律,我們在處理復雜社會問題時,除了法律還應有政策、紀律、規章、習俗、道德等的調整。即使是在需要綜合治理的場合,法律有時也不是首選的手段。法律只調整那些重要的社會關系領域,對有些“私”領域(諸如人們的思想觀念、認識和信仰問題),只要它尚未表現為外在的行為,并產生超出該領域以外的社會影響(例如信仰可能外化為暴力行動),就不宜采取法律手段加以調控。
誠然,法院對精神贍養方面的具體判決具有很大的肯定意義,它不但保障了老人的物質生活問題,同時也牛氣沖天地樹起了精神贍養之“孝”旗,但“孝”是發自內心的恭敬,是心甘情愿的自發性行為,而不能僅用數字來計量(每月的贍養費和探望次數),在這方面,依靠法律的懲罰,也許遠不如道德輿論的壓力更有效。以“公”的手段來解決純粹“私”的問題,不僅無效無益,反而有害。冤家宜解不宜結,對簿公堂后的子女,因輸了官司,丟了面子,在法律的威嚴之下,或能依法行事,但心里存留的或許只是更多的怨恨;對簿公堂后或許收獲的只是例行公事般的“孝道”和兩代人之間更深的隔膜。
一句話,法律與道德是社會規范最主要的兩種存在形式,它們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但在起源、形成方式、表現形式、適用范圍等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只有法德相融,依法治國和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并舉,無論是法律道德化還是道德法律化都綜合考慮,權衡利弊,力求法律適當道德化,道德適時法律化,才能實現社會和諧,人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