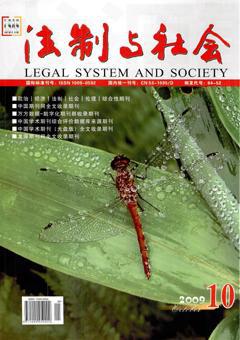宅基地引起的糾紛
李文靜
摘要宅基地作為中國特色的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一部分,雖然隨著國內實時環境的變化而對相關法律、政策進行相應的修改,但是不得不說的是,在宅基地證的管理上存在著眾多漏洞,致使在這方面的糾紛一件接著一件發生,影響了村民的正常生活和國土局的正常工作。本文試從在宅基地方面產生的法律糾紛中總結出其存在的問題,并對問題進行合理分析,以期能夠對宅基地的管理有所裨益。
關鍵詞集體土地所有權 宅基地 宅基地證
中圖分類號:D92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0592(2009)10-120-02
一、從集體土地所有權看宅基地
集體土地所有權,是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屬于集體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分配的權利。我國集體土地的所有權,是解放后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后逐步形成的,它是在土地私人所有權的基礎上產生和形成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由村農業生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已經屬于鄉(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于鄉(鎮)農民集體所有。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已經分別屬于村內兩個以上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于各該農業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0條第2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8條第2款之規定,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客體范圍包括: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農村的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對于宅基地,農村集體組織成員可以在其上修建住宅,住宅的所有人對該宅基地只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自留地、自留山只是意味著農民可以在其上進行經營并將所獲得的產品歸其個人所有,該農民對該自留地、自留山并不享有所有權。宅基地使用權,是指農民集體組織中的成員依法取得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用于建造房屋,居住使用的權利。根據我國法律規定,農村居民獲得宅基地使用權用于住宅建設,應當符合鄉(鎮)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并盡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內空閑地。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的標準,且農村村民不得買賣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宅基地。農村村民出賣、出租住房后,再申請宅基地的,不予批準。農村村民對宅基地上的房屋、廠柵、豬圈、廁所、竹木等歸農民所有。
二、土地征用引發的糾紛
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60條”,就規定農民自己的房產可以出租、也可以買賣。可是《農村人民公社60條》承認農民房產的交易權利,但又禁止宅基地的交易。為適應廣州市基本建設需要,建設海珠區官洲國際生物島,廣州市啟動一場比較龐大的征地運動。廣州市海珠區官洲國際生物島范圍內的集體土地,經省政府報請國務院批準同意征用,市政府于2004年4月發布《征用土地公告》(穗府征〔2004〕12號)。2004年6月16日廣州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發《征地補償安置方案公告》(穗國土證補[2004]24號),2007年11月26日發《征地補償安置方案補充公告》(穗國土征補[2007]7號),2008年廣州市人民政府發《關于推進海珠區官洲國際生物島征地拆遷安置通告》(穗府[2008]32號)。對于征地補償的方案一個接一個的出臺,但是官洲村的村民對其補償方案頗有意義,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糾紛。政府已經對村民按照出臺的方案發放補償,但是村民拒不交出土地,行政部門對不交出土地的村民發布《責令限期交付土地決定書》。因為征收的土地會涉及村民的宅基地,所以廣州市國土資源與房屋管理局海珠分局就會將其存檔的《農村(墟鎮)宅基地使用證》的相關資料調出來查閱,這樣一來問題就產生了。國土局發現村民的宅基地證的存在不合法,像是證上標注的面積超過法律規定的范圍,申請人不具備法律規定的資格,發證的程序不合法等等。隨即運用行政處罰的手段,發布《行政處理決定書》,依法撤銷村民的宅基地證。這對于持證十余年的村民而言是一種打擊,所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狀告廣州市國土局的行為違法,要求撤銷行政處罰。僅就2009年前半年就處理了不下5個類似的案子,還有許多相關案件。
三、分析原因
(一)職能部門職權范圍的變化
原來是縣政府下設的區公所管理宅基地證的審批、發放等工作,但是2002年4月22日發布了《關于撤銷海珠區新滘鎮設置官洲華洲兩個街道辦事處的批復》(穗府函[2002]27號)撤鎮設街的決定,使得原新滘鎮變成如今的官洲和華州兩個街道,并將宅基地證的管理權限轉移到廣州市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期間的工作交接和雙方訂立的標準的不同都產生了許多問題。縣政府下設的區公所對《農村(墟鎮)宅基地使用證》的審批及發放的程序并不嚴格,可以說是標準根本不一致,導致建立起來的檔案不齊全,發出去的宅基地證也有不合法的情況,遺留問題眾多。由于原來由更接近村民的區公所受理宅基地事宜,所以很多時候區公所在辦事時不會很嚴格按照程序來走,會為村民大開方便之門,而導致新舊管理部門交接時,出現檔案資料不齊全的問題。
(二)實際情況復雜
對新滘鎮的管轄,歷史上曾有多次變動。建國初期,由廣州市直接管轄;1956年以后劃歸廣州市郊區管轄;到了1960年7月新滘劃入海珠區管轄;1961年8月又劃到芳村區管轄;1962年8月,隨著芳村區與郊區合并,新滘鎮又屬于廣州市郊區管轄;1986年5月新滘鎮再次從郊區劃出,歸海珠區管轄直到最后撤銷。2002年3月28日官洲街、華洲街掛牌成立,連同2001年10月12日成立的南洲街、琶洲街,時稱“四個洲”。至此,原新滘鎮所轄20個行政村,全部劃歸8個街道辦事處管理:昌崗街管理聯星村,鳳陽街管理五鳳村、鳳和村,瑞寶街管理瑞寶村、石溪村,江海街管理紅衛村、桂田村,南洲街管理瀝滘村、三滘村、東風村,琶洲街管理琶洲村、黃埔村、石基村,華洲街管理龍潭村、土華村、小洲村,官洲街管理北山村、侖頭村、赤沙村、官洲村。按照城鄉一體化原則理順街村關系,街道轄內的村社在原建制不變的前提下,剝離與新滘鎮的關系,納入街道管理。五鳳村劃歸鳳陽街管理;紅衛村劃歸江海街管理;瑞寶村劃歸瑞寶街管理;聯星村屬下28個經濟社行政工作歸所在街道管理,聯星村合作經濟組織歸口區鄉鎮企業局管理。據國土局工作人員透露,新滘鎮曾有多次門牌號碼的變動,而檔案卻沒有來得及更新,致使發放了的《農村(墟鎮)宅基地使用證》的地址與現實的地址出現矛盾,無法確定證的所指是哪里。這給遺失宅基地證的村民在補辦證時帶來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不僅僅是程序上要多走一環,即需要村委會或經濟合作社開具證明方能去國土局遞交,一旦缺少這一環節國土局將不受理村民請求,即使其原來辦證的程序齊全。
(三)法律條款、規范模糊
關于宅基地的法律規定是模糊的,很多情況下,不能找出明確的法律條款來支持村民的請求或者行政部門行政行為,但是相較而言法律的不完善卻可以給行政部門帶來很大的空間自由裁量,畢竟行政部門擁有行政立法權。國土局應對村民提起訴訟所利用的一般是以下幾部法律及其條款:《廣東省土地管理實施辦法(1991修正)》“第二十條農村居民、回鄉落戶的干部、職工、復退軍人以及華僑、港澳同胞和臺灣同胞建住宅使用集體所有的土地,應向鄉(鎮)、村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提出申請,經同意后,上報審批:使用原有宅基地、村內空閑地和其他土地的,由鄉(鎮)人民政府批準,并辦理用地手續;使用耕地的,經鄉(鎮)人民政府審核,報縣級人民政府批準,并由縣級人民政府國土管理部門辦理用地手續。第二十一條鄉(鎮)、村居民興建住宅用地應當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內空閑地;需要使用耕地的,必須從嚴控制。每戶用地限額:平原地區,八十平方米以下;丘陵地區,一百二十平方米以下;山區,一百五十平方米以下。但在人多地少地區和城市郊區以及鄉(鎮)非農業戶,六十平方米以下。各市、縣(區)人民政府可在以上用地限額內結合本地實際情況,規定具體用地標準。華僑、港澳同胞和臺灣同胞興建住宅用地,參照當地標準,可在增加百分之二十的額度內給予照顧;超過限額的,報縣級人民政府批準。”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1988修正)》“第三十八條:農村居民建住宅,應當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內空閑地。使用耕地的,經鄉級人民政府審核后,報縣級人民政府批準;使用原有的宅基地、村內空閑地和其他土地的,由鄉級人民政府批準。農村居民建住宅使用土地,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出賣、出租住房后再申請宅基地的,不予批準。第四十一條:城鎮非農業戶口居民建住宅,需要使用集體所有的土地的,必須經縣級人民政府批準,其用地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并參照國家建設征用土地的標準支付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以上的都是適用范圍比較廣,法條解釋相對于模糊的法律,詳細一點的是《廣州市農村村民住宅建設用地管理規定》對于廣州市市轄區范圍內的農村村民使用本集體經濟組織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建設住宅進行了規定。這是由廣州市政府頒布的,但也只是對申請批準住宅建設用地進行大致上的程序規定。對于宅基地證的遺失補發并沒有在法規上提起,只是在國土局的官方網站上有將其程序列出來。
四、總結
宅基地對于村民而言,使他們在多年的奮斗中得到的一點回報,是他們能夠生存在這片土地的依據。一旦突然失去這份已經屬于他們很久的財產,他們心里將會產生極大的不安,同時對于政府的不滿情緒也爆發出來。政府對待宅基地一想貫徹便民的思想,一切以村民方便為主要目標,盡量簡化程序與民方便。但是,當時的便民路線卻埋下了隱患的種子。縣政府撤銷,由廣州市海珠區國土資源和房屋管理局接手,一切習慣改變,原來的程序要求也跟著改變。國土局收到的可是一個爛攤子,當時的宅基地管理并不系統,也不科學,就算知道要建立檔案也是參差不齊的,但是已經十幾年了,國土局也就沒有再去追究缺漏眾多的檔案。2004年廣州市為了繼續發展而要征地建設官洲國際生物島,此時村民與國土局的矛盾開始浮出水面。長久以來,民與官之間存在著一層不可逾越的隔閡,人民對于當官掌權的總是抱有深深的成見。突然之間就要征走他們居住了數十年的土地,人們當然頗有怨言。政府出臺的征地補償方案,盡管補償在全國范圍內來說已經不錯,但是村民還是對其充滿著不信任。雙方僵持之下,國土局只能強制執行其權力,與此同時村民也不愿意交出土地,雙方矛盾激化。國土局在翻查舊檔案的時候就發現,原來數十年前發放的宅基地證存在著眾多不合法的地方,依法撤銷了村民持有的宅基地證,村民固有的敵視觀念與征地政策聯系起來,就會產生誤解,認為國土局在搶他們的土地,至此矛盾爆發出來。政策的理性與目標群體的期望發生強烈的沖突時,不僅影響政策的繼續執行,同時也破壞了政策制定者在目標群體眼中的形象,影響了雙方日后的配合。
廣州市的宅基地管理仍然在不斷的改進,適當的從法院的訴訟中汲取經驗教訓,從民間聽取意見,對于將來處理相同問題也可以有據可循,對于將國土局從無休止的糾紛中解放出來是百利而無一害的。
參考文獻:
[1]楊一介.農村宅基地制度面臨的問題.中國農村觀察.2007(5).
[2]趙樹楓.試論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農林工作通訊.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