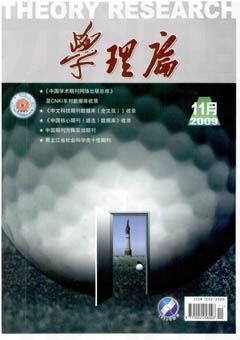石羊河流域水權制度建設評析
李 珂
摘要:我國的水權制度,仍處于研究階段,許多具體的制度內容還需要進行理論上探索和實踐上的檢驗。就石羊河流域而言,有關流域治理規劃、水量分配方案(計劃)奠定了水權制度建設的基礎。但是從具體實施和操作層面來看,尚需進一步完善,必須實現從單純的水量分配到完善的水權制度建設演進。水權建設必須在水量分配的基礎上,建立水量分配方案實施的制度和能力保障,構建水量分配的權利邊界,實現水量分配由“量”到“權”的轉化。因此,如何通過公平和公正的程序將制定的水量分配方案落實為水權分配方案,如何將水權分配方案實施,并建立必要的實施和保障機制,這些機制的建設和執行是水權制度建設的核心。
關鍵詞:石羊河流域;水權;水權制度;評析
中圖分類號:D922.38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09)29—0034—02
一、水權制度概述
(一)水權的概念
水權由水資源所有權派生而來的,而人們對水資源的認識可以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般地說,是指人類可以利用的,逐年可以得到恢復和更新的一定質量的淡水資源。廣義上往往還包括經過工程控制、加工和凝結人工勞動和物化勞動的水商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江河湖海等水資源作為人類無法控制、獨占的共有物,沒有形成水資源所有權的概念,一般用河岸權、地役權等物權來調整水資源權益。隨著水資源開發利用規模的擴大和水資源問題的日益嚴重,普通法的有關規定已經很難適應水資源的使用和管理,一些國家的法律開始將江河湖海等水源賦予所有權概念。顯而易見,在水資源之上設置權利,乃是經濟發展的需要和時代發展的必然產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此的定義為:水資源為可利用或有可能利用的水源,具有足夠的數量和可用的質量,并能在某一地點為滿足某種用途而可被利用。此定義有三個顯著的特征:①將經濟、技術因素隱含在水資源中,強調了水資源的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②將失去使用價值的污水劃歸到水資源行列中,為污水再次開發利用開辟了途徑;③明確強調水資源是環境資源,因而水資源的開發利用必須限制在環境可承受的范圍之內。
關于水資源的產權,也可以簡稱為水權(Water Entitlements或Water Rights),我們可以定義為:水權,即水資源使用權是指水資源使用者在法律規定范圍內對所使用的水資源的占有、使用、收益和依法處分的權利。
(二)水權制度
水權制度是指約束和保護人們行使水權的各項權利的制度安排,是規范人們相互之間水行為的各種制度的總和。具體地講,水權制度是劃分、界定、配置、調節、保護和實施水權,明確國家和用水戶權、責、利關系的規則,從法制、體制、機制等方面對水權進行規范和保障的一系列制度的總稱。完善的水權制度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減少水事糾紛,平衡各方利益。這在水資源極為緊缺的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區流域顯得尤為重要。我國《憲法》和《水法》均明確了水資源的國家所有權。有關流域、區域和行業初始水權配置的法律法規從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等三個層面基本構筑了區域和行業初始水權配置的路徑。同時,現行法律法規規定的取水許可制度、用水定額制度、水資源費征收制度等構筑了取水權配置的途徑。
水權制度建設是整個水資源管理制度體系的核心,也是破解流域生態環境惡化難題的重要途徑。在水權制度建設方面,作為西部內陸河流域典型的石羊河流域,結合實際進行了有益的實踐和探索,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但是也存在不太成熟的地方。
二、石羊河流域水權制度的沿革及現狀
石羊河流域初始水權制度的建設分為兩個階段:一是以時分水階段,二是以量分水階段。石羊河流域自古以來就有以時分水的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因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在石羊河流域先后進行了以“以時分水”和“以量分水”為基本原則的水利規劃,但長期以來由于各種原因,協議并未得到真正執行和實施,從而也就無法調解上下游用水需求的矛盾,并造成整個流域用水的無序和混亂。截止目前,全流域用水量已超出流域水資源承載能力近6億m3,嚴重威脅到整個流域的可持續生存和發展。為緩解這一嚴峻形勢,建立良好的用水秩序,保證石羊河流域的可持續發展,甘肅省水利廳在水利部指導下,重新開始“以量分水”模式的探索及實踐。2005年10月,甘肅省人民政府制定并批準實施了《甘肅省石羊河流域水資源分配方案及2005~2006年度水量調度實施計劃》。同時,圍繞落實該分配方案,編制完成了《石羊河流域重點治理規劃》。甘肅省水權制度建設不僅體現于全流域層面,而且體現于區域層面。
石羊河流域農民初始水權配置的探索,是從地表水和地下水兩個層面展開的:農民地表用水的配置,實行灌區配水到戶,農民用水戶協會分水、收費到社(組、戶):農民地下用水的配置,實行灌區份額到支,農民地下水用戶協會分水,收費到社(組、戶)。其中農民用水者協會。在實踐中,其具體做法是,按照先組建、后規范、邊試點、邊探索、邊總結的總體思路,根據多年來掌握的農業用水情況、灌水定額、渠系配套、作物種植的實際制定了用水定額指標,認真丈量各用水戶現有耕地,以實際面積確定初始水權,按渠系逐戶造表建冊,并張榜公示,在全體用水戶無異議后,發放《水權證》,以水定地,明晰水權。
三、石羊河流域水權制度建設評析
石羊河流域的水權制度建設,作為流域重點治理的一項重要內容業已取得令人欣慰的成績。該流域水權制度的建立和運轉不但明確了用水戶的水使用權,而且強化了水資源的國家所有權,實現了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的有計劃用水,完善了有償用水制度,并為水權市場的建立提供了基礎。這樣,水資源的利用效率將空前提高,公民節水意識也大大增強。但由于這一套制度剛剛試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
首先,“以電控水”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且與電力部門的利益相沖突。水權制度賴以運轉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以水定電,以電控水",在此之前,地下水開采基本上處于無法控制的局面,只要有電,農民就能通過抽水設施無限制地從機井取水。而現在,電力部門只能按照由用水量換算的用電量供電,供完就予以停電,用水戶自然無法超額取水。因此在目前的技術水平下,以電控水是對地下水開采量最有效的控制方法。但根據《電力法》第七條的規定,電力建設企業、電力生產企業、電網經營企業依法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行政機關除履行監督職能外,不能對電力企業的依法經營予以干涉,要求電力公司控制供電量的行為顯然與該原則不符。并且對于電力公司來說,電量的控制將使其面臨利益損失,尤其是要失去這樣一個大的市場份額,自然會產生抵觸情緒。
其次,水權流轉范圍狹窄,水權市場的發展受到限制。水權制度建立的目的在于使水資源達到優化配置,提高水資源的利用效率,因此水權轉讓機制和水權市場的充分發展至關重要。但由于目前水權制度正在試行階段,水權轉讓的管理尚不完善,因而各地均對水權轉讓作了嚴格限制,只允許同一灌區內轉讓,有的甚至只允許同一農業用水者協會進行內部轉讓,灌區和灌區之間、地域和地域之間、各行業之間的轉讓都不允許。實際上,隨著勞務輸出人口的增加,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農民臨時或長期在外打工,并未從事農業生產,其擁有的配水額或者水票期待轉讓,另一方面由于種植作物、地質以及澆灌方式的不同,一些農戶的配水額也許不能滿足生產需求,加之計劃外用水受到嚴格限制,因而又期待他人轉讓水權,此間必然存在較大的水權市場空間。例如,在水權制度實行以前,民勤縣薛百鄉種植小蔥效益較高,據悉每畝小蔥的收入可達1萬元以上,由于品質好,其中一部分還出口日本,這不但增加了農民收入,也增加了縣財政收入甚至出口創匯。但小蔥屬于高耗水作物,水權制度推行后,用水戶只能按照配額用水,這樣小蔥種植肯定受到影響,為了繼續維持較高的經濟效益,向其他灌區購買水權自然是一個經濟實惠的選擇。
第三,制度建設薄弱。石羊河水權制度建設,發揮了水量分配方案在水權制度建設中基礎作用,重視了工程配套設施在落實水權權利邊界中的支撐作用,但沒有認識到制度建設在水權制度建設中的重要意義。缺乏有關水量分配方案確立過程中的協商制度、水量分配方案頒布實施的責任、管理和獎勵制度、水資源監測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這些制度對于維護規劃和水量分配方案的權威,保障規劃、方案順利實施,實現水量權利轉化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四,農民用水戶協會性質模糊。石羊河流域現有的農民用水戶協會性質模糊主要表現為協會更多體現為灌區下屬的管理機構,而非農民共有水權的代理人。民勤縣建立農民用水戶協會的初衷是為了解決水費收繳過程中的灌區和農民之間的糾紛和灌區維護費用收繳水費和灌區維護費難的問題。因此,農民用水戶協會的主要職責是收繳水費和灌區維護費,負責灌區的管理和維護,沒有真正履行共有水權代理人職責。但農民用水戶協會因其規模效應和草根性,對于降低農民水權的配置、履行及保護,提高共有水權的管理效率,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具有天然的比較優勢。因此,明確界定農民用水戶協會的共有水權代理人性質,轉化農民用水戶協會在灌區管理中的權利主體地位,是發揮農民水權在水權制度建設中的基石作用、維護農民合法權益、增強農民節水意識、規制灌區配水行為、提高灌區管理水平、減少農戶與灌區配水糾紛的根本舉措。
綜上所述,石羊河流域的水權制度建設還很薄弱,因此,在石羊河流域管理中,必須以立法為先導,通過法律、政策規定一系列相關制度,來保證流域管理的有效運轉。而水權制度立法不僅是水資源管理和開發利用的基礎,而且也是生態環境恢復和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的根本保證。
參考文獻:
[1]高而坤.中國水權制度建設[M].北京: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7.
[2]李珂.水權與水權交易體制的理論分析[J].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4,(1).
[2]裴麗萍.水權制度初論[J].中國法學,2001,(2).
[3]馮尚友.水資源持續利用與管理導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4]劉世錦.經濟體制效率分析導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5]徐華飛.我國水資源產權與配置中的制度創新[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1,(11).
(責任編輯/石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