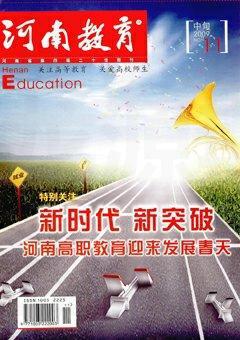重返“五四”現場與省思“五四”精神
劉宜慶
在眾多關于五四運動的書籍中,葉曙明的《重返五四現場: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和楊念群的《“五四”九十周年祭——一個“問題史”的回溯與反思》這兩本書,不但加深了我們對民國初年歷史的了解,也為我們反觀身處的時代提供了一種視角。
如何紀念五四運動?這兩本書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供了研究五四運動的視角和方法:一是重返五四現場,近距離觀察五四運動,描摹“五四”人物的言行,勾勒被人忽視的細節,發掘被湮沒的場景,呈現五四運動的歷史邏輯鏈條;二是反思五四運動,將五四運動擴展至清末變革和民初社會革命的前后長線關聯中進行重新定位,關注“五四”發生的社會環境,考察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判斷和歷史選擇,厘清從晚清民初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這段歷史。
《重返五四現場》以“五四”人物為經,以晚清民國為緯,綱舉目張,牽出五四運動的前因后果與諸多方面,通過一個個鮮活的歷史人物和事件現場來透視當時的歷史與社會,構成了一幅立體的五四運動的全景圖。他把廣東人梁啟超、陳炯明當做五四運動的序曲和尾聲,言之成理,令人耳目一新。
我們不妨穿越90年的時光隧道,回到1919年5月4日那一天,親臨歷史現場,發掘五四運動中被遮蔽和被忽視的細節。也可以從個體記憶和公眾輿論中聆聽那些被歷史煙云湮滅的聲音,感受悲喜交集的歷史心情,省思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繼承五四運動的精神遺產。
歷史充滿了偶然性,歷史又是一個篩子,有時會漏掉極為重要的信息。重返歷史現場,我們可以看清楚很多問題。1919年5月4日,是個星期天。倘若并非星期天,起碼美國駐華公使芮施恩可以出面接見羅家倫等人的說帖。若如是,在天安門廣場游行示威的學生的激憤之情將得到很大的緩解,事件很可能不會進一步激化。學生在烈日下苦等“遞交說帖”無果,遂轉向趙家樓發泄怒火。火,每逢歷史的緊要關頭就會出現。火燒趙家樓,這是革命之火、民主之光,當然,更是愛國學生的激情燃燒。《重返五四現場》一書,對1919年5月4日的高潮有精彩的描述,它援引“五四”人物的回憶和當時報刊的報道,撥開重重迷霧,讓我們看到了“五四”的真相。
1919年5月4日,天安門前豎起一塊旗幟式的長白布,上面寫著一副對聯:“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頭。”落款為:“北京學界同挽。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遺臭千古。”《重返五四現場》中說,這副著名的對聯是北大學生打出來的。筆者查閱了幾份史料發現,對聯應為北京高師學生張潤芝所撰。
《重返五四現場》一書所征引的史料大抵可靠,葉曙明對與五四運動緊密關聯人物的描摹,更加豐富和有層次,這有助于消除歷史人物臉譜化之影響。比如,對徐世昌的描寫:
自號“退耕老人”的徐世昌,是前清皇族內閣的協理大臣,滿肚子舊學問,一腦子舊倫理,他的母親劉氏又是桐城派劉大的后人,新文化諸子罵“桐城謬種”,他內心當然不爽。但他既沒有派軍警抓人,也沒有下令《新青年》或《新潮》停刊。你要出版,還讓你繼續出版;你要罵人,還讓你繼續罵人。只是讓教育總長傅增湘去給蔡元培提個醒。
五四運動是一個歷史大舞臺,政界、學界的人物都粉墨登場,《重返五四現場》中的政客、軍閥、警察、教授、學子、報人等各色人等無不接近歷史真相,它寫出了歷史的“溫度”,使人物的態度可感、聲音可聞。
“五四”是一個啟蒙的大時代,在新舊交鋒之際孕育出萬千氣象。“五四”不僅是德先生、賽先生、費小姐交替登場的舞臺,也不僅是一曲簡單的愛國主義贊歌,更是一塊各種新思潮和新主義的試驗地。主張文學改良的,主張保護國粹的;主張三綱五常的,主張個性解放的;這邊要打孔家店,那邊要把孔儒升格為宗教:思想的多元化,創造了眾聲喧嘩、異彩紛呈的劇場效果。如果說《重返“五四”現場》偏重歷史敘事,那么《“五四”九十周年祭》則偏重歷史省思:前者重視史實的呈現,后者重視史識的闡發;前者以飽滿、鮮活的歷史細節引人入勝,后者以睿智、思辨的歷史分析發人深省。
楊念群不僅從思想史的層面,而且從更廣闊的社會層面觀照五四運動,將之“社會史化”。新潮思想與保守勢力的交鋒,文學革命乃至白話文的興起,是“五四”的前奏,而“五四”對社會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更需要關注,因為五四運動誘發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造風潮,其得失成敗雖見仁見智,卻難以回避。楊念群在《“五四”九十周年祭》第四章《踐履型知識群體的崛起與社會改造運動》中指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后五四”邊緣群體的崛起,逐漸打破了“五四”時期原有主流思想的壟斷格局。這樣,分析“五四”啟蒙的路向如何就被徹底轉換了。
對于關注中國近現代史的人來說,“五四”是一個無法繞開的命題。誠如陳平原先生撰文所說:與“五四”對話,可以是追懷與摹寫,也可以是反省與批判;唯一不能容忍的是漠視或刻意回避。在這個意義上,“五四”之于當下的知識分子,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更是精神。如果“五四”精神只在每年的5月被提及,那是冷漠。錢穆先生講過,一個本國的公民當對自己國家以往的歷史具有溫情和敬意。選擇進入歷史的核心,“五四”永遠是一個最佳的路徑。
(作者系《半島都市報》文藝部編輯)
責編:曉 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