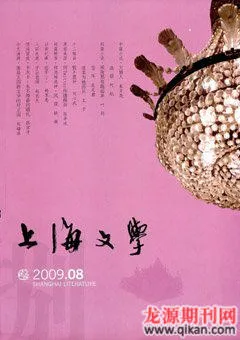子云老師
6月10日清晨,睡眼惺忪中,我習慣性地拿過枕邊的手機看時間,發現有一條未讀短信。打開:“很悲傷地通知各位親友,我姑姑李子云在華山醫院于6月10日凌晨一點因病離世。李揚。”
我一下子醒了。天還沒大亮。短信是凌晨兩點發來的,當時我睡著了,沒聽見。我又看了一遍。沒看錯,也不是在夢中。我傻了一樣,實在難以置信。其實,我還是有點思想準備的。一天前,8日下午,我聽說李老師住院,就趕去看她。她輸著氧,說話有點氣急,但還是平時的模樣,沒有過分的病態。她說她難受,胸口憋得很。她說你是知道的,我怕痛,我想舒服一點地走。我說哎呀,你這樣子,說什么走啊,會好的!我真是覺得她會好的,盡管我知道老人得肺炎很麻煩,我還是完全沒有想過她會有生命危險。9日聽說醫院報過一次病危,但搶救過來了。我依然沒意識到危險迫近,我覺得她會度過這一劫的,她是生命力多么旺盛的人啊。二十天前,王蒙來上海,我們一起吃飯,她還談笑風生,完全不像要過八十大壽的老人。作協的同仁們正在張羅給她祝壽。上海人的習慣,生日是過九不過十,明天就是她七十九周歲的生日,她竟然提前一天告別了!
前一段,她已經在打算過生日了。她說她要請四桌,一桌是親戚,三桌是朋友。她說要分四次請,一次一桌,這樣和每桌的人都可以說話……唉!
我趕緊起來,給作協的幾位同事通報了情況,然后給李老師的侄子回短信:“李揚,實在想不到,這么充滿活力的子云大姐忽然仙逝,非常震驚,非常悲痛,三十年往事歷歷在目,揮之不去。她是對中國文學有貢獻的人,我們會永遠紀念她。”
“她是對中國文學有貢獻的人”。能承受這樣評價的人,不多,但我確實認為,她當之無愧。《上海文學》1979年4月號發表評論員文章《為文藝正名——駁“文藝是階級斗爭的工具”說》,震動了全國文壇,對于新時期文學界的撥亂反正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篇重要文章就是李子云牽頭撰寫的,在當時,寫這樣的文章,需要見解,更需要膽識勇氣。李老師是個有眼光,有見識,才華橫溢的批評家。她不是那種學院派的理論家,她長期在文學刊物工作,天天看稿子,天生的藝術感悟能力和豐富的編輯經驗融合在一起,就成為難得的藝術感覺好、貼近創作實際的編輯家和評論家。所以,我所接觸過的作家,談到她,都很服,引為藝術知己;不管是作為作者聽編輯談對作品的修改意見,還是看她在評論文章中對作品的分析,都覺得意見準確貼肉,直抵要害。很快,在她周圍,聚集起了一批有才華的中青年評論家。上海之所以文學批評力量特別強,在全國出類拔萃,除了因為有復旦和華師大兩所著名高校,有賈植芳、徐中玉、錢谷融這些名師,還因為有一本優秀的文學雜志《上海文學》,有李子云、周介人這樣的編輯名家。
我1978年5月在《上海文學》(當時名為《上海文藝》)發表第一篇小說,開始認識李老師,但接觸不多。她是著名文學刊物的領導,我是初學寫作的業余作者,距離太遠,只能算是遠遠仰望的關系吧。1985年我調入作協,她正主持《上海文學》雜志,和她也只是工作上的一些聯系,談不上友情。真正相熟,是在1990年以后。
1990年,巴老和于伶、王元化三位文學前輩發起成立上海文學發展基金會,吳強同志提議我擔任基金會的秘書長,而子云老師則是負責實際工作的常務副會長。我是她主要的助手,來往自然就頻繁起來。基金會可以說是白手起家。政府給了很少一點啟動資金,加上巴老捐的第一筆款,總共只有幾十萬。對于不能動用本金,只能用利息開展工作的基金會,幾十萬基本上是沒有辦法正常運作的。要籌募資金,對于李子云老師,實在是一件渾身不搭介的事情,既沒有這方面的能力,又沒有這方面的關系,平時又是恥于談錢的名士風格,真是難為她呀!我其實對于募錢,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的人,做她的助手,實在是不合適。況且,那時候我還是作家協會的秘書長,主持著日常事務,瑣事很多,也少有時間精力來為她分擔雜務。我以這兩大理由推辭,她卻不允。她說,和錢打交道,我最看重的是人要可靠。結果,許多應該秘書長做的雜七雜八的事情,都是她自己去張羅了。后來,仰仗交通銀行潘其昌董事長等的熱心扶植,才使文學基金會初具規模。其中,子云老師嘔心瀝血,個中甘苦,我是深有體會的。
子云老師是個充滿生活情趣、洋溢著生命活力的人。她喜歡吃飯,在上海灘,起碼在我們這個圈子里,是著名的美食家。有時候她會對我說,聽說哪里開了家飯店不錯,沒去過,什么時候一定要去一次;好幾個外地作家告訴我,他們吃過的最好的上海菜,就是李老師請他們吃的。所以我們有時要請客,常常會想到去問問她哪個飯店好;和她一起吃飯,當然是她點菜,準保是又好吃又有特色又價錢實惠的。
她愛熱鬧,喜歡交朋友,也有很多朋友。她的朋友上至文化界的權威泰斗,下至非常年輕的作家記者,并且保持著經常的聯系。所以直到晚年,很少外出了,依然消息靈通。她去世當天,鐵凝打來電話,說我好久沒見她了,挺想念這位老太太的……第二天,碰到吳亮,吳亮懊惱地說,好幾次碰到她,都說要好好聊聊,一直沒去,總覺得有機會的,唉……
我想,一定有很多很多她的朋友在想念著她,想念著這位智慧的、有見解的、有風度的、有趣的、健談的朋友。一個被很多人想念的人,她的生命,多么有價值啊。可惜的是,她的一肚子故事,因為她在中國文化界所處的特殊位置而了解的許許多多有價值的人和事,都隨著她的離去而帶走了。她好幾次說過要寫,沒來得及寫出來。她自己也沒想到會這么快地告別。這是無法彌補的遺憾。有價值的生命離去,總是會留下遺憾的,沒有辦法。
攝影/徐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