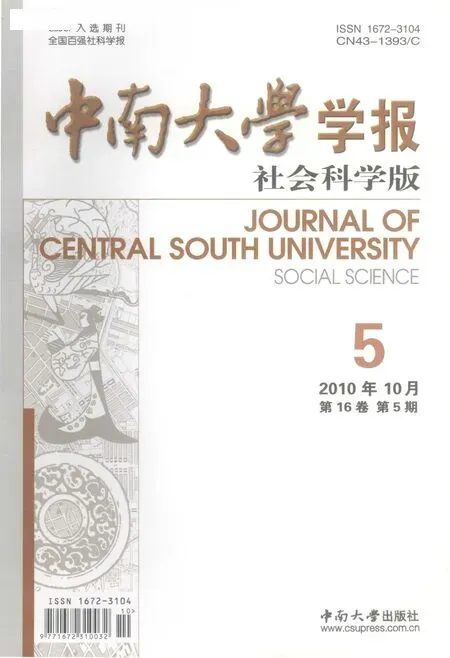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的刑罰適用問題研究
黃瑛琦,張洪成
(東南大學法學院,江蘇 南京,211189;中國刑警學院禁毒學系,遼寧 沈陽,110854)
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是我國《刑法》明確規定的一個行為方式選擇的選擇性罪名。故從本質上講,其為一個罪名,但也可以分開使用,也可以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進行重新組合適用。即在一個案件中,如果涉及到幾個行為方式,那么,該罪名所涵括的行為方式,均可以自行組合成為一個罪名,而無須實行數罪并罰。根據刑法的相關規定,作為一個罪名,其量刑的基準是同一的,故我們在將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分別從罪質上論述以后,再從量刑上對之進行統一的介紹。
一、毒品的數量與純度
(一)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的數量與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
按照《刑法》第347條第1款的規定,“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無論數量多少,都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予以刑事處罰。”但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則規定了對于販賣、運輸少量毒品的行為,予以治安處罰。如《治安管理處罰法》第71條第1款第3項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三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非法運輸、買賣、儲存、使用少量罌粟殼的。”按照國家食品藥品監管部門出臺的毒品目錄,罌粟殼無疑屬于毒品的范疇,故按照刑法的規定,非法運輸、買賣應當沒有數量的限制,但是《治安管理處罰法》卻明確將其作為行政違法行為處理,這應當說是一個明顯的沖突。筆者認為,對于這一沖突,完全可以通過法理學中“重法優于輕法”的法律適用原則來解決,即在行為人從事了走私、販賣 、運輸、制造毒品時,直接按照犯罪來處理就可以。
而實踐中的做法也證明了這是正確的。如有論者指出:“實踐中,筆者所在地法院均是嚴格依照該規定判處毒品案件被告人,即使是販賣0.1克,也予定罪處刑,沒有判決結論認為被告人不構成犯罪或免于刑事處罰的案件。”并指出,應當按照刑法第13條的規定“對毒品犯罪案件,同樣是適用的”。[1]該論者肯定販賣毒品罪無論數量多少均需要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這是正確的。但是對于其所指出的“對所有的販賣毒品犯罪,一律定罪處刑”,有論者持懷疑態度,認為“予以刑事處罰并不等于一定要判處實刑,也不等于一定要判處刑罰,對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數額極小的,可以判處緩刑,或者在審查起訴環節以不起訴處理,也可以在審判階段予以定罪免刑。予以刑事處罰并沒有排斥對犯罪作定罪免刑的處理,這才是立法的真正含義”。[2]筆者認為該批判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刑事處罰和定罪免刑還是存在差別的,二者在刑事責任承擔的一面是平行的,是刑事責任承擔的兩種方式,不能互相替代。
在我國現行的法律下,刑事責任主要是指:“行為人因其犯罪行為所應承受的,代表國家的司法機關根據刑事法律對該行為所作的否定評價和對該行為進行的譴責的責任。刑事責任本身具有實體的懲罰性意義。”[3]而根據我國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刑事責任的承擔方式有以下幾種:第一,行為構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并給予刑罰處罰;第二,行為構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只給予非刑罰處罰;第三,行為構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但既免除刑罰處罰,也不給予非刑罰處罰,即單純宣告有罪。可見,刑事處罰應當屬于刑事責任的下位概念。
而通觀我國刑法第347條的規定,其行為只能符合第一種責任承擔方式,那么就表明行為構成犯罪,必須給予刑事處罰,排斥了行為的行政處罰,即所謂的刑法與行政法的競合。從這個角度講,我國現行的立法還是存在矛盾的。那么,對于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的行為,既然立法中已經明確規定不管數量多少都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予以刑事處罰,那么就表明了該類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就理所當然地要適用刑法的規定進行定罪處罰。對于刑法與治安處罰法上出現的矛盾,應是今后立法中必須全面考慮的問題。
(二)毒品的純度對量刑的意義
作為一種物品,毒品以其本身的含量來滿足吸食者的需求,這樣毒品的純度直接決定了毒品的社會危害性。因為純度越高,其潛在的威脅就越大,其對社會構成的危害也就越大。因此,毒品的純度是毒品犯罪中繞不開的一個問題。
在我國香港地區的毒品管制法規中,雖然沒有關于持有、販運、非法供應和制造危險藥物罪的數量要求,但是,在具體的案件中還是比較注意對毒品純度的計算,即對于查獲的毒品,一般均要求折算成該危險物質的凈含量。香港特區的《危險藥物條例》(香港法例第134章)第二條“釋義”中規定:“任何分量的危險藥物,即使不足以秤量或使用,也屬危險藥物。”另外,該條例也對液體制劑和鹽類中所含物質的百分率的計算方法作出了規定。根據香港法律的規定,盡管涉案毒品的數量并非持有、販運、非法供應和制造危險藥物罪的構成要件,但是毒品數量卻與刑期之間具備密切的關系。①在香港的有關判例中,相關的判決書所認定的精神藥物及其制劑的重量,是以該種物質的凈含量為標準的。法院判決的刑期主要參考被控罪行的性質、涉案毒品的種類及分量、被告人的具體犯罪情節和背景而綜合決定的。可見,毒品的純度在香港刑法的量刑中還是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的。
相反,在我國臺灣地區相關的毒品管制法規中,毒品的數量就不具有獨立的影響定罪量刑的意義,而只是作為認定行為情節嚴重的基準之一。臺灣《毒品危害防止條例》依“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將所有的毒品分為三級,對運輸、販賣、制造不同級別的毒品的行為,處以不同的刑罰。涉案毒品的數量只是決定情節輕重的一個方面,而非法定刑的量化標準,所以,對毒品的純度進行檢驗是為了確定涉案毒品的數量,這只是量刑的參考。
由此可以看出,我國不同地區關于毒品犯罪是否以毒品純度計算重量的問題有不同的規定。的確,從醫學和化學角度看,純度較高的物質與含有其他物質而導致純度降低的混合物有質的區別,同樣重量的純度較高的毒品與純度軟低的毒品在交易中也有不同的價位。但對于刑事立法而言,特定時期的刑事政策、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以及法律的可執行性才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綜上所述,計算毒品的純度和重量的做法,是為了以統一的標準計算不同犯罪中的毒品數量,以作為定罪量刑的標準,從而實現執法的公正和統一。但是,在去掉“雜質”的同時,對行為人主觀惡性的評價也相應降低了,與犯罪的主觀意識明顯不符;在篡改了行為人對其行為危害性的認識程度的同時,也使刑法的主客觀一致的原則遭到破壞;違反了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從而造成罰不當罪。因為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的保護客體在我國還是社會管理秩序,真正決定行為對社會的危害程度的還是毒品的數量,毒品的純度雖然也很重要,但是僅在量刑方面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而無實際的決定行為社會危害性大小的意義。因此,不以毒品純度折算毒品的數量,實際上還是根據設立該罪的目的來決定的。
我國刑法中規定的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不以純度折算的做法也獲得了我國澳門地區的認可。如澳門特區在修改相關的禁毒法律時就主張,應當參考內地《刑法》所規定的以查證屬實的毒品數量計算,不以毒品的純度計算的規定。制定明確、可行又能達到有效打擊毒品犯罪目標的刑事法律規范。[4]
至于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當走私、販賣、運輸、制造行為涉及到不同的毒品種類,如何折算時,有論者就指出,“關于混合型毒品犯罪的量刑:絕大多數同志認為,根據我國從嚴打擊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混合型毒品犯罪的量刑應當以‘毒害說’為主,以‘數量說’為補充,即按混合毒品中危害性最大的毒品種類為標準來定罪量刑,當混合毒品是由多種毒性相當的毒品合成時,則按照數量最多、比重最大的毒品種類為標準來定罪量刑。在具體量刑時,還要考慮毒品的純度問題,即結合上述處理毒品的純度與量刑的關系之原則來具體確定適用的刑罰。少數同志主張‘折算說’,即認為混合型毒品犯罪應當以某一有明確量刑標準的毒品為參照物,將混合型毒品按一定比例折算,然后按照參照物的標準量刑,但鑒于目前不同毒品的折算標準尚未出臺,執行亦有困難。”[5]筆者認為,該論者所說的客觀困難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因為公安部已經出臺了一個解決不同類毒品的換算標準問題的文件,這種將其他種類的毒品換算成海洛因的形式,更能保證定罪量刑的統一性。
具體而言,以下幾類常見的新型毒品與海洛因之間的換算如下:
1克海洛因=20克氯胺酮(化學名稱:2-(2-氯苯)-2-甲氨基環己酮,俗稱K粉)
1克海洛因=20克美沙酮
1克海洛因=10克替甲基苯丙胺(MDMA)(化學名稱:N,a-3,4-亞甲基二氧基甲基苯丙胺,俗稱搖頭丸、迷魂藥)
1克海洛因=10克替苯丙胺(MDA)(化學名稱:a-3,4-亞甲基二氧苯丙胺,俗稱搖頭丸、迷魂藥)
1克海洛因=1000克三唑侖(化學名稱:1-甲基-8-氯-6-(2-氯苯基)-4H-〔1,2,4〕三氮唑[4,3-α]〔 1,4 〕苯并二氮雜卓,俗稱藍精靈、海樂神)
1克海洛因=1500克安眠酮(又稱甲喹酮)
1克海洛因=10000克氯氮卓(化學名:7-氯-2-甲氨基-5-苯基-3H-1,4-苯丙二氮雜卓化合物,俗稱利眠寧、綠豆仔)
1克海洛因=10000克地西泮(又稱安定)
1克海洛因=10000克艾西唑侖(又稱舒樂安定)
1克海洛因=10000克溴西泮(又稱寧神定)
二、法定從重情節
《刑法》第347條第6款規定:“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從重處罰。”
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從重處罰。“利用”是指欺騙、蒙蔽未成年人犯本款規定的行為,犯罪人與被利用者之間缺乏共同故意;而“教唆”是灌輸犯意,即利用各種方法,如勸說、利誘、授意、慫恿、收買、威脅以及其他方法,將自己的犯罪意圖灌輸給本來沒有犯意或者雖有犯意卻不堅決的人,使他人決意實施自己所勸說、授意的犯罪,教唆者和被教唆者對所實施的犯罪主觀上是有認識的。利用和教唆的區別在于前者使未成年人作為犯罪手段而不告知為毒品犯罪,以隱瞞真相的方法使他人成為被利用的犯罪工具;而后者則是告知真相,但是以各種方法促使他人在此基礎上實施毒品犯罪。
《刑法》第356條規定:“因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過刑,又犯本節規定之罪的,從重處罰。”
三、毒品數量累計計算的方法
我國刑法第347條第7款規定:“對多次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未經處理的,毒品數量累計計算。”應當說,這一條款的存在使我們在確定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的毒品數量時有了重要的指導性根據。
(一)行為人每次實施犯罪行為時,必須具備相應的刑事責任能力
對行為人實施的毒品犯罪數量累計計算,意味著行為人每次實施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行為時都必須具有可歸責性,這就昭示了行為人在實行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等行為時,都必須具備刑事責任能力。換言之,行為人每次的行為均可以獨立地構成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否則,因主體不適格而不成立相應犯罪的,就不可能進行累計計算。
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的主體包括自然人與單位。關于自然人的刑事責任能力,我國《刑法》作了規定,尤其是對刑事責任年齡,更是從規范學角度作出了嚴格劃分,即販賣毒品罪的自然人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為14周歲,走私、運輸、制造毒品罪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則為16周歲。從這個角度看,自然人在實施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時,只有符合《刑法》這一條件,才能追究刑事責任,即適用刑法第347條第7款。
根據刑法理論,單位成為犯罪主體的,只能以相應條文有明確規定為限,否則,只能追究相關自然人的刑事責任。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的主體可以是單位,按照《刑法》的規定,單位犯本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依照各該款的規定處罰。因此,單位和被追究刑事責任的責任人員,在追訴時效之內,又犯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的,都應當按照《刑法》第347條第7款進行處斷,累計計算毒品的數額。對于被追究責任的單位和直接責任人員以外的其他成員,則不能適用本款。
(二)前后的犯罪行為都必須在追訴時效之內
“毒品數量累計計算”這個規定,還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即相繼的行為都必須在追訴時效之內,否則沒有“累計計算”規定適用之余地。
我國《刑法》第87條對追訴時效做了規定:“經過下列期限不再追訴:(一)最高刑為不滿五年有期徒刑的,經過五年;(二)最高刑為五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的,經過十年;(三)最高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經過十五年;(四)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二十年。如果在二十年以后認為有追訴必要的,須報請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
在實踐中,多次從事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行為的,基本上都是數量不大的零星販毒行為,從法定最高刑看,這些行為的追訴時效一般都在5年、10年,而經過5年、10年后再實施上述犯罪的并非罕見。
我國《刑法》第89條第2款規定:“在追訴期限以內又犯罪的,前罪追訴期限從犯后罪之日起計算。”這表明,追訴時效的中斷以在追訴期限內又犯罪、或者因被害人的告訴或者公安機關立案等為條件,至于后罪為何種犯罪,應受何種刑罰處罰,則不問。根據《刑法》的規定,追訴時效中斷,前罪與后罪的追訴時效起算的時間均為“犯后罪之日”。犯后罪之日,就是后罪成立之日。[6](691)后罪作為時效中斷的條件,一方面影響前罪時效的計算,另一方面后罪也有一個時效計算的問題。在時效中斷的情況下,不能忽略后罪的時效。
于毒品犯罪而言,在前后行為之間,穿插進了其他犯罪的,可能使訴訟時效中斷,從而使經過的時效歸于中斷,追訴期限從規定事由發生之日起重新計算。如張某在14周歲時販賣冰毒15克,在其19周歲時,張某又盜竊了他人1600元錢,那么對張某的追訴時效就可以達到34周歲,而非24或者29周歲。如果在14周歲后、34周歲前犯走私、販賣毒品行為的,行為人具備相應的刑事責任能力,則可以對其走私、販賣、運輸、制造的毒品數量累計計算。
在司法實踐中,要想使追訴時效擴張,可以通過縝密地判斷行為人前后的走私、販賣、運輸、制造行為構成連續犯,則追訴時效就能得到延長,因為連續犯使初始的行為與最后行為的時效均從后行為結束之日計算,不論前后行為之間的間隔時間,而一般的犯罪則受到前后之間追訴時效的限制。根據《刑法》第89條第1款:“追訴期限從犯罪之日起計算;犯罪有連續或者繼續狀態的,從行為終了之日起開始計算。”對于毒品犯罪,只要是連續犯,其時效的起算就是連續行為終了之日,這樣,追訴時效就能得到延長,毒品數量累計計算的訴訟成本就能降低。
所謂連續犯,主要是指出于同一或概括的犯罪故意,連續實施數個獨立成罪的犯罪行為,觸犯同一罪名的情形。從刑法上選擇性罪名的本質看,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屬于選擇性的罪名,其分割開來屬于獨立的罪名,犯罪名稱雖然不同,但犯罪構成卻是同一的。于公安機關而言,若要查證屬于連續犯,突破口在于證明具有同一或概括的犯罪故意,即以連續的數行為實施犯罪。在主觀上,于開始犯罪時,為了完成預定的犯罪計劃,或者為了實現一個總的目標,或者預見總的結果。[6](696)在毒品犯罪中,連續犯在犯罪集團等犯罪形式中表現得比較明顯。對于這些行為,只要在客觀上查明屬于某個毒品犯罪集團,均可將之作為連續犯論,追訴時效就以連續行為終了之日起算。
依照我國臺灣地區的刑法,連續犯的概括故意,本質上是數個故意,但數個故意同時產生,互相結合而不可分。并且根據第56條連續數行為的要求,數個故意必須在相連接的時空里實現,時空的連接密度如何,至今學說和實務中未提出具體標準,這也是如何認定連續犯最大的難題。數個故意的類型也因為“同一罪名”的條件而受到限制,能結合成一體的數個構成要件故意,根據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52號解釋,必須是構成要件相同的故意才能結合。而何謂構成要件相同,最高法院對此明確說明:(1)肯定構成要件相同者有:①既遂犯、未遂犯、預備犯、陰謀犯之間,單獨犯、共犯(包括教唆、幫助犯)之間。②結合犯與其基礎之單一犯(例如強盜故意殺人與強盜)之間。③屬于加重類型者。④屬于加重結果者。(2)反之,不屬于相同構成要件的則有:①在同一法條或者同一項款中,如其犯罪構成要件不同時,不得成立連續犯。②結合犯與相結合之單一犯(例如強盜故意殺人與殺人)不得成立連續犯。③擬制之罪與真正之罪不得成立連續犯。④觸犯刑法之罪與觸犯刑事特別法之罪,或觸犯兩種以上刑事特別法之罪,除其犯罪構成要件相同者外不得成立連續犯。⑤此外,過失犯無犯罪之故意,不發生連續犯問題。[7]應當說,這一觀點值得我們借鑒,畢竟其操作性強于我們的抽象規定,如“同一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這樣的規定雖然從理論上可以解釋,但在實踐中真正操作起來非常困難。
目前,零星販毒在我國邊遠地區猖獗。尤其部分婦女以攜帶小孩作為掩護,長期從事販毒活動,這完全符合職業慣犯的特征,應從販賣毒品的連續行為終了之日,即被抓獲之日開始計算追訴時效,對其販賣的數量累計計算,從而遏制該類犯罪。
(三)“未經處理”的含義
表面上看,“處理”的外延非常寬泛,它包括行政處罰、刑事處罰,還包括民事處理等,但于危害性較大的毒品犯罪,人們可能將其限定在刑事和治安處罰的范圍內。[8]筆者認為,這一看法存在片面性,因為,如果對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適用治安處罰,則顯然是不恰當的,前文申明:“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無論數量多少,都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予以刑事處罰。”對該行為只能追究“刑事責任”,給予“刑事處罰”。如此看來,這里的處理就只能是刑罰方法,如果行為人已經被進行了行政處罰,筆者的意見是傾向于認為其屬于“未經處理”的范疇,而應當對其數額累計計算,至于其已經受到的治安處罰,可以折抵相應的刑罰處罰。這樣既保證了刑法適用上的統一性,也能保證對毒品犯罪嫌疑人的打擊,防止實踐中出現個別部門以罰代刑的做法。
因此,從我國《刑法》對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的規定來看,刑法第347條第7款規定的“未經處理”只能是指沒有經過刑事處分。
四、毒品犯罪的刑罰適用趨勢——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之提倡
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近幾年我國刑法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而且該問題確實是對我國長期的嚴打政策的一個反思與總結。在世界范圍的刑罰輕緩化形勢下,著眼于當前我國毒品犯罪的現狀,提倡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所謂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首先意味著應當形成一種合理的刑罰結構,這是實現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礎。[9](356)從當前我國刑法對毒品犯罪的刑罰配置來看,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的最高法定刑是死刑,其最低的法定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從刑罰結構看,是比較合理的。但是,從整體上看,其刑罰還是偏重的,因為《刑法》第347條第2款明確列舉了一些法定的可以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五種情形。事實上,在司法實踐中,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率也是相對較高的,其適用率可能僅次于故意殺人、爆炸等少數幾類嚴重的暴力犯罪。可見,我國對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無論是從立法上,還是從司法上看,均呈現出“嚴”的特色,這與當前世界范圍的刑罰輕緩化趨勢是不符的。我國學者也認為死刑一般只應適用于少數幾類嚴重的暴力犯罪。如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現階段,非暴力犯罪死刑的逐步廢止應首先被提上日程,尤其對于非暴力犯罪中沒有具體被害人的犯罪和對其他人人身基本權利不存在潛在危險的犯罪,完全應該通過立法即行廢止其死刑。”[10]而毒品犯罪恰恰屬于沒有具體被害人犯罪的范疇,因此,對其廢止死刑是符合現代刑事法治的發展趨勢的。
實際上,世界各國對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還是持相對緩和的處理態度的。如1988年《聯合國禁止非法販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物公約》要求,各締約國要采取必要措施使這類犯罪受到充分顧及其嚴重性質的制裁,確保對這些犯罪的執法措施取得最大成效,并適當考慮到需要對此類犯罪起到威懾作用。[11]但是,該《公約》卻并不主張對嚴重的毒品犯罪適用死刑,其第3條規定:“各締約國應使按本條第1款確定的犯罪受到充分顧及這些罪行的嚴重性質的制裁,諸如監禁或以其他形式剝奪自由,罰款和沒收。”事實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運用刑罰打擊毒品犯罪時都沒有動用死刑,即使在毒品最大的消費國——美國,毒品犯罪最嚴厲的刑罰也僅僅是30年監禁;在毒品犯罪非常嚴重的德國最重的處罰也只是 15年自由刑;在日本處罰最重的是10年懲役。對毒品犯罪規定死刑的國家在世界上占極少數,它們多為亞洲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如越南、老撾、泰國、中國等。[12]雖然在廢除死刑的國家對毒品犯罪一般也處以最嚴厲的刑罰方法,但是,從本質上其還是否定了對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
在中國等亞洲國家,對毒品犯罪實行死刑,是在當前毒品犯罪日益猖獗的形勢下所作出的無奈之舉,此外,多年以前鴉片戰爭的慘痛教訓也堅定了中國政府嚴厲打擊毒品犯罪的決心。但是,伴隨著刑法發展的日趨理性化,對毒品犯罪的刑罰選擇也應當有所調整,因為刑罰輕重不僅受到政治理念的影響,同時還受到刑法理念的制約。從刑法理念上來說,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雖然具有一定的策略內容,但其刑法的理念基礎應當是刑法謙抑。[9](364?365)謙抑性已經被我國刑法學界廣泛接受,如何在現行法律體制下貫徹這一理念,就成為司法者的神圣使命。
我們相信,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人們對毒品犯罪的容忍度也會出現一個逐漸寬容的過程。當前,從司法上逐步減少毒品犯罪的死刑適用可能更加符合社會現實。
注釋:
①如法官在“劉德明”及“程德雄”案件中確立毒品數量與刑期的關系,確立了量刑的基本標準。有關判例中,判決書所認定的精神科物質或制劑的重量。具體參見趙奕:《澳門特區禁毒政策與法規——有關毒品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中國藥物濫用防治雜志》2003年第3期。
[1]雷文.毒品犯罪案件中的幾個法律適用問題[N].人民法院報,2003?06?07,(A6).
[2]酈毓貝.毒品犯罪司法適用[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5:8?9.
[3]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 386.
[4]趙奕.澳門特區禁毒政策與法規——有關毒品犯罪的法律適用問題[J].中國藥物濫用防治雜志,2003,(3): 25?28.
[5]王軍,李樹昆,盧宇蓉.破解毒品犯罪法律適用難題——毒品犯罪法律適用問題研討會綜述[J].人民檢察,2004,(11):30?32.
[6]馬克昌.刑罰通論[M].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
[7]許玉秀.當代刑法思潮[M].北京: 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 322?323.
[8]肇恒偉、關純興.禁毒學教程[M].沈陽: 東北大學出版社,2004: 191.
[9]陳興良.走向規范的刑法學[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7:356.
[10]趙秉志.論中國非暴力犯罪死刑的逐步廢止[C]//陳興良,胡云騰.中國刑法學年會文集 2004年度——死刑問題研究(下冊).北京: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 781.
[11]張智輝.國際法通論[M].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46.
[12]任志中,汪敏,毒品犯罪案件死刑適用的司法限制[C]//陳興良,胡云騰.中國刑法學年會文集2004年度——死刑問題研究(下冊).北京: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 782?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