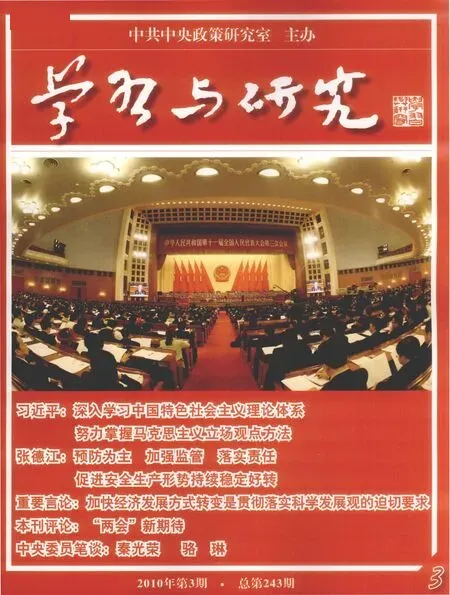陳訓慈歷史教學思想初探
吳忠良
(浙江工商大學,浙江 杭州 310018)
陳訓慈歷史教學思想初探
吳忠良
(浙江工商大學,浙江 杭州 310018)
陳訓慈一生多次與教育結緣,誨人不倦。對于歷史教學,他一直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主張改革當時不良的歷史教材,力主中小學歷史教師努力借鑒國際先進教學經驗,崇尚以民族主義為中心的中小學歷史教學目標。陳訓慈的教學思想最終為當時學界所認可,主持編制了《初級中學歷史暫行課程標準》,對此后的中學歷史教學產生了較大影響。
陳訓慈;歷史教學;教學標準
陳訓慈(1901-1991),浙江慈溪人,歷史學家、圖書館事業家。他自1924年任教寧波效實中學始,先后在浙江省立第四中學、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江蘇省立南京中學、中央大學、浙江大學等校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所授課程為中國近代史和西洋近代史,上世紀40年代還出任民國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委員。在近20年教學研究與實踐中,陳訓慈積累了大量的歷史教學經驗,提出了不少卓見,并為當時的民國學界所認可。遺憾的是,由于各種原因,學界尚未對陳訓慈進行專題研究,這與他在近代浙東教育史上的地位極不相稱。研究陳訓慈的教學思想與實踐,對于當下的歷史教學依舊具有較高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教材改革
教材是教學之本,是師生進行教學活動的最主要的材料和依據,集中體現著教育目標,直接關系著人才培養的規格與水平。而自從清末翻譯日本和西方歷史教科書以來,許多中小學采用的歷史教科書依舊不改以前面貌,因襲守舊。雖出現了如夏曾佑《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這樣的佳作,但它并未在中學中得到廣泛應用。針對當時國內研究歷史教學之人甚少,所用教本甚差的現象,陳訓慈指出:“近數十年來,學者應接歐化,益無深造,史地繁博之學,尤稀人過問。試揆之著述,徵之教育,察之學者之團結,無在不呈荒落之現象”。他“通觀十余年來之出版界,終覺舊學日荒而新智寡聞。出版書籍之以史名者,不為不多,特自輾轉變換之教科書外,殊多稗販抄襲之作,其能薈萃前言,獨出心裁,蔚成專著者,絕不多得。即敘次較詳之國史教本,亦不可見。”反映在具體的學校教育中,所用歷史教本多不再版,再版者又不盡切合,而教師卻大多孤行寡聞,常年照本宣科,大炒冷飯,所授內容多不及當代史,基本上為一戰以前之史,如若時間不夠,甚至尚未述及近代。地學方面,同樣令人擔憂。“調查事業之不興,使本國無一完備正確之輿地。編述者稱引之表計,大致得諸日人或西人之言,而又不能盡量采為己用,或用之不得其當。外國之地理,不必高言分國,但求一敘次略詳之世界地理,尚不可得。戰后世界之改造,吾國終無一書焉以詳敘現狀。輿圖出版者不為不多,而其間大多出之模擬。即此抄襲模擬,猶有未能盡善者焉。”“中小學之歷史地理二科,其教本之不良,與教師之多不勝任,皆不容諱言之事實”[1]。
如何改變此種不利形勢?陳訓慈認為中國史學界應盡速開展史學運動,通過史學運動來對中小學校的歷史教學進行統籌改造,并進而謀求歷史常識到普及。具體到實際操作,陳訓慈認為當下中小學史地教學須改良處可以從三方面著手:中小學史地教本之編纂;史地教員之檢查,或設法補濟其缺,如設補習學校;設法普及國民之史地常識。上述三端在以后成立的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的具體工作中得到了很好體現。民國時期的史地教育委員會關于改進中小學史地教育的主要事項就以調查中學史地教學,中學史地師資之訓練,審查中等學校史地教科書,編纂中國史地書籍等項為主要事業。
編纂優良的中小學歷史教本和進行師資培訓,都需要學有專長的專家和學者來擔任。如若一些學術素養不深的人來從事這方面的工作,那效果可以想見。1922年夏天,中華教育改進社在濟南舉行年會,歷史和地理都自成一組,云集了當時大學歷史教授與地理教授以及其他學者,于史地教學頗有所商榷。如徐則陵提議“研究關于中小學歷史教學問題”,何炳松提議“編輯或講授歷史,應以說明歷代社會狀況之進化”,梁啟超提議“中學國史教本改造案并目錄”,認為“現行之教科書及教授法,實不能與教育目的相應”,柳詒徵對中小學歷史學做了商榷等[2]。陳訓慈認為歷史教學的改進,本來就不是泛泛教育者所能主持,必須集合專家的討論方能進行;如是,方能取得歷史教學的改良。編纂中小學歷史教本也是同樣,非集合專家學者討論進行不可。
二、借鑒國際先進教學經驗
在呼吁學界重視教科書編撰同時,陳訓慈也非常重視國外足資借鑒的名著和先進的教學經驗。如陳訓慈在介紹美國亞丹博士(G.B.Adams,Ph. D)著《英國憲政史》時,稱此書內容共分若干章:(1)盎格魯撒遜民族之政府(2)諾曼征服之封建時代(此節最佳)(3)Lancastrian與Yorkist時代(比較稍遜)(4)Turdor時代(5)Stuart時代與國會之勝利(6)十八世紀與內閣制(7)十九世紀與普通選舉及民治政府之成立(案英雖君主立憲,實已民治)(8)近今之英國憲法。“每章皆敘次中肯,故其全書能臻美善也。”所以“此書從各方面觀察,實為教科用之良書”。因為,“近來教科書之作者大都為有學之士;故取材之豐,批評之切,解釋之精審,幾為共有之長。然事物之意義之真正說明,則往往為普通教科所不及”。而此書“不但盡有上述之長,且能有全部之智識,與堅實之見解,實非初事著作者可幾。書中取材,非不詳贍,顧于事實之外,猶能為重要原則之說明;初非繁重堆積,無結論綜觀者比也。故此書不但可為教科,且可為編書者取法。全書簡潔清晰,文體亦雅馴可讀。”[3]
在介紹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漢斯著的《近世歐洲政治社會史》時,陳訓慈指出:“吾國之講求西史雖久,而專精之著述寡聞,是以國人至今但知中西關系之切,而對于歐洲各國進化之大概,稀能有明確之觀念。大戰以后世界之問題益復,往往瞬息變幻,莫知其故。蓋一事之發生,無不有其已往之背景,故欲領解近來事變之意義,‘至少須熟習歐洲近四五百年來之事實’,是則歐洲歷史中之近世部分,尤為今日世界公民之常識,而‘列強逼處’中之中國人,更不能不亟加注意也。”遺憾的是,當時國內“關于歐史之書籍,國內坊間無佳本;即西籍之中,吾國通用之書,亦多有偏枯敘述不適于用之患。(中等學校用西文教本者,如Colby,Renouff,及Robinson與Beard之書,多陳舊不可用。)”而漢斯之書則堪稱佳構:“融貫人事之各方面,無偏重政治或社會之弊”、“長于敘次之觀念與方法,使讀者得了解之最高之效率”、“表達之流暢、清晰,與生動”,且“全書不涉繁衍,更非疏淺,詳略得中,足供國人之需”。陳訓慈認為該書三大長處很值得中國史學界借鑒。當時中國學界存在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了強調自身史觀之新,重視民史、社會史,而忽視甚至排斥政治史,從而人為地割裂了歷史,以致所編教科書無系統可言。他說:“舊史家以歷史為‘過去之政治’,故于通常社會人生,忽焉不述;好新之士,又往往側重社會,忽視政治,以為帝王世紀,無與民生。”如此,就造成了“往昔之歷史課本,(textbook)大率疊累事實,不能融貫闡發。故讀者但見事實之堆積,不明起伏之故;索然寡味,以為于今無涉”。近來作者,“雖已知采社會事實,然多分離成章,不能見其關聯。是又非真能兼述二者”。而《近世歐洲政治社會史》的作者,“固認定政治活動,大部分受經濟及社會所支配,故既常以專章述社會方面之變遷,且于全書之政治事實,咸注意其社會的背景。然同時彼又‘深信政治活動出于人之本能,而于人類關系最為普遍’。(序文第七頁)故于帝王議會,乃至政事戰役,無不加相當之注重,而不欲疏略。此其不偏不激,融通全局,實代表最真實之新史觀”。“其于政治史及社會史,確能連貫之使成真實之綜合也”。在此觀點主導下,漢斯采用縝密之方法,對材料加以取舍整理,內容變得豐腴生動,干枯之事實頓陳新意。陳訓慈不禁感嘆到:“吾國學者稍聞社會史之意義,動以為忽棄帝王政事,乃新史注重社會必取之手段。不知真正史家,固仍注意政治事實,不因噎廢食也。”此外,他還指出了該書在編纂上的優點:“(1)、目錄之詳備,列有說明之參考書目于每章之末.其所列種數之豐多,與說明之周賅,實他書所罕見;讀者進欲研求,可即此求極良之導師;(2)、插圖之美備;(3)、腳注之互著;(4)、索引之詳審;(5)、標目之精密能賅,實為歷史課本中不可多得,有助于讀者之觀覽及溫習參查之便不少也”。因此,他強烈建議,“全國中等學校之歷史教習,務各備一卷,以供近史之參考”[4]。
具體的歷史教學中,陳訓慈主張學者或教員重視插圖和歷史掛圖等圖表的作用,在《史地學報》一卷四期的“書報紹介”欄內特意介紹了美國學者Shepherd的《歷史地圖》,希望能引起中學歷史教員的重視。內云:“近來國中學者及學校教科,漸知趨重西史,然地圖缺乏,輒為大患。坊間編譯,多忽插圖(或無之,或有而極簡陋)。美國近來出版歷史地圖,集群籍之成,可供學者參稽者,Shepherd之歷史地圖其一也。此書明晰新穎,詳略適當,縱有小失,無傷大體,有志歷史者,頗可采用。中等學校歷史教員,為學為教,尤不可不人手一本也。”
他還譯述了美國葛爾綏教授(Prof.R.W. Kelsey)的《戰后之德意志歷史教學》以為本國歷史教學之借鑒。該文內容分為“大戰對于學校歷史教學程之影響、近世史之特重、大學校中近世史學程舉例、國際諒解問題之解答、教員之經濟狀況、反對民主之觀察”六個方面,由此“可見德國大學校中歷史教學之概況,更可知最近德國之史學日漸趨重近世史”,“以俾國人得有外邦史學界之一瞥”。在文末“譯者按”中,陳訓慈認為,就文中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對于德國歷史教學又二種最顯著傾向,一為近世史之趨重,二為民主之反動。對于近代史的重視,將導致許多古代史研究專家轉移學術陣地,此為史學之一劫;對于民主的反動,直接則為民主之推翻與王政之恢復,間接則為民族主義之重盛。“蓋歷史既為學者目前鼓吹之手段,或且成異日德意志重吐積緒之導因。是則歷史為政治役屬之運,猶未有已,而世界史之企圖,將欲以打破民族間之偏見者,終不可期。此又新史學之一大劫也。”雖有此二劫,陳訓慈認為“此不足憂”。因為,古史研究仍有一部分德國人從事,“而近世史之整理,或且經德意志沉潛有統之頭腦,更形堅實精邃。矧新歷史之前途,固將與現實問題益相攜手,誠得德意志著名史家倡導而躬行之,其成就何可限量。繼今政治外交乃、至實業教育,必因近世史之研究,與歷史關系尤密。則此種傾向,豈非足提高歷史之新價值乎?”至于歷史為政治或民族觀念所役屬,“則吾人不能不望德國學者翻然自省,勿令學術牽入政治漩渦。縱欲重視國史,同時當不忘世界史之研究。而各國學者,尤不當因德國此種傾向,貿然棄其新理想,使萌蘗之新歷史,更受巨大之打擊也。”[5]換言之,在陳訓慈看來,歷史教學應當注重近世史之教學與民族觀念之灌輸,這有助于新史學的發展,但在新的世界背景之下,注重國史的同時不能忽略世界史。顯然,他考察的雖是德意志之歷史教學情況,意欲表達的卻是對于本國歷史教學的建議。
三、以民族主義為教學目標
陳訓慈關于歷史教學方面的理論得到了學界的承認和重視。1928年秋,大學院組織中小學課程標準起草委員會,其中初中歷史課程一部分,委托何炳松、顧頡剛與陳訓慈三人起草。(高中部分因教授科目未制定暫緩)三人中,陳訓慈年齒最幼,起草執筆重任由陳訓慈擔任似是順理成章的。當時顧頡剛遠在廣州中山大學,陳訓慈未能相與商討;而何炳松處“則曾面就商榷,示以意見若干點,而以屬筆之役相責”。陳訓慈根據自己對中學歷史教學的理解,結合自身的教學經歷和何炳松所提意見,其間又曾得向達幫助,于該年12月草成《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草案》。因《史學雜志》于1929年創刊,“同人以專究與應用不偏廢相期,因謂關于歷史教學方面之文字不可缺”,故而陳訓慈對草案內容次序作了更改,內容復增以說明,與原草案已經有較多出入,所以發表之時并未合署何炳松之名。《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草案》內容分為:一、目標,二、時間支配,三、教材大綱,四、教法要點,五、作業要項,六、畢業標準。該草案結合教學實際,拋棄了在中學教學實踐中失敗了的“混合教學法”,采用分別教授的方法來講授中國史和世界史,其理由如下:1、中西民族,在十六世紀以前為個別發展,其史跡關聯甚少。混合編制與教授,無法尋繹其間相通之線索。即使在近世,雖然多共通之事,但仍復自為系統,若必牽強附和,雜然并舉,勢必強為遷就,失去歷史之真相。2、世界史之提倡,由來已久,至一次世界大戰后而益盛。然混合中外歷史為一世界史,是否能包羅普及妥善,盡史學之效能,尚為史學界一大問題。3、世界史之混合雖非易,但綜合比較,考古代之關系,明現代史事之連貫,亦讀史者應有之本分。但這要求讀者必須于中外史實已有相當之根基,方克從事。如果中學學生在小學學習階段,國史僅聞故事,西洋史所知更鮮,(甚有全未教過者)升入初中,基本知識尚待灌輸,若馬上混中外為一家,求其通貫,自將感凌亂無序,茫然不解矣。“要之照現行混合史之理想,實非初中學生程度所能及,將欲使學生明人類文化演進之共同狀況,結果將局部而不能曉,并基本常識而不易得矣。據此種種理由,歷史混合教法實屬困難,至少在初級中學中已無存在之余地。”[6]這實際上否定了常乃德草成并于1923年頒布的《初級中學歷史課程綱要》。
與此前撰寫《五卅痛史》、《近世歐洲革命史》等書時注重發揚民族主義精神一致,對于中學歷史教學主要目標,陳訓慈明確指出,首要教學目標當為“研求中國政治經濟變遷之概況,說明近世中國民族受列強侵略之經過,以激發學生之民族精神,并喚醒其在中國民族運動上責任的自覺”。對此教學目標,陳訓慈有所說明:“本草案目標第一項即標明激發學生之‘民族精神’,誠以民族精神,為現代民族生存之要素。而在不平等條約未廢除,中國尚未達到國際上之自由平等以前,即國民革命之全功未竟,歷史課程尤當注意及此。”[6]對于陳訓慈所擬定的歷史教學主要目標,有論者指出:“這個教學目標方向明確、觀點鮮明、要求恰當、層次分明,是以前的目標所不能比的。它既指明了歷史是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又強調了古今中外歷史互為聯系的因果由來,還提出引導學生學習歷史‘服務人群’,‘培養高尚情操’與‘增進其觀察判斷的能力’的要求,更顯出歷史教育的功能。尤其是目標指出要‘激發學生的民族精神’,‘養成其遠大的眼光與適當的國際同情心’及‘培植學生國際的常識’。在當時這樣的目標不僅符合歷史學科特點.而且富有較強的時代感,在中國近代歷史教育發展過程中是一重大進步。”[7]p28該《草案》于1929年以《初級中學歷史暫行課程標準》之名頒布實施,其中內容與陳訓慈單獨發表之《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草案》大同小異,所異處基本上是陳訓慈所增之說明。該《標準》的頒布實施,是對陳訓慈史地教學理論和實踐的最大認可。
在陳訓慈的教學生涯中,他也是很好地貫徹了此類思想,如在中央大學歷史系講授中國近代史課程時,口講指畫,慷慨激昂,整個課中貫穿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令聽者為之動容。堅持民族主義為中心的教學目標,在陳訓慈整個教學研究生涯中是一以貫之的,上世紀30年代主政浙江省立圖書館時,他依舊關注歷史教學。在《歷史教學與民族精神》一文,陳訓慈就指出,訓練學生了解人類社會一切事物之由來與演進,陶冶其不虛不夸正大光明之思想與德行,鍛煉其適應環境與解決問題之能力,輔益各學科智識的完成,皆為歷史教員應注意之事;但“吾人就人類社會組織之由來與現狀觀之,由今日各國史地研究之趨勢推之,則知歷史教學之主要目標,尤特應顧及其民族本位之意義也”。雖然提倡民族主義會有很多流弊,但善用之足以固民族之自衛,而絕無損人利己之弊。“吾人于今日中國歷史教學許多目標之中,不能不確認其中心目標,乃在充分表達中國民族之由來變遷與演進,說明世界各國演進之大勢,而與本國相印證,直接間接以加強學者之民族意識,以激勵其為本國民族之生存與繁榮而努力。”他還重點介紹了歷史教學中闡揚民族精神應注意之要點:(1)講明中國民族為整個的重于說明其悠久與優越;(2)表揚先民之忠烈應勿忘貶斥前代之奸惡;(3)頌美救國之實行而同時糾責虛憍空談之士習;(4)表彰任重助成之庸德急于褒稱卓犖開創之特行;(5)推闡鄉土之民族史跡不背于整個民族精神之發揚;(6)以國史激發民族的自覺應輔以外國史之聯絡與印證[8]。陳訓慈的言論得到了浙江圖書館館員們的熱烈反應,如李絜非就撰寫了《中國男兒文文山先生》,認為文天祥(文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自強不息”的精神最可佩,為中國立國之真精神,需發揚光大[9]。學友繆鳳林也認為中學國史教學的目標即在于:“從講習國史,以喚醒中華民族的自信心,振起中華民族精神,恢復中華民族墮失的力量,達到結合國人成一堅固的民族之目的,以挽救當前的危局,使中華民族永遠存在而已。”[10]
歷史誠然需要有人進行高深研究,但她同樣需要有人進行通俗的普及工作。對于激發民眾愛國心和彭湃的民族情感而言,歷史教科書之功能不可小視。但清末民初的歷史教科書編譯存在很多問題,大多為急就章性質。夏曾佑的《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后改名為《中國古代史》)于1933年被商務印書館編入《大學叢書》再版,就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當時歷史教科書質量之一斑。而抗日戰爭前的史學界,學者都將目光投向專的方面,忽略了通的方面。顧頡剛反省說:專家的研究“是史學界的基石,萬萬缺少不得”,而普及者卻是“接受專家研究的成果,融會貫通之后,送給一般人看。……喚起民族意識,把握現代潮流,都靠在這上了。”將來的史學應當“兩條路都走,兩種人才都培養,然后可以學盡其用。”[11]p327陳訓慈既于史學理論有較深研究,又于歷史知識的普及多所著力,更顯得難能可貴了。
[1]陳訓慈:《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史地學報》第2卷第3期,1923年3月。
[2]《今夏中華教育改進社關于史地教育之提案及歷史教育組地理教學組之會議記錄》,《史地學報》第2卷第1期,1922年11月。
[3]陳訓慈譯:《史學書紹介四則》,《史地學報》第1卷第3期,1922年5月。
[4]陳訓慈述,【美國】漢斯(Carlton J·H·Hayes)著:《近世歐洲政治社會史》(APoliticaland SocialHistory of Modern Europe(1500—1914)),“新書紹介”,《史地學報》第2卷第2期,1923年1月。
[5]陳訓慈譯、[美]葛爾綏(R.W.Kelsey)著:《戰后之德意志歷史教學》(History Teaching in Germany),《史地學報》第2卷第2期,1923年1月。
[6]陳訓慈:《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草案》,《史學雜志》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
[7]馬衛東主編:《歷史比較教育》,廣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8]陳訓慈:《歷史教學與民族精神》,《圖書展望》第1卷第4期,1936年1月。
[9]李絜非:《中國男兒文文山先生》,《圖書展望》第2卷第2期,1936年12月。
[10]繆鳳林:《中學國史教學目標論》,《教與學》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
[11]顧潮:《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責任編輯 梁一群)
K20-42
A
1008-4479(2010)03-0115-05
2010-01-02
吳忠良(1977-),男,浙江富陽人,歷史學博士,浙江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