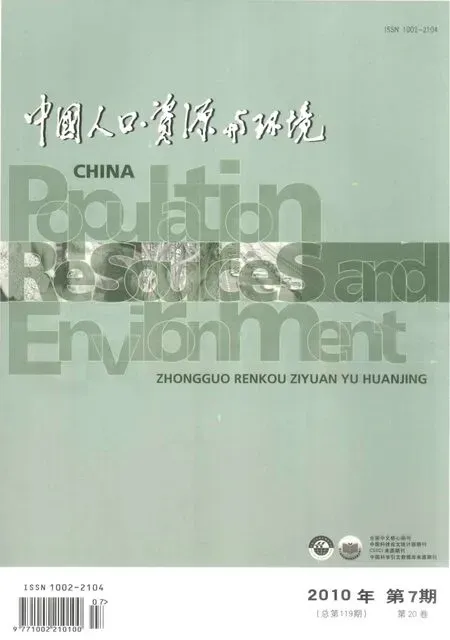戶籍制度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制約與完善*
鄧海峰 王希揚
(清華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84)
戶籍制度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制約與完善*
鄧海峰 王希揚
(清華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84)
土地承包經營權物權化的根本意義在于使這一權利作為財產,在市場上自由流轉,我國于2007年頒布實施的《物權法》已經為此創造了堅實的制度保障。但是就目前來看,我國初具雛形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仍然存在著外部的制度缺陷。其中,戶籍制度作為一套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和完善起來的社會管理制度,嚴重阻礙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以至于使得這一制度所應發揮的基本功能被抽空。因此,本文提出以現行戶籍制度為核心對當前社會保障體制進行改造,從而為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掃清障礙。最初通過“以土地換社保,變農民為市民”的方法,允許進城農民在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的前提下,有資格加入城鎮的社會保障體系之中。進而逐步過渡到取消基于戶籍限制的城鄉二元化模式,逐步構建覆蓋全國范圍的基本社會保障體系,最終實現土地承包經營權市場化流轉制度的基本功能。
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戶籍制度;城鄉二元體制;全國社會保障體系
土地承包經營權,是指公民或集體經濟組織及其成員對集體所有或國家所有由集體使用的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以下簡稱《物權法》)在“用益物權”一編規定了“土地承包經營權”,將這一權利明晰為一種具有財產屬性的用益物權,結束了幾年來對其根本屬性的爭論,進而促進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走向商品化和資本化。法律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提供了穩固的制度保障,繁榮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二級交易市場的形成理應指日可待。
但是,在現實中,土地承包經營權并未如立法者所愿,通過市場交易創造出更大的價值,種種制約因素的掣肘,致使其實踐成效大打折扣。其中,戶籍制度便是諸多亟需克服的制約因素之一。隨著我國完成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戶籍這一形成并發展于計劃經濟時期,以穩定社會、保障經濟建設為目的而建立的舊制度愈發制約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當前,我國正處于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之際,人口的大規模遷移,特別是農民進城務工已經成為與城市化進程相伴的社會趨勢。然而,現行城鄉二元的戶籍制度卻阻斷了作為農民工進城務工配套制度出現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可行性與有效性,致使我國出現了城市化進程不徹底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低效率的雙重不利局面。因此,我們需要在認識和分析戶籍制度與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相互關系的基礎上,提出以戶籍制度改革為核心完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制度建議。
1 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理論基礎與現狀
理論上,土地流轉包括土地歸屬關系的流轉與土地利用關系的流轉兩方面。其中,土地歸屬關系的流轉,是指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轉變,如土地的買賣、贈與、征收等;土地利用關系的流轉,是指在土地所有權不變的前提下,土地利用關系在主體之間發生轉變[1]。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決定了我國的土地屬于國家或者集體所有,不存在土地私有的現象。因此,我國土地權利交易市場的客體為土地使用權,而非土地所有權,土地流轉實際上僅指土地利用關系的轉變。具體到農村土地權利交易而言,主要是指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即在不改變集體土地所有權性質及其農業用途的前提下,土地承包經營權在二級交易市場上發生的權利主體的轉變,包括轉讓、出租、入股、互換、抵押等多種形式。
從現實情況來看,盡管我國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已經初具雛形并日漸成熟,但近年來,這一市場的發展并不如人們所預期之繁榮順暢。事實上,雖然我國的法律與各項配套政策已經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提供了依據與基礎,但現實中各種制約因素仍然在對這一過程發揮著制約作用。一方面,土地承包經營權無法完全走入交易市場,真正作為生產要素供給手段的功能難以發揮,土地資源優化配置難以實現;另一方面,農民通過土地承包經營權獲取資本性收入的預期難以達到。因此,促進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必須減少上述阻礙因素,使土地使用權能夠充分發揮投資功能,在市場經濟中顯示出巨大威力。
2 戶籍制度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制約
2.1 我國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
我國的戶籍制度是以戶口登記與管理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一套社會管理制度,包括常規人口登記和上報制度、居民戶口或身份登記及管理制度,以及與戶口相關的就業、教育、保障和遷徙等方面[2]。在計劃經濟時期,這種社會身份與經濟身份相包容的城鄉戶籍差異在解決社會問題、穩定社會秩序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使中國在建國初期沒有出現西方國家所普現的城市貧民問題[3]。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單一的公有制模式被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模式所取代,城市中的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開始活躍起來。在市場化改革的影響之下,城市居民脫離了國營、城市大集體單位,其依托于國營、大集體單位的經濟身份自然而然地隨之消失,成為了不受所屬經濟組織形式約束的自由人。與此同時,城市居民能夠基于其所具有的社會身份獲得城鎮的養老、失業、醫療等社會保障,使其在自主地選擇職業、居住地的同時毫無后顧之憂。然而,在廣大的農村地區,以還原經濟自由為導向的經濟身份改革未能在農民身上得以實現,同時,社會身份又決定了他們在離開土地、脫離集體經濟組織后沒有新的社會保障來源,因此,農民仍然需要依靠土地維系生存,無法以自由人的身份去尋求更廣闊的發展。可以說,現行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猶如一道無法跨越的藩籬,束縛著城鄉各階層之間的人員流動和信息交換,由此引發城鄉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化走向。
2.2 戶籍制度與土地承包經營權之間的關系
戶籍制度與土地承包經營權之間通過農民所具有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發生聯系。
根據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法》,對于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發包方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承包方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交易僅局限在本集體經濟組織之內。對于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人,取得農村土地使用權可以通過兩種途徑:其一,通過參與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承包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農村土地;其二,從發包方處直接取得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但要受到嚴格限制,“應當事先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會議三分之二以上成員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報鄉(鎮)人民政府批準”。
也就是說,在土地承包經營權初次分配的過程中,只有具備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才能夠以家庭承包的方式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對于非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特別是想要承包農村土地的城鎮居民,只能通過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取得“四荒”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在土地承包經營權二次分配的過程中,如果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為受讓方則不受限制,而受讓方非為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需要取得集體經濟組織一定數量以上成員的同意,并經鄉或鎮政府批準。對于農村人口來講,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經濟身份決定其有資格作為承包方,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簽訂土地承包合同,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而對于非農人口,不屬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取得就要受到嚴格限制。
2.3 現行戶籍制度制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之原因
農村土地對農民具有生存保障與投資的雙重作用,并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土地功能的長期趨勢將呈現為從生存保障走向投資[4]。在此背景下,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實際上具有多重功能:其一,打破原有的靜態財產權分布格局,盤活農村土地資產,刺激土地投資價值的實現,促進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功能的進一步市場化;其二,為打破城鄉二元化的社會結構奠定經濟基礎,為農民的自由流動創造制度可能;其三,為實現土地所承載的農民社會保障功能的貨幣化創造制度支撐。
如前所述,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實現了城鎮居民的經濟自由,但對于億萬農民來講,社會身份和經濟身份都沒有隨之改變,他們的生存仍然需要依靠土地提供最根本的保障、需要依附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現行戶籍制度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根本制約就在于:這種身份差異所引發的更為深層次的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差別導致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三項功能難以實現。分述如下:
第一,現行戶籍制度引發的二元就業制度阻礙農民的自由流動。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迅猛發展,農民工們揮汗如雨的工作場景在城市中隨處可見。盡管如此,由于農村居民的社會身份沒有得到轉變,很多工作崗位都將農民工拒之門外,想要在城市中找到有穩定收入的工作難上加難,例如很多收入高、待遇好的崗位在招工的范圍上有嚴格限制,唯有城市居民才屬于被招用的對象,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只能望而興嘆[5]。在市場化改革下,城鎮居民在經濟身份上擺脫對國營單位的依賴,獲得職業選擇的自由。但對于農民工來講,他們進入城市卻仍然屬于農村村民,社會身份沒有能夠轉變為城市居民。在這種情況下,盡管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為農民的流動創造了制度可能性,但現行戶籍制度導致農民工無法自由選擇職業,使得這種可能性難以成為現實。
第二,現行戶籍制度制約土地社會保障功能的貨幣化。對于農民來講,一方面,土地上之權利作為一種動態財產權,能夠通過市場化流轉的途徑實現價值,促進土地投資功能的發揮;另一方面,作為必不可少的生產資料,土地是農民最基本的生存依靠,負有生活、就業、養老三重社會保障功能。因此,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應當能夠使土地的投資與社會保障雙重功能的價值實現貨幣化。
然而,現實的情況卻并非如此。一方面,農民在轉讓土地使用權后,只獲得了土地作為生產要素的部分資源性價值,土地的級差地租遠遠沒有在土地流轉的對價中反映出來[6];另一方面,土地所承載的社會保障功能的貨幣化未能得以實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社保功能貨幣化實際上是農民進城后基于身份轉變而應當取得的城鎮社會保障,而城鎮戶籍與農村戶籍的區別化使得農民在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后,無法完成由農民身份到城鎮居民身份的社會身份轉化,從而導致農民在退出集體經濟組織,喪失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社會身份后,無法取得城市居民的社會身份,從而不能獲得與城市居民相同待遇的社會保障。這一項對于農民安身立命至關重要的功能無法實現必將造成兩重后果,并且該后果將根本制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
其一,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價值應當囊括土地的兩項基本功能:生存保障和投資,即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應當是這兩項功能轉向貨幣化的過程。然而,土地社會保障功能貨幣化無法實現,直接導致土地承包經營權本身的市場價值大幅減損,由此引發的后果就是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讓的貨幣價值降低,使土地作為生產資料的財產性價值被制度性壓低。長此以往的交替循環就造成了土地承包經營權不值錢的怪現象。
其二,對于很多進城務工的農民,他們早已擺脫了土地的束縛,卻無法擺脫農民的身份,他們走進城市之中,卻無法成為城市的主人。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就意味著將喪失土地這一自然的社會保障基礎,同時他們又無法像城市人那樣享受各種社會福利性救助,一旦遭遇失業將毫無生存保障。而事實上這種狀況已經發生,據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2008年約有2 000萬外出農民工因金融危機失業返鄉,而在這些返鄉農民工中,有1 000萬早已沒有“承包地”[7],他們正面臨著失業又失地的生存問題。嚴峻的現實狀況加重了農民的“惜地”心理,“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的想法愈發根深蒂固,他們寧愿“撂荒也不轉讓”的保守態度,導致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出現有效供給不足,明顯制約著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
可見,現行戶籍制度是直接造成土地社會保障功能貨幣化無法實現的重要根源,也是間接壓低土地資源性價值的重要根源。它使得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的后兩項功能落空,即農民在城鄉間的自由流動受阻,土地社保功能貨幣化無法實現。而建立動態土地資產的第一項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農民的自由流動以及土地社保功能貨幣化的實現。由此,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本應發揮巨大作用的三項功能基本被抽空,而其弊害則是深遠的。
其一,違背建立平等、自由的共同體成員關系的正義倫理。這里所說的社會共同體,主要表現為國家。平等意味著一國之內的所有公民應當享受最基本的權利和受到最基本的保護,國家不應根據人們的出身、職業、居住地等在政策和制度上區別對待公民,而應當對所有公民一視同仁[8]。很顯然,現行戶籍制度無形中造成了戶口身份的高下、貴賤之分,進而引發制度歧視。
其二,阻礙生產要素在市場間的合理流動。市場經濟要求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依靠價值規律的調節在市場上自由流動,現行戶籍制度卻極力限制土地、勞動力在體制內的流動和轉移,而且繼續為各種不平等的行政政策的執行提供依據和條件[9]。這一制度早已與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不相協調,與如火如荼的城市化進程背道而馳。
其三,侵害了國民于城鄉間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這種阻隔不僅表現在阻止農民獲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同時還表現在阻止城市居民購得土地承包經營權,并基于取得土地承包經營權而獲得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身份并享有成員權的可能。
長遠來看,這種制約將造成我國城鄉二元化的社會結構由形式矛盾走向實質矛盾,成倍放大未來改革的成本。
3 戶籍制度改革的制度構造與功能分配
根據以上所述,針對現行戶籍制度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制約,為了使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的功能有效發揮,本文提出以戶籍制度改革為核心的制度建議,根本目的在于協調戶籍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掃除障礙。具體表現為:
第一,農民轉讓土地承包經營權后,需要以新的社會保障方式替代土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從而使土地社會保障功能貨幣化得以實現;
第二,城鎮市民受讓土地承包經營權后,應當避免出現既享有城鎮社會保障,又擁有土地使用權的“超級公民”待遇。因此,土地承包經營權人轉讓權利后如何辦理城市社保接續和城鎮居民購得土地承包經營權后如何實現社保關系的轉移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對此,可以采取以下兩種對策:
其一,徹底取消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體制,實現全國戶籍的統一,進而實行全國一體的社會保障體系。結合國外戶籍管理的經驗來看,戶籍制度的根本功能在于作為公民身份的證明以及國家統計人口的工具。而自19世紀形成以來,我國戶籍制度所發揮的作用已經遠遠偏離了其原初的功能。其實,現行戶籍制度的弊病不在于制度本身,恰恰在于它承載了太多原本不應當具有的社會功能。因此,改革戶籍制度的根本目標在于恢復戶籍制度的單一功能,取消附著于戶籍制度上的種種附加值,使其從區別公民待遇的手段轉變為純粹的公民身份證明和政府人口統計工具。只有建立功能一元化的戶籍制度,才能保證城鄉居民具有統一的公民身份,平等地享有權利、承擔義務。
事實上,現行戶籍制度造成的身份差異最主要體現在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差異化,依據城里人或農村人的不同,享有的社會保障也不相同。目前,我國城鎮的養老保險實行的是省級統籌,有些地方是地市級統籌[10]。由于農民工普遍在其居住地以外的省市打工,他們無法取得工作地的城鎮戶口,該省市的養老保險制度也就完全將戶口不在本省市的農民工排除在外,造成了農民工無社保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之一就是提高養老保險的統籌層次,建立養老保險基金全國統籌,并設立覆蓋所有公民的普遍社會保險金制度,實行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針對這種普遍性的社會保險,公民均有資格成為投保者,并且只要投保達到一定年限,同時符合該項社會保險對領取者的要求就可以享受社會保險金。這種打破舊體制而重新建立的統一社會保障制度不僅能夠減少不同地區轉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成本,有助于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而且將從根本上解除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制度障礙,以新型的社會保障方式取代土地的社會保障作用,充分實現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貨幣價值。當然,這種較為激進的破舊立新式改革,顯然需要付出較長的準備時間方能實現。
其二,維持現有城鄉二元的社會保障體制,僅將城鎮的社保體系加以改造,使其不再設置戶籍限制而向農民開放,即“以土地換社保,變農民為市民”的改革方法。城市居民“有社保無土地”、農村居民“有土地無社保”的現實狀況是由城鄉居民不同的生活條件決定的。相比之下,城市居民的生活風險在一定程度上比農村居民要大,因為城市居民一旦失業,將會完全失去收入來源,而農村居民尚有土地可以依賴。這種原本相安無事的局面隨著農民大量涌入城市被打破,對于農民工而言,他們的身份實質已由農民轉變為工人,但卻無法以城鎮居民的身份獲得相應的社會保障,由此引發出失地農民的生存問題。其根本原因在于公民沒有自由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即“放棄土地以換取社保”或“放棄社保以換取土地”的選擇模式沒有形成。
因此,在維持現有二元社會保障體系的條件下,進一步改造城鎮社保體系可以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之一。對于在城市有穩定收入,愿意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變為市民的農民工,應當允許他們通過繳納一定社會保險費用的形式加入城鎮的社會保障體系之中。也就是說,進城農民以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宅基地使用權為前提,真正轉變為城鎮市民,有資格參加城鎮的社會保障。這樣做便于操作和管理,可以解決失地農民和農民工的保障問題[11]。而對于那些想要投入到農業生產中的城市人,購得土地承包經營權后應當放棄城市給予的社會保障,由城鎮市民轉變成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
4 結 語
在市場經濟迅猛如潮的今天,我國農民所面臨的問題已經與傳統農業社會和計劃經濟體制下之的遭遇截然不同:如今,農村經濟已經不完全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12],許多農民已經不再以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耕為生存方式,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的改革將更多的中國農民與市場而非土地捆綁在一起,他們的命運是與市場化緊密聯系的。筆者認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物權化的根本意義就在于使這一權利成為財產,能夠在市場上自由流轉,而農民作為土地承包經營權的主人,可以通過理性的風險評估和分析,選擇保有權利或者將其讓渡,從而實現個體利益的最大化。現行戶籍制度及其所引發的問題使得土地承包經營權難以順理成章地通過市場化實現其價值,法律所構建的土地使用權物權化就無異于是紙上談兵,無形中浪費了立法資源、增加了適法成本。因此,以破除傳統戶籍制度為核心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已勢在必行且迫在眉睫。
基于前述分析,筆者主張采取漸進式改革的模式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允許農民通過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方式,加入到城鎮的體制中來,變農村戶口為城鎮戶口,并有資格取得城鎮社會保障,而對于城鎮居民,也可以在放棄城鎮生活條件的前提下,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份子享有成員權。在此基礎上,逐步過渡至消除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不再以戶籍作為公民身份的確認標準,建立以身份證為核心的統一公民身份制度,最終形成覆蓋全國范圍的基本社會保障體系。
(編輯:田 紅)
References)
[1]孟勤國等.中國農村土地流轉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44.[Meng QinGuo,et al.Study on China’s Rural Land Circulation[M].Beijing:Law Press,2009:44.]
[2]陸益龍.超越戶口——解讀中國戶籍制度[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1.[Lu Y iLong.Beyond the Household:to Analyse Chin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M].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04:1.]
[3]Tiejun Cheng,Mark Selden.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J].The China Quarterly,1994,139:650.
[4]孟勤國等.中國農村土地流轉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8.[Meng QinGuo,et al.Study on China’s Rural Land Circulation[M].Beijing:Law Press,2009:18.]
[5]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140.[Yu DePeng.Urban and Rural Society:From Isolation towards Openness:Study on Chin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aw[M].Jinan:Shandong People’s Press,2002:140.]
[6]孟勤國等.中國農村土地流轉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08.[Meng QinGuo et al.Studyon China’s Rural Land Circulation[M].Beijing:Law Press,2009:108.]
[7]中國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外出勞動力返鄉問題日趨嚴重對土地承包關系的影響初步顯現[EB/OL].2009-03-03,[2009-03-29]http://www.caijing.com.cn/2009-03-03/110111348.html.[Rural Economy Research Center,Ministry of Agriculture.Increasing Problem of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Home and the Beginning Impact to Land Contractual Relations[EB/OL].2009-03-03,[2009-03-29]
[8]劉翠霄.天大的事——中國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25.[Liu CuiXiao.Study on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f Chinese Farmers[M].Beijing:Law Press,2006:125.]
[9]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302.[Yu DePeng.Urban and Rural Society:From Isolation towards Openness:Study on Chin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aw[M].Jinan:Shandong People’s Press,2002:302.]
[10]劉翠霄.天大的事——中國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95.[Liu CuiXiao.Studyon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f Chinese Farmers[M].Beijing:Law Press,2006:295.]
[11]四川省經濟信息中心課題組.以土地換社保變農民為市民——改革戶籍制度的基本思路[J].四川改革,2007,(10):29.[Research Group in Sichuan Economic Information Center:Changing Land Rights for Social Security,Making Peasants Become Citizen:the Basic Idea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ation[J].Sichuan Reformation,2007,(10):29.]
[12]劉翠霄.天大的事——中國農民社會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98.[Liu CuiXiao.Studyon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f Chinese Farmers[M].Beijing:Law Press,2006:198.]
AbstractBeing usufructuary right,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as a kind of property can be traded in the market.“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operty Law”,which was promulgated in 2007,has created the solid protection to this trade system.However,the emerging trade market of this land rights still has external system problems.As the social management institution,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which is a product of the planning-market economic system,hinders the market circulationof this right seriously.Therefore,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focusing on the existi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we need to reform the current social security systemwhich is basedon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so as to clear the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e market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At the beginning,through the wayof“changing land rightsfor social security,making peasants become citizen”,rural migrant workers can get social security on the premise of giving up their rural land rights.Finally,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should be abolished and a new nationwid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hould be constructed so that the functions of the trade market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can be achieved.
Key wordsthe trade market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nationwid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Restrictions to the Trade Market of the Right to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from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DENG Hai-feng WANG Xi-yang
(School of Law,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F301.1
A
1002-2104(2010)07-0097-05
10.3969/j.issn.1002-2104.2010.07.016
2009-12-07
鄧海峰,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環境法、自然資源法。
*該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環境法重點研究基地重大招標項目“中國自然資源物權創新制度研究”(編號:2007JJD820166)階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