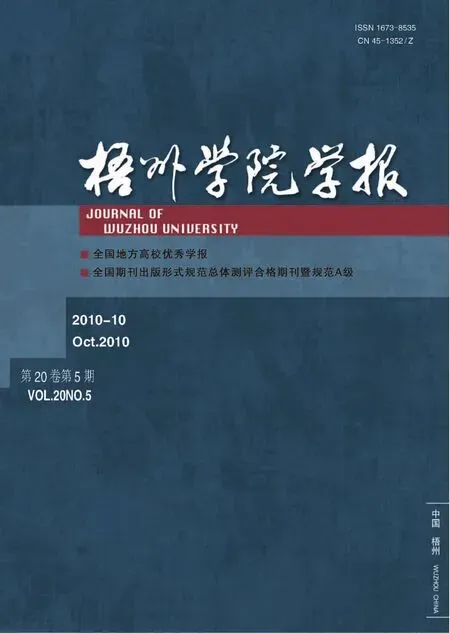也談散文詩的可能性——不僅僅只是與余光中前輩的偏見商榷
林美茂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北京 110000)
也談散文詩的可能性
——不僅僅只是與余光中前輩的偏見商榷
林美茂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院,北京 110000)
余光中先生認為散文詩屬于一種 “非驢非馬”般的存在,這種觀點幾十年來成為許多人對于散文詩偏見的代名詞。通過對中國和日本文學界存在的幾種正面肯定散文詩的觀點以及散文詩產生與發展歷史的考察,分析回應了余先生的偏頗以及這種言論產生的背景,指出這種文體不僅屬于詩歌文學發展歷史的必然趨勢,更進一步展望了散文詩由于其美學特質超越了簡單的自由詩與散文的結合,必將發展成為聚各種文學、藝術的表現精華于一身,具有立體審美可能性的 “大詩歌”文學。
非驢非馬;散文詩;獨立文體;立體審美;大詩歌
“在一切文體之中,最可厭的莫過于所謂 ‘散文詩’了。這是一種高不成低不就,非驢非馬的東西。它是一匹不名譽的騾子,一個陰陽人,一只半人半羊的faun。往往,它缺乏兩者的美德,但兼具兩者的弱點。往往,它沒有詩的緊湊和散文的從容,卻留下前者的空洞和后者的松散。”[1]157
這是余光中先生在20世紀60年代對于散文詩所表達的觀點。之所以筆者要在今天重提這個觀點,原因有二:一是時間雖然過去了40多年,但在今天的大陸文學界,一談到散文詩,仍然有不少人以 “非驢非馬”來界說它的文體特征,余光中先生的膚淺和偏見至今陰魂未散;二是從近幾年中國的散文詩創作現狀來看,許多作品的美學與思想高度已經向新詩趨近,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散文詩的美學特質越來越明顯,誰也無法否定它與新詩、散文并存發展了。是時候了,散文詩可以理直氣壯地矯正余光中先生曾經的偏執與輕狂了。
不管當時余先生出此言論時臺灣文壇的現實背景如何,我們仍然可以說不知道是誰給予了這位詩人這種權利,可以如此狂妄地認為散文詩不值得存在,其言辭達到了對于散文詩的存在幾近侮辱的程度。正如玉米不能說水稻長得矮小,南瓜不能嘲笑紅薯不夠肥大一樣,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學名:莊稼。它們都可以滋養我們的身體,其不同只是味道相異而已。新詩作為現代漢詩的一種表現形式,其存在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秉承了古典漢語文學中駢賦詩詞等韻文學的一條支脈向現代延伸。而散文詩同樣屬于中國古典韻文學向現代漢詩發展過程中的另一條礦脈,其存在的獨立性早已有許多文論家述及,它的存在與新詩一起構成現代漢詩的左右兩翼,只有這樣才能讓現代漢詩展翅,實現中國韻文學從古典向現代健全地滑翔著陸,怎能說 “它是一匹不名譽的騾子”呢?
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針對余光中先生的這段輕言,談一談散文詩的存在理由以及其作為一種文體所蘊含的巨大發展可能性。
一、無論散文詩是什么,它的存在無法否定
從中國的新詩與散文詩的誕生來看,它們幾乎同時出現,第一本新詩 《嘗試集》 (1920年)和第一本散文詩集 《野草》 (1927年)的出版時期前后相距不到十年。更不用說 《野草》作為中國現代文學一部不朽的名著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當然,究竟散文詩是一種怎樣的文體至今尚無法給予明確的定論,而對于新詩不也是如此嗎?除了在形式上采用分行寫作,在語言上主要運用意象的表現技巧、情感節奏的緊湊簡潔之外,我們還能找到更多的關于新詩的特點嗎?這一點余光中先生在他的上述那篇文章中似乎也同樣遭遇到新詩無法明確界定的問題。所以,他除了以 “一切文學形式,皆接受詩的啟示和領導”[1]來強調新詩的優越性之外,也無法更多地為其所推崇的現代詩進行自身優越性的炫耀。
筆者相信至今為止還無人敢說波特萊爾的《巴黎的憂郁》比其 《惡之花》遜色。也沒有人說過泰戈爾的 《吉檀迦利》比不上他的其他詩歌作品 (當然諾貝爾獎只是把這部作品當作詩集頒獎,而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當作散文詩集來讀,其分行形式和對節奏的把握已經超越了一般我們所熟悉的自由詩)。而圣瓊佩斯、紀伯倫、屠格涅夫、魯迅和萩原溯太郎等大師所留下的散文詩名著,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散文詩作為一種獨立文體在中外文學界被廣泛運用,并留下了寶貴的創作遺產,這些是誰也無法否定的。縱觀中外文學界我們不難發現,有些詩人年輕的時候,一開始寫過散文詩,后來才放棄了這種文體轉向只寫新詩。而有的文學大師卻是在其藝術技巧和思想深度達到極其圓熟的時候才寫開始散文詩。這種現象究其原因,應該是這種文體難以駕馭的緣故,因為它對作者的學識、修養、審美境界、人生境界等要求都極高。[2]
對于散文詩的難寫,自從這個文體被引進中國以來就被人們論及。到了20世紀70年代,林以亮先生也在 《論散文詩》的文章中談到: “散文詩是一種極難應用到恰到好處的形式,要寫好散文詩,非要自己先是一個一流的詩人或散文家,或二者都是不可”。所以他認為: “散文詩并不是一種值得鼓勵的嘗試”,并進一步強調: “寫散文詩時,幾乎都有一種不可避免的內在的需要才這么做,并不是因為他們不會寫詩或寫不好散文,才采取這種取巧的辦法”。[3]當然,筆者引用這個觀點,并沒有狂妄自大到認為寫散文詩的人都是一流的詩人或散文家,只是想指出一點,散文詩絕非一種可以輕視的文體,那是寫作者 “幾乎都有一種不可避免的內在的需要才這么做”的文體,所以,王光明先生認為: “散文詩絕不是為了自由解放而自由解放的,是詩的內容就不該為了追求自由而寫成散文詩-詩不應該有這種毀滅性……所以散文詩不是詩意的散文,也不是散文化的詩,它是一個獨立的存在,一個完整特殊的性格”。[4]
從筆者多年來的散文詩創作經驗以及一些散文詩作者的創作經驗出發,大家一般都會對上述的這些評論家精辟的觀點產生共鳴。散文詩寫作者之所以寫散文詩,那是來自于自己生命律動的本能需要,需要通過這種文體才足以表達自己的審美感受,才能把自己的生命推演到極致。如果用新詩來表現,會感到其不能完全地觸及到自己生命的底色,不能淋漓盡致地敞開自己,完成自己的生命綻放。當然這只是從筆者個人以及一些散文詩寫作者的創作感受而言,絕非含有否定新詩的意義。
二、散文詩與新詩在表現特征上的區別
從某種意義來說,新詩是一種可以隱藏的藝術,通過意象之間的組合、跳躍、張力等作用,把一些應該表現的東西為了追求精煉而隱藏起來,讓讀者在閱讀中自己去完成。這是新詩的長處,然而也是它一種軟肋,因為這樣容易造成一些本來并不具備一流素質的詩人,在表面上看來卻好像是那么一回事,而其自身究竟在寫什么根本就不明確,甚至不知道,許多思想只是后來的評論家們過度闡釋所賦予的。而散文詩則不同,它像一面鏡子,可以讓作者的學識、修養、審美高度、思想深度,以及情感的起伏、節奏的舒緩、內在韻律的顫動一覽無余。好的散文詩作者自己在寫什么,要寫什么,其中的思想、情感、審美、場景與意象的指向極其明確,不然根本無法自然而自如地展開生命的律動細節,寫出來的作品就會捉襟見肘,根本無法游刃有余,寫不出好的散文詩。所以,與新詩可以隱藏相比,散文詩是一種暴露的藝術,所以,郭沫若先生稱之為 “裸體的美人”。[5]
是的,散文詩需要裸體才能呈現其美,不能有任何遮掩。也許正因為如此,日本的現代詩奠基者原溯太郎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不無感慨地說: “在我國一般被稱為自由詩的文學中,特別優秀的、比較上乘的作品才稱得上是散文詩”[6]。后來,他又在另一篇題為 《超越散文詩時代的思想》文章中強調指出: “我當然承認散文詩的藝術意義,并相信其在未來將取得更大的發展。畢竟散文詩作為散文詩的原因,以其藝術的意義是不可能被純粹意義的詩歌所取代的。我絕不否定散文詩。……換一種看法,實際上也可以說現代是散文詩時代”[7]。有識者都知道,萩原溯太郎的一生主要成就在于現代詩的創作,而他最晚年的作品集 《宿命》卻采用了散文詩這種表現形式,他不但沒有排斥散文詩,相反,他更把散文詩置于新詩之上。他認為散文詩與抒情詩相比,內容上的觀念性、思想性因素更多,所以,可以把散文詩當作音樂節奏強、藝術香氣濃厚的思想詩。筆者在這里雖然引用萩原的觀點,但并不意味著完全贊同他的觀點,主要是不同意他簡單地把散文詩放在新詩之上來認識。我們必須肯定幾十年來新詩的輝煌成就,新詩的探索與發展為我國現代文學的繁榮留下了寶貴的遺產,那是散文詩無法替代的。
余光中先生作為現代詩的前輩,他在新詩方面的輝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正因為如此,我們對他的貢獻才極其敬重。由于他的巨大成就和對于現代詩創作上的貢獻,也許有資格認為新詩君臨于其他文體之上。但是,即使如此,他也完全沒有權利否定散文詩。更可悲的是,我國還有許多自己只能寫出小學生詩歌水平的所謂詩人,他們也在附和余先生,認為散文詩是一種 “非驢非馬”的存在,這些人好像自己這么一說就可以跟余先生的藝術與審美高度相提并論了,這種淺薄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三、余光中發言的歷史背景
跟余光中先生學舌的那些膚淺之輩當然無心深入了解,余先生當年發表這種言論時臺灣文壇的現實背景。其實當時的臺灣現代詩壇正在為了是 “橫的移植”還是 “縱的繼承”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最初在50年代中葉,針對紀弦先生強調新詩橫的移植,提倡包容自波特萊爾以來一切新興詩派精神與要素作為 “現代派”詩群的美學主張。而余光中先生則代表 “藍星”詩社明確表明反對這種主張,表示不愿貿然作 “橫的移植”[8]。而到了60年代初,經歷50年代的那場被稱為“現代詩保衛戰”的關于現代詩路線和傾向的論爭之后,臺灣詩壇又出現了在詩人之間展開的關于如何面對新詩現代化問題的論爭,其中影響較大的就是余先生與 “創世紀”的洛夫先生之間的論爭。以洛夫先生為代表的一群詩人選擇了對于傳統更為徹底的反叛,而以余光中先生為代表的另一群現代派詩人則轉向對于傳統的重新體認。本文開頭引用的 《剪掉散文的辮子》中的那段話,其寫作背景即在此后不久的時期。我們無法進一步探知余先生當時說此話有沒有現實的具體所指,如果僅從認為散文詩起源于西方,以波特萊爾作為最初的代表性作家的情形來看,反對 “橫向移植”的他發此言論我們似乎可以理解,更何況當時屬于 “現代派”成員的紀弦、羊令野等詩人都創作了大量的散文詩。然而,我們如果更進一步審視中國的古典文學,可以視為散文詩源頭的辭賦詩文等亦大量存在,郭沫若先生甚至把屈原的《卜居》、 《漁父》,莊子的 《南華經》中的一些文字等也當作散文詩。[5]那么,余先生即使再反對“橫的移植”,而他既然認同了傳統的價值,強調重新認識傳統,那就不該持有如此偏執的觀點,更何況余先生的詩歌作品中,有許多篇章基本都可以當作散文詩來讀。當我們縱觀這些,余先生的這種發言不免會讓人感到與他在現代詩創作上的巨大成就極其不和諧。
從文字的表現上看,前面引述的那段余先生的關于散文詩的看法,措辭過于激烈,過于武斷與輕狂,這一點是否與臺灣文壇爭論時的措辭習慣有關呢?筆者不得而知。不過,這種傾向我們似乎可以從其他人的文章中窺之一斑。比如,蘇雪林在一篇題為 《新詩壇象征派創始者李金發》文章中,痛斥臺灣的現代詩 “更像是……匪盜的切口”。甚至有的詩人謾罵臺灣的現代詩是 “可羞”的 “李金發的尾巴”。而余先生似乎偶爾也有這種措辭傾向,他在與洛夫的論爭中,說自己已經 “生完了現代詩的麻疹”。此處的 “匪盜”、“尾巴”、 “麻疹”等都是粗俗的謾罵用語。如此看來,我們也許對余先生關于散文詩觀點的那段話的措辭也不應該憤慨,因為這是他們爭論時的用語習慣,不值得放在心上。
然而,問題是余光中先生屬于臺灣現代詩壇的領軍人物之一,他應該十分明白自己所掌握的話語權對于社會的輿論界、讀者界具有極大的影響力,這就決定了余先生作為個體存在與作為公共知識分子,自己所應該具備怎樣的良知的問題是需要思考的。我想這一點余先生不會不明白。更進一步,我們可以認為,也許他就是要憑著自己影響大,偏偏就不想顧及這些。然而,我們即使承認余先生在現代詩創作上的成就,可他的這些成就也無法否定魯迅先生的散文詩著作 《野草》的存在。如此等等,筆者不想再就此深究。
總之,我們即使可以從余光中先生的上述發言的歷史與現實背景以及其言說方式的地域性特點出發,從而做到心平氣和地笑對其狂言,不計較他那與其身份不相匹配的膚淺與偏見,但也不能忽視他的這種言論對于當代文壇人們認識散文詩所造成的誤導和傷害。筆者之所以要把余先生的這段話揪出來說事,并非針對余光中先生本人。2009年,中國大陸文壇崛起了一群以“我們——北土城散文詩群”為核心的散文詩探索者,在他們所追求的 “大詩歌”創作情懷面前,余光中先生的這種觀點只是一顆小石子激發的浪花。 “我們——北土城散文詩”的引領者周慶榮先生讀了余先生的這段話,說了一段很能體現 “我們”態度的感受: “余光中曾經把鄉愁寫到了鄉愁之外,我們有過經典的感動,對他四十多年前的輕言我只選擇抖一抖肩膀,不會去介意,這進一步說明我們必須讓散文詩有意義,讓我們的寫作與當下的生活有關,我相信,我們是有自己的信念的人,余光中先生動搖不了,比他更強大的人也同樣動搖不了”。
四、余光中言論的滋生與存活的土壤
在我們檢閱當代散文詩的創作成就時,重提人們對于散文詩偏見的言論,并非像以往那樣,總是糾纏著散文詩究竟是什么身份確認,散文詩發展到今天早已超越了它是什么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它該怎么寫、寫什么的問題。當然也不是擔心當下文壇上還存在的一些有關歪曲散文詩的言論會動搖我們探索散文詩巨大的美學可能性的認識。問題是我們在面對這種言論的時候,必須思考為什么會產生這種言論?其獲得人們共鳴的原因何在?所以,我們有必要檢討當代散文詩的歷史,其自身發展過程究竟存在著什么問題?一些問題來源于何處?明確這些問題對于我們今天的散文詩發展是極其必要的。
其實,造成人們對于散文詩這一文體美學偏見的責任不能全部都推到余光中先生身上,從某種意義上說,更重要的是來自于幾十年來中國散文詩發展自身存在的一些模糊的、不自信的、不明智的言論為余先生的言論提供了獲得受眾的土壤。更具體地說,造成這種局面與一些前輩散文詩人對于散文詩認識的模糊與不自信有關。且不說魯迅先生對于 《野草》寫作的感受: “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夸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后印成一本,謂之 《野草》。”[10]這段話我們無論怎么看都可以理解為魯迅先生自謙的表現,但同時也不能否定魯迅先生在這里對于散文詩這種文體自覺依然模糊不清。當然即使這樣,并不會影響到 《野草》作為中國散文詩之里程碑的存在意義。問題是后來的發展過程中人們只抓住 “小感觸”說事,卻忘記了其中承載著時代大悲痛是魯迅先生 “小感觸”背后巨大的敘事背景。這就造成了幾十年來散文詩創作在繼承和斷裂上出現了本末倒置的現象,該繼承的沒有得到繼承,該斷裂的沒有被揚棄。比如,郭風在 《葉笛集·后記》中寫道: “寫作時,有的作品不知怎的我起初把它寫成 ‘詩’說得明白一點,起初還是分行寫的;看看實在不像詩,索性把句子連接起來,按文章分段,成為散文”[11]。而柯藍則企圖創建他所認定的散文詩美學特征:以小見大,短小精美。[11]魯迅對于 《野草》文體的模糊、以及 “小感觸”之“小”的謙虛表達,這些表面上的東西被放大到作為散文詩的寫作態度和美學特征被言說或者提倡。幾十年來,作為散文詩壇代表性作家都如此不明確自己要寫什么、在寫什么,或者都如此不自信、或者那么缺少自知,散文詩還能期望得到別人公正的評價嗎?
不過,有關散文詩文體認識的問題,不僅僅中國的現狀這樣,在我們的鄰邦日本也存在相同的現象。日本著名散文詩人粕谷榮市先生在散文詩的創作談中也表達了相似的感受: “長期以來寫散文詩,近四十年了。然而,沒有一次想到是在寫 ‘散文詩’。是想寫詩的,自然地成為那樣(散文詩)了。也許這就是所謂的不中用吧!為了自由,至少可以說,寫作的時候我希望是自由的。就這樣,不知不覺地采用了這種形式。這就是我的理由”。[12]而在這章散文詩刊載的同一期雜志上,另一位散文詩人高橋淳四先生也同樣拒絕承認自己是在寫散文詩,他說自己只是根據內在節奏而需要句子的長短表現,所以,自己的作品被當作散文詩,而自己沒有打算寫散文詩,而是在寫詩,[14]等等。看來,無論中國還是外國,對于散文詩的寫作,都存在著不自覺的、模糊的認識傾向。就是作者自身的這種非自覺寫作,為那些否定散文詩的觀點提供了滋生與存活的土壤。
然而,從中國當代的散文詩創作情況來看,這種非自覺的散文詩創作歷史應該可以劃上句號了。許多作者不再是想寫新詩而寫成了散文詩,而是自覺地、明確地要創作散文詩。特別是一些兩棲性的作者,他們一方面從事新詩寫作,另一方面明確地以區別于新詩創作的情感、思維駕馭方式、有意識地要寫散文詩,并且能夠比較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所采用的兩種體裁在表現手法上是不一樣的。這應該就是林以亮先生所說的 “一種不可避免的內在的需要”,或者王光明先生所談到的那樣,應該寫成新詩的內容,就不會為了追求自由而寫成了散文詩的形式。這句話反過來也可以說,應該是散文詩就不可以采用新詩的寫法,所以,像上述那些非自覺寫作者那樣寫自由詩因為不像成了散文詩,不可能從自由詩變成了散文詩。
總之,那些對于散文詩認識模糊的作者,不可能寫出真正的好的散文詩。也許,這是散文詩這種體裁處于萌芽階段所要走的一段必然的摸索路程。而在當今的中國文壇,這個階段應該可以宣告結束了。散文詩的文體美學確立、創作繁榮的時代正靜悄悄地開始了。
五、散文詩的可能性
所以,作為散文詩這種文體的探索者、實踐者,我們根據自己的創作經驗,絕不贊同散文詩像余光中先生所說的那樣: “兼具兩者的弱點”,恰恰相反,它可以兼具兩者、甚至所有文學藝術的優點。正因為這樣,我們覺得有必要替余先生糾正他的偏執,讓他在現代中國詩壇更能顯示出其存在的從容與大氣。從中國現代詩的發展歷史來看,余先生所追求的如何處理橫的移植與縱的繼承的關系,尋求中國詩歌從傳統向現代的過度的探索都值得我們借鑒。恰恰因為我們敬重他的貢獻,才需要糾正他的這種極其膚淺的認識,把他的觀點提出來進行商榷。那么,筆者的結論是:散文詩不僅可以兼具散文和詩的優點、甚至可以吸收所有文學藝術中的精華元素來發展自己。
筆者的這種觀點,不僅只是許多創作實踐者來自于創作過程的切身感受,對于散文詩潛在的美學可能性,著名文學理論家謝冕先生也早已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在1985年寫的一篇題為 《散文詩的世界》文章中精辟地指出: “散文詩的‘兩棲性’便成了它在文學體系中的特殊的一種身份。它的 ‘雙重性格’使它有可能兼采詩和散文之所長 (如:詩對對象表達的精粹和飛騰的幻想性,以及散文的流動、瀟灑等),摒除詩和散文之所短 (如:詩的過于追求精煉而不能自如地表達以及詩律的約束,散文一般易于產生的散漫和松弛等)。在詩歌的較為嚴謹的格式面前,散文詩以無拘束的自由感而呈現為優越;在散文的 ‘散’前面,它又以特有的精煉和充分詩意的表達而呈現為優越。在全部文學藝術品類中,像散文詩這樣同時受到兩種文體的承認和 ‘鐘愛’、同時存在于兩個不同的環境中而又回避了它們各自局限的現象,大概是罕有的。這一特殊的地位,無疑為散文詩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證。”[14]筆者認為這是一位文學理論大家令人信服的敏銳眼光。
不過,筆者覺得還應該補充一些謝冕先生未曾論及的問題。一直以來,我們總是把散文詩當作散文和詩的結合,正因為如此,有些前輩就認為它是 “美麗的混血兒” (王幅明)。筆者認為散文詩不是兩者的結合,散文詩完全超越了這兩者的存在,它是一個可以包容所有文學藝術中精華的元素來鑄就自己的美學品格的文體。如戲劇一樣,音樂、美術、詩歌、散文、小說等要素融為一體成就了戲劇這門藝術。所以,說散文詩 “非驢非馬”也許對,但它本來并非驢 (散文)和馬(詩)的雜交而誕生的騾子這一點必須明確。我們如果把文學進行大的分類的話,傳統的看法無非只有詩歌 (有韻文學)、散文 (無韻文學)、小說(故事文學)三種。筆者認為散文詩的內在情緒節奏接近于傳統的韻律,這就決定了它應該歸入傳統意義上的詩歌范疇,當然不是現代意義的新詩,也不是散文,更不是詩和散文結合的產物,為了區別這些, “我們”散文詩群使用了 “大詩歌”的概念。因為它作為一種具備內在情緒節奏特質的文體,其本質上完全可以在創作中吸收音樂的節奏和旋律,散文的自由與從容,詩歌的意象與象征,小說的敘事與細節,戲劇的場景設置與情節安排,美術的構圖、圖像與色彩,光與影、潑墨與留白等手法,盡可能以精煉的文字,自由地綻放生命的展開機制,通過場景、細節、象征、情緒濃淡、節奏的舒緩等有機的詩化結構處理等,創造出一種既超越于單純地為追求精煉而隱藏,為了分行而跳躍的新詩,又區別于松散、冗長、拖泥帶水的敘事散文以及淺白直抒、單純平面的抒情散文,使散文詩展現出具備立體審美可能性的、全新的、綜合現代各種藝術技巧于一身的、屬于現代意義的、具有內在韻律節奏的 “大詩歌”范疇中的一種文體。特別是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快餐文化的普及和流行,人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被時間的因素所左右,那么,長篇大論的大部頭小說將越來越被拒絕,而散文詩恰恰可以把一些生命的具體場景和細節進行詩化的處理,濃縮成一篇精美的生命與情感律動的文字。可以預見,在未來的社會里她將被更為廣泛地接受。
所以,筆者一方面認同謝冕先生的觀點,那是來自于自己創作經驗所帶來的強烈共鳴。同時,也承認中國散文詩90多年來發展滯后于新詩的創作成就,散文詩的探索還遠遠不夠,自身的突破尚且遠遠不足,謝冕先生為散文詩所作的美學定位還遠遠沒有抵達,更不用說已經抵達聚各種文學藝術精華于一身的、具備立體審美可能性的“大詩歌”了。然而,筆者堅信謝冕先生的觀點是對的,當代的散文詩創作,正在通過各種探索逐漸趨近這種美學高度。這種高度的抵達需要生命與審美的極致飛翔,并且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更進一步,筆者甚至大膽展望,今天中國文壇關于散文詩這種文體的一切美學探索實踐,在將來的文學歷史中,將有可能會綻放出具有世界性意義的意義。因為據筆者所知,當今的世界,只有中國人把散文詩這種體裁作為一種獨立的文體,并有許多人正在進行著不懈的探索。
[1]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辮子[M]//余光中.寂寞的人坐著看花.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15.
[2]林美茂.散文詩,作為一場新的文學運動被歷史傳承的可能性[J].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8(4).
[3] 林以亮.論散文詩[J].文學雜志, 1956(1).
[4] 王光明.關于散文詩的特征[J].福建文學,1983(2).
[5]郭沫若.論詩三札[M]//郭沫若選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201.
[6] 原溯太郎.關于散文詩[J].現代詩手帖,1993(10).
[7]原溯太郎.超越散文詩時代的思想[J].現代詩手帖,1993(10).
[8]余光中.第十七個誕辰[M]//余光中.余光中散文選集:第2輯·聽聽那冷雨·焚鶴人.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7:339-358.
[9]魯迅.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M]//魯迅.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456.
[10]郭風.葉笛集·后記[M]//葉笛.葉笛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
[11] 柯藍.散文詩雜感[N].文匯報,1981-02-21(3).
[12] 粕谷榮市.月明·散文詩觀[J].現代詩手帖,1993(10).
[13] 高橋淳四.天使·散文詩觀[J].現代詩手帖,1993(10).
[14] 謝冕.散文詩的世界[J].散文世界,1985(10).
On the Feasibility of Prose Poetry——beyond a Discussion about Mr.Yu Guangzhong's Prejudice
Lin Meimao
(Philosophy College,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10000,China)
Mr.Yu Guangzhong thought that prose poetry is a being of“neither a donkey nor a horse”.This viewpoint has been a substitution of many people's prejudice over prose poetry.In this paper,after analyzing some affirmative viewpoints in Japanese literature circle about prose poetry,the history of prose poetry,Mr.Yu Guangzhong' prejudice and its background,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is style is not merely an inevitable developing trend of poetry and literature.The author predicts that because the literature features of prose poetry surpasses surpass the combination of simple poetry and prose,prose poetry will inevitably develop into a“great poetry” literature containing full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combining the cream of all kinds of literatures and arts,because the literature features of prose poetry surpasses surpass the combination of simple poetry and prose.
neither a donkey nor a horse;prose poetry;independent style;full aesthetic appreciation;great poetry
I207.25
A
1673-8535(2010)05-0083-07
2010-07-01
林美茂 (1961-),男,福建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哲學博士,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柏拉圖哲學、公共哲學、日本思想史、散文詩。
覃華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