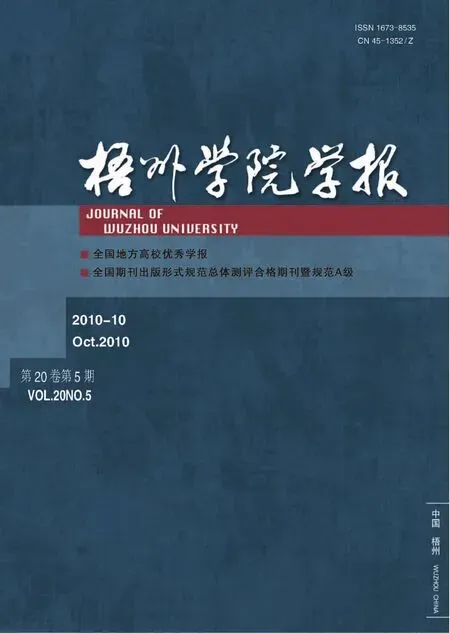論現代漢語規范化問題
劉光婷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048)
論現代漢語規范化問題
劉光婷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北京 100048)
語言的規范化問題愈來愈引起人們的重視,但與大投入相比,其效果似乎并不理想。規范是一種有效的干預,在規范化的過程中,首先要做好“層次”的區分;其次應樹立動態的規范觀,做好“度”的把握。語用價值才是現代漢語規范化的根本依據。
現代漢語;規范化;動態;理性原則;習性原則
俗話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無一例外地都遵守著一定的規矩,自然界、人類社會自不必說,甚至我們的語言學領域也有自己的規矩。但與其他領域相比,語言學領域的規矩似乎最復雜、問題最多,于是語言的規范化問題也就愈來愈引起人們的關注。現代漢語規范化工作,主要是根據漢語的歷史規律,結合漢語的習慣用法,對普通話內部(包括語音、詞匯、語法各方面)所存在的少數分歧和混亂現象進行研究,選擇其中的一些讀法或用法作為規范,并加以推廣;確定其中的另一些讀法或用法是不規范的,應舍棄的,從而使漢語沿著健康和規范的道路向前發展,使人們在使用語言文字時有一致的標準。[1]早在1955年,國家就把“實現漢語規范化”作為語言文字工作的三大任務之一。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相關部門做了一系列扎實有效的工作,甚至出臺了相應的政策、法規,重視程度是顯而易見的。例如,1956年國務院把推廣普通話作為漢語規范化工作的核心,影響深遠;1957年完成的漢語拼音方案在語文應用、新聞出版、信息處理等各方面均發揮了很好的作用;1960年編輯出版的以詞匯規范為目的的《現代漢語詞典》鉛印本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2000年通過并實施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立了普通話和規范漢字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法律地位。[2]尤其是1997年《普通話水平測試等級標準》的頒布,進一步說明語言規范化工作已經步入一個更加標準化、科學化、現代化的新階段。
但令人遺憾的是,與這樣的大投入相比,產生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往往一提到規范化問題,人們就認為是要求大家墨守成規,反對創新、抹殺個性,難免會產生抵觸情緒。我們認為,對于什么樣的語言是規范的,大家一定會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點應該是明確的,即語言規范的目的絕不是要束縛語言使用者的語言行為,絕不是要阻止語言的健康發展。相反,規范是一種有效干預,通過這種干預,不斷完善我們的語言生活,最終積極促進語言生活的良性發展。“規范不但要能評價通例,而且要善于發現創新,積極鼓勵創新。”“不應該用‘純潔語言’的旗號來反對交際中新現象的出現。相對于‘顧后’而言,語言規范化更重要的是要有‘瞻前’意識,見微知著。”[3]我們認為在規范化的過程中,首先要做好“層次”的區分;其次應樹立動態的規范觀,做好“度”的把握。
一、規范的“層次”問題
語言的規范化問題首先應區分為靜態語言的規范和動態語言的規范這兩個基本層次。
(一)靜態語言的規范
靜態語言指的是未進入交際層面的語言,其規范化一般涉及文字、語音、語匯等語言要素。例如漢字的書寫形體、書寫順序都有特定的要求,“柿”與“肺”這兩個字右邊的部件是不一樣的,但很多時候我們都疏忽了,容易寫錯,這就需要規范;“不共戴天”不應寫作“不共帶天”,這也需要規范。再如一些語匯的讀音問題,“暴殄天物”中的“殄”不應念作“zhen55”,尤其是一些多音字在具體語境中的讀音、釋義問題也都需要規范。這在目前的規范問題中是存在問題較少的一部分,隨著漢字的定音、定序、定形,以及若干法規的頒布,大家基本已達成共識,只要我們不斷提升自己的知識水平,要做到準確運用是不難的。
這里需指出,在靜態語言的規范化過程中,語匯的規范稍顯復雜。眾所周知,語匯是一種語言中發展速度最快、最為活躍的因素。近年來,社會生活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語言環境的空前活躍,漢語普通話和英語、港臺方言以及內地各方言之前的相互碰撞、滲透也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趨勢,加之手機、網絡等現代化信息傳播手段的促進,各式新詞應運而生。其中,如Email (電子郵件)、GDP(國內生產總值)、WAN(廣域網絡)、WTO(世界貿易組織)、MBA(工商管理碩士)、FTP(文件傳輸協議)等純外文字母詞語日益流行開來。前不久,廣電總局向央視下發了通知,在主持人口播、記者采訪和字幕中,不能再使用諸如上述外語縮略詞。某網站就此做了一個調查,結果顯示:支持者僅為21.5%,72.7%的反對者認為許多外來語尚無合適的譯詞存在,相反,外語縮略詞形式簡潔、表義明確,又能滿足人們對新異表達形式的追求,何樂而不為呢?我們認為,廣電總局之所以有這樣的舉措,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為了維護漢語的純潔性;二是不得不承認,外語縮略詞形式的確讓部分對此存在認知盲點的人摸不著頭腦,相反漢語全稱在表義時卻能做到清晰、明白,有時甚至可以“望文生義”。因此,此舉的出發點應該是值得肯定的。但語言是發展變化的,其規范與否是相對的,我們的規范觀理應也是動態的。對外文字母詞語及其他流行詞語的使用不妨以“必要、規范、適當”為原則,規范讀音、規范書寫形式,防止濫用、誤用。針對不同的語體、不同的人群,制定不同的使用標準。在此基礎上,可以有條件、有選擇地吸收新生詞語中一些有生命力的成分來不斷豐富、完善漢語普通話,真正做到使漢語沿著健康和規范的道路向前發展。
(二)動態語言的規范
動態語言的規范主要指語言交際層面的規范問題,一般涉及句法結構、語義搭配甚至語言環境,當前分歧較多。特別是對于一些非常規表達的理解,往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例如下面這些例子就曾一度引起了大家的廣泛爭議。
(1)恢復疲勞
(2)打掃衛生
(3)大樓一片漆黑,只有他的房間還亮著燈。
鄒韶華就此提出了規范中的理性原則和習性原則。一種語言現象規范與否,理性原則以是否符合邏輯事理為判別標準,習性原則就是要拿出數據來,以約定俗成的程度為標準。其中,習性是第一性的,理性是第二性的。“為了使人們的交際能順利進行,就必須從共時的角度出發把已約定俗成的東西確立為規范。”“習性原則既可以確立某種規范,同時也可以淘汰某些不合規范的新起的語言現象。”[4]
這里,有兩個問題可以商討。首先,對理性原則之“理”的闡述不夠全面。曹德和認為理性原則之“理”除了邏輯事理還應包括語言組織規律、言語交際規律以及語言演變規律。施春宏指出,理性之“理”的單一化導致了語言規范化工作的平面化,必須從理性的角度重新審視理性原則之“理”。理性不等于邏輯事理;理性不只是說明單一規則的運用,還需要說明不同層次規則之間的協同作用;理性原則不但要考慮語言結構自身之理,語言之外的要素對語言交際的影響中蘊涵的“理”也必須考慮到,等等。這些認識進一步豐富了理性原則的內涵。
理性之“理”也是一種規律,至少應包括語言規律之“理”和邏輯規律之“理”,且二者地位不同,語言規律才是根本。試看下面的例子。
(4)月亮過碧綠把走。
(5)武警戰士睡覺時都睜著一只眼睛。
很明顯,例(4)徹底違反了句法配置規律,它雖然穿上了句子的外衣,卻是一個十足的不合格句。例(5)句法組配合理,但似乎不合邏輯。既然是睡覺,怎么會睜著眼睛?可是交際中,由于我們總相信說話者的語言能力和真誠意圖,就會努力尋找讓句子成立的邏輯真值條件。這里,是夸張手法的運用,表意更加形象、到位。類似“我從面包里吃出了一個汽車輪胎”,這句話給我們的第一感覺是:簡直太荒謬了!但略一思考,如果這是一只玩具汽車的小輪胎也未嘗不可。劉大為稱之為“破格句”[5],即它雖然與常規的合格句還有一定的距離,但還算不得病句,它是與眾不同的可接受的句子,我們總能找到至少一種符合人類認知規律的語義解碼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這里的“理”本質上是對語言現象、對客觀世界的一種認識,由于認識是不斷深化的,因此我們所堅持的“理”也不應是一成不變的。
其次,夸大了習性原則在語言規范中的作用。把習性解釋為語用頻率、解釋為約定俗成,這似乎意味著即使語病明顯的句子,若語用頻率高了就可使其變為合格句。謬誤重復一千遍就變為真理,這顯然是荒謬的。語言具有任意性和理據性,二者之中,理據性才是其本質特性。相應地,在理性原則和習性原則之中,理性原則才是首先要堅持的,習性原則只是理性原則的一種有益補充,可以看作是在找不到可靠的理據時臨時得到的一個解,隨著認識的深入、理據的完善,我們就會用新的答案去替換它。因此,徹底的“無理而妙”是不存在的,只要是妙的,就有蘊含其中的“理”,不過有時還未挖掘出而已。
進入交際領域的語言是動態的、多變的、復雜的,從不規范到規范是一個漸變的連續統,其界線是無法徹底厘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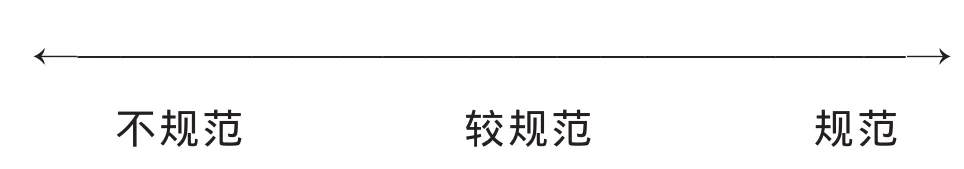
通常,大家爭議較多的是那些處于中間地帶的表達,戴昭銘把這類客觀存在而資格可疑的言語形式叫做“可能規范”。要想對它們制定一個整齊劃一的規則,是不容易做到的。規范的原則在這里只能有一條,那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在語用本位的前提下談規范問題。換言之,必須將交際值或者說語用價值作為現代漢語規范化的根本依據,語用價值是統領理性原則和習性原則的最高原則。
例如,一本語法書在講到動賓搭配時舉例說,“咬自己的鼻子”因為不合事理,即使句法結構沒問題也是錯誤的。仔細琢磨一下,孤立地看這個搭配似乎有問題,但在特定語境中,并非不可以。試想,老板給某員工布置了一項工作,員工聽后答道:您是讓我咬自己的鼻子啊!這里,完全可以用“咬自己的鼻子”來形容工作根本無法完成。所以,表面看不合事理,但在具體的語用環境中,傳遞的是特殊事理蘊含的特殊信息,不能簡單地得出一個是與非的結論。總之,完全不規范的語言現象在整個語言運用過程中實際占有的比例并不大,只要是不影響交際、合乎理性、合乎表達習慣的都應該看作是規范的。
二、規范化過程中“度”的把握
以交際值或者說語用價值為出發點來談規范問題,就要求建立一種動態的規范意識,也就是要尊重鮮活的語言事實,在客觀存在的語言現象中取精華、去糟粕。語言是對現實世界的符號化,世界是豐富的,語言也應是多彩的。千萬不能本末倒置,削語言之足以適規則之履。所以,首先應防止規范過程中的“度量過小”,唯語言學家馬首是瞻,一切以教科書為唯一準繩,那樣就會損傷我們在語言使用過程中的積極性,一味地復制、模仿,缺乏創新意識。欲使語言永保其生命力,必須不斷向其輸送新鮮元素。其次,應防止規范過程中的“度量過大”,在創新大旗的掩護下,不加區分地接受一切語言現象,甚至要“扭斷語法的脖子”,標新立異,這種心態也是要不得的。語言表達形式固然是多樣的,要保留一些有價值的棱角,但它畢竟是日常交際的工具,為了保證交際的順利進行,還應做語法規則的棋盤上一枚規規矩矩的棋子。
綜上所述,語言規范分為靜態語言的規范和動態語言的規范兩個層次,目前分歧較大的是動態語言的規范問題。規范化的過程中,交際值或者說語用價值才是根本依據,語用價值是統領理性原則和習性原則的最高原則。
現在,全球學習漢語的人數已經超過4000萬,已有109個國家的3000多所高等學校開設了漢語課程。因此,漢語已不僅僅是一種民族語言,更是一種世界語言。漢語規范化應當是漢語在全世界傳播戰略的基礎工作之一,[6]不容忽視。
[1]黃伯榮,廖序東.現代漢語[M].增訂4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0.
[2]侯精一.漢語規范化50年[J].語文研究,2006(3).
[3]施春宏.語言規范化的基本原則及策略[J].漢語學報,2009 (2).
[4]鄒韶華.語用頻率效應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245.
[5]劉大為.“破格句”研究[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2).
[6]于錦恩.試論漢語規范化和規范漢語[J].語言文字應用,2006(8).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u Guangting
(Faculty of Literature,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China)
The problem of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is increasingly attracting people's attention.However,compared with the big investment,the result is not as well as expected.Standardization is a kind of effective interference.In the process of standardization, the firststep to be taken is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t levels,and the second step to be taken is to establish the dynamic perspective of standardization in order to control its extent.Pragmatic value is eventually the fundamental basis of the standardization of modern Chinese.
modernChinese;standardization;dynamic;principle of rationality;principle of customary
H102
A
1673-8535(2010)05-0063-04
劉光婷(1976-),女,甘肅武威人,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在讀博士,講師,研究方向:句法語義學、言語習得。
(責任編輯:鐘世華)
201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