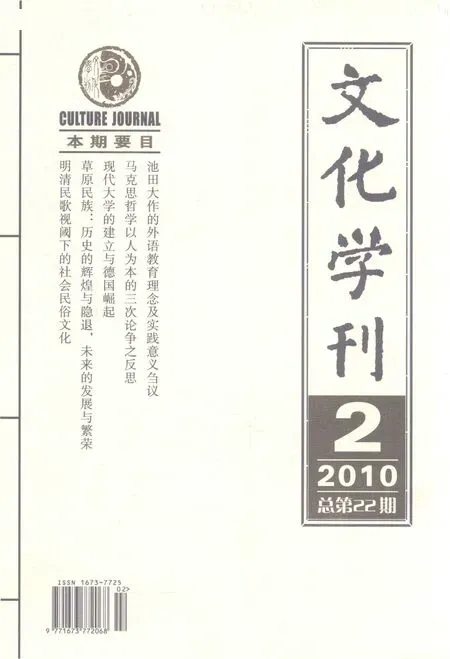文明形式論
吳秋林
(貴州民族學(xué)院,貴州 貴陽(yáng) 550025)
文明是人類的或者說(shuō)是一個(gè)文化體的自然能力和文化能力,以及這兩種能力所創(chuàng)造的成果的總的評(píng)價(jià)和表述。但這里也有一個(gè)標(biāo)志性的表述,即文化力量要在這總的力量中形成一定量的比例后,這樣的“能力”才能稱為“文明”。一般而言,完全以身體的力量所獲得的能力,是生物性的能力,這不是文明,在人類使用某種外在力量方式來(lái)延伸自己的能力的時(shí)候,人類的文明就誕生了。比如說(shuō)使用了工具,進(jìn)而由于工具的形式不會(huì)隨物質(zhì)工具的磨滅而消失,人能夠從中意識(shí)到自己的存在,這樣,人類的文明力量就呈現(xiàn)為幾何級(jí)數(shù)的放大,人類的文明歷史開(kāi)始了。
但是,在人類思考自己的文明的時(shí)候,文明也有自己的外在形式,也會(huì)在不同的自然能力和文化能力,以及影響這些自然能力和文化能力的多種因素中,形成不同形式的文明。比如說(shuō)在世界上影響力最大的兩種文明形式——農(nóng)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文明形式會(huì)在一定的環(huán)境中既定,但形成后的文明形式會(huì)成為一種文化的標(biāo)志,成為一種相對(duì)獨(dú)立的力量來(lái)影響文化的運(yùn)行和發(fā)展。這很重要,許多文化運(yùn)行中的令人費(fèi)解的文化事象,實(shí)際就與文明形式直接關(guān)聯(lián),但我們對(duì)于文明的成果往往津津樂(lè)道,對(duì)于文明形式和獨(dú)立的文明形式的力量,卻知之甚少,這就是我們今天論述文明形式的意義。
一、形式和文明形式
形式最初的呈現(xiàn)是自然法則的力量所致,即每一種可見(jiàn)和不可見(jiàn)的物質(zhì)存在,自然和宇宙都會(huì)給定它一個(gè)存在的形式,這個(gè)存在只受自然和宇宙力量的限制。這就是我們所說(shuō)的自然形式,它是人類所謂文明形式的原始動(dòng)能。沒(méi)有這種原始動(dòng)能的存在,我們的文明形式的發(fā)生和存在是不可能的。所以,對(duì)于形式的認(rèn)識(shí),它既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從一般意義上的形式來(lái)說(shuō),它可以概括所有的物質(zhì)存在和精神存在,凡存在的,都可以說(shuō)是由形式來(lái)標(biāo)定的。沒(méi)有形式,我們不可能“看到”內(nèi)容,沒(méi)有形式,我們也不能表述內(nèi)容。我們?cè)凇澳闷稹贝嬖诘臅r(shí)候,以為只是“拿起”了內(nèi)容,得到了內(nèi)容,但殊不知你也“拿起”了形式。但我們并不知道為何?不知道形式的意義。
形式是隨著存在而普遍存在的,它貫穿了我們所有存在的空間和時(shí)間,不管是物質(zhì)的存在還是精神的存在。
形式是重要的,誰(shuí)最早認(rèn)識(shí)了形式的意義,誰(shuí)就是這個(gè)世界的主宰者,人類就獲得了這個(gè)先機(jī)。我們今天的人類文明歷史有這樣的認(rèn)識(shí),說(shuō)是人類在工具的制造中“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存在,這種存在就是“自意識(shí)”的存在,由于“自意識(shí)”的發(fā)現(xiàn),人類才逐步展開(kāi)了自己的文明歷史。這個(gè)“自意識(shí)”中的發(fā)現(xiàn)是什么?就是形式!人類在按照自然法則創(chuàng)造了一件符合于在地球物理環(huán)境中使用的工具,延伸了自己的物性能力。在這件工具被自然地使用磨滅以后,人類會(huì)自然地尋找同樣的物質(zhì)材料來(lái)做一個(gè)同樣的工具,以延續(xù)對(duì)這個(gè)工具的使用,這樣,這個(gè)工具的樣子(也就是形式)被重復(fù),也就是形式被保留下來(lái)了,在當(dāng)這個(gè)工具的創(chuàng)始者自然死亡后,他(她)所創(chuàng)造的工具的樣子又被他(她)的后代或者說(shuō)群體繼續(xù)延續(xù)下來(lái)。到這里,這種形式的應(yīng)用并不重要,而是人們發(fā)現(xiàn),死去的人在他(她)所創(chuàng)造的工具中有一種形式的存在。在這里,人們才意識(shí)到,“我”可以在我的工具中存在,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存在,就是一種形式的存在。
在最初的工具制造中,自然法則的選擇是多種多樣的,你可以選擇這樣,他可以選擇那樣,即最初的人類可以在多種多樣的選擇中實(shí)現(xiàn)自己“自意識(shí)”的發(fā)現(xiàn)。這樣,人類的“自意識(shí)”發(fā)現(xiàn)就是多點(diǎn)的,即有數(shù)個(gè),甚至數(shù)百個(gè)這樣的文化原點(diǎn)出現(xiàn),它也就預(yù)示著人類文化的多樣性,表明人類文化的多樣性是從其文化的原點(diǎn)上開(kāi)始的。這正好證實(shí)了文化發(fā)生學(xué)派的觀點(diǎn),因?yàn)槲幕南嗨菩钥梢詠?lái)源于自然形式的相似性,來(lái)源于“自意識(shí)”發(fā)現(xiàn)的相似性。
我們?cè)谇懊嬲f(shuō)過(guò),誰(shuí)發(fā)現(xiàn)了形式,誰(shuí)就取得了文明發(fā)展的先機(jī)。先機(jī)是什么?就是唯一的機(jī)會(huì),文明的發(fā)展中永遠(yuǎn)只有一個(gè)一。這種文化先機(jī)是我們?nèi)祟愇拿鞯囊环N基本屬性,在我們的人類文明發(fā)展的內(nèi)部,這種表現(xiàn)比比皆是。誰(shuí)第一個(gè)解讀了這個(gè)世界,誰(shuí)就取得了這一次的先機(jī)。我們今天對(duì)此有許多類似的表述,比如說(shuō)“話語(yǔ)權(quán)”就是最接近于此的東西。這樣的“根”也就在最初的形式發(fā)現(xiàn)。在這樣的過(guò)程中,我們不難看到,形式在人類文化的發(fā)生中的重要性,實(shí)際上,我們今天所說(shuō)的形式,在“自意識(shí)”沒(méi)有被發(fā)現(xiàn)前是自然法則的形式,而在之后,就是人類文化的形式意義了。可以說(shuō),我們?cè)诎l(fā)現(xiàn)“自意識(shí)”的時(shí)候,我們也發(fā)現(xiàn)了形式。
人類的文化就這樣在無(wú)數(shù)的形式的誕生和發(fā)現(xiàn)中走過(guò)來(lái)!人類在文化中也非常重視形式的意義,除了在物質(zhì)的世界中尋找適合我們?nèi)诵缘奈镔|(zhì)形式,也在形式中建構(gòu)一種非物質(zhì)的事物,并以此來(lái)滿足我們非物質(zhì)的一系列需求,最后把它們發(fā)展為一種總稱為精神的事物,來(lái)與物質(zhì)世界對(duì)稱。實(shí)際上,這種所謂精神的最終極的本質(zhì)就是形式——一系列的形式!這樣,我們的人類文化才可以成為文明,不同形式感的文化,也就稱為不同的文明。今天,我們?nèi)祟愒谒伎歼@些文明的時(shí)候,給予了在歷時(shí)性中存在的和共時(shí)性中存在的文明許多名稱。大致地歸納如下:采集文明、狩獵文明(包括漁獵文明分支)、游牧文明、農(nóng)耕文明(包括不同自然和水利條件下的農(nóng)耕形式,以及介于游牧文明和農(nóng)耕文明之間的“游耕文明”)、工業(yè)文明等等。這些文明都有一定的標(biāo)志性的表述。采集文明是以采集自然中植物生長(zhǎng)的可食用植物為主要生存資料,并從而建立起一定的文明形式和能力及文明成果的文明;狩獵文明(包括漁獵文明分支)是一種大量借助工具的力量,從自然中獲取以動(dòng)物的肉、皮為主的生存資料,并從而建立起一定的文明形式和能力及文明成果的文明;游牧文明是在自然環(huán)境中放養(yǎng)以羊、牛、馬為主的動(dòng)物,以獲取其奶、肉、毛、皮、畜力等為主的生存資料,并從而建立起一定的文明形式和能力及文明成果的文明;農(nóng)耕文明(包括不同自然和水利條件下的農(nóng)耕形式,以及介于游牧文明和農(nóng)耕文明之間的“游耕文明”)是在自然環(huán)境中,以土地上種植多種多樣的糧食植物為主,輔助性飼養(yǎng)如雞、豬、牛、羊、馬等動(dòng)物,從而獲取生存資料,并建立起一定的文明形式和能力及文明成果的文明;在此,“游耕文明”是農(nóng)耕文明在中國(guó)山區(qū)的一種特有表現(xiàn),即用“刀耕火種”的形式,在山區(qū)的一定區(qū)域內(nèi),三五年一換的游動(dòng)耕作。既具有游牧文明的移動(dòng)性,又具有農(nóng)耕文明的耕作方式和內(nèi)容。工業(yè)文明是以工廠的形式,全面地獲取自然中所有物質(zhì)作為生產(chǎn)資料,全面地生產(chǎn)所有人類所需求的生存資料,并從而建立起一定的文明形式和能力及文明成果的文明。這種文明形式的主要特性有:標(biāo)準(zhǔn)化、商品化、全球化。
每一種文明都有特定的環(huán)境對(duì)應(yīng)。采集文明——自然植物生長(zhǎng)的環(huán)境;狩獵文明(包括漁獵文明分支)——有動(dòng)物分布的自然環(huán)境(有魚(yú)類分布的水環(huán)境);游牧文明——有適應(yīng)大量牲畜生存的草地、草原;農(nóng)耕文明——有適應(yīng)于種植的土地;工業(yè)文明——有適應(yīng)于商品生產(chǎn)的市場(chǎng)、交通、信息、人才、科技水平等等。
對(duì)于各種文明,可能在我們的文化中會(huì)有許多的認(rèn)知和表述,我們?cè)谶@里要表述只是它的形式意義,即我們?cè)谝陨系膶?duì)應(yīng)中看到,每一種環(huán)境因素,自然造就一種文明形式,但反過(guò)來(lái)說(shuō),每一種文明形式,也會(huì)去尋找適合自己文明形式的環(huán)境。這在中國(guó)文化的歷史上有許多例子,如屬于氐羌族群的彝族人,他們?cè)谀舷轮螅顑?yōu)先尋找的生存環(huán)境是高山草原,因?yàn)樗麄兊募榷ㄎ拿餍问绞怯文廖拿鳌T诿恳环N文明中,最外在的是它的形式,并且一旦既定,就會(huì)成為一定程度上的永恒。
二、文明形式的力量
在自然法則的力量下得到的形式是自然和宇宙的形式,是形式的基礎(chǔ),但它不是我們所說(shuō)的文明形式,文明形式一定是人類文化力量體現(xiàn)的過(guò)程中形成的形式,它自然要受到自然法則的影響和制約,但它體現(xiàn)的是人的力量和意識(shí),以及意志、精神等等。
在以上的表述中我們知道,有一種文明就有一種文明形式,不管這種文明取得多大的文明成果,或者說(shuō)沒(méi)有取得什么有影響力的文明成果,它都有一種形式存在于這種文明中。石器時(shí)代有它一定成就標(biāo)準(zhǔn),陶器時(shí)代有它一定的成就標(biāo)準(zhǔn),……但是,不同的文化體在向這些文明邁進(jìn)的時(shí)候,會(huì)通過(guò)不同的方式來(lái)完成它,來(lái)形成一定的有別于其他文化體的文明形式。
某一個(gè)文化共同體一旦在初始的狀態(tài)中形成一種文明形式,不管是否取得有影響力的文明成就,其形式就會(huì)在其文化中起作用,并體現(xiàn)文明形式的力量。我們把這種形式的作用力分為三種:一是與物質(zhì)生產(chǎn)有關(guān)的形式力量;二是與生活方式有關(guān)的形式力量;三是與精神觀念有關(guān)的形式力量。
(一)與物質(zhì)生產(chǎn)有關(guān)的形式力量
一種文明自然就有與之相適應(yīng)的生產(chǎn)方式和工藝技巧,如果這種形式一直在原來(lái)產(chǎn)生這種文明形式的原地,我們看不出它的力量,但是,這種形式一旦出現(xiàn)移動(dòng),移動(dòng)到另外一個(gè)與之不一樣的自然環(huán)境中,其形式的力量就顯現(xiàn)了。這方面,我們?cè)诿褡鍖W(xué)的田野調(diào)查中,看到過(guò)無(wú)數(shù)的例證。
在云南省、四川省、貴州省的彝族人,其文明形式是在其游牧文明中賦予的,在氐羌族群南下到達(dá)這三省時(shí),最早的氐羌族群的先民并不以山地農(nóng)耕文明的形式來(lái)選擇居住區(qū)域,而是以游牧文明的形式來(lái)選擇居住區(qū)域,即他們選擇長(zhǎng)草的地方來(lái)居住,并不是選擇長(zhǎng)莊稼的地方來(lái)居住,但在這三省地域中,長(zhǎng)草的地方是好地方嗎?雖然經(jīng)過(guò)千年的變遷,大多數(shù)彝族人現(xiàn)在已經(jīng)最終選擇了農(nóng)耕文明的形式,但其中來(lái)源于游牧文明的生產(chǎn)方式、工藝技巧方面的形式力量,至今隨處可見(jiàn)。
布依族人是百越族群的后裔,是一個(gè)典型的南方少數(shù)民族,他們的建筑文明形式起源于“樹(shù)居”、或者說(shuō)“鳥(niǎo)巢居”,即在潮濕的南方山區(qū),居住的房屋一定要支撐離地,在半坡山要伸出吊腳,這種形式的建筑我們稱為“干欄式”建筑,也俗稱“吊腳樓”。這是自然環(huán)境所賦予的形式,但是,我們?cè)诂F(xiàn)實(shí)中看到,當(dāng)這些環(huán)境要素消失后,比如在很干燥的地帶,布依族人也把其建筑建設(shè)成“干欄式”,第一層仍然不住人。吊腳是在山坡上的選擇,但他們的建筑到了平地上也要在后屋壘起一個(gè)兩米多高的土臺(tái),把前面腳“吊”起來(lái)。
仡佬族人是貴州最早的原住民,其先民是百濮族群的直接后裔。在一定的歷史時(shí)期,仡佬族人有篾仡佬、打鐵仡佬、花仡佬、紅仡佬等稱謂,這篾仡佬、打鐵仡佬就是關(guān)乎某種生產(chǎn)工藝技巧的分屬,也就是技巧形式成為這些族群的標(biāo)志了。奇妙的是,我們今天還能在這些族群中看到這樣的物質(zhì)的形式力量。在這些族群中,幾乎人人都是篾工藝形式的技師,人人都是打鐵的匠人,今天的社會(huì)已經(jīng)基本不需要這樣的生存技能了,但這些物質(zhì)文明的形式力量仍然在起作用。
在廣大的民間,傳統(tǒng)工藝中所織的土布,布的功能性差異不大,但不同文明文化來(lái)源的織布機(jī)卻深受其形式力量的左右。在民間,一般使用的是所謂“黃道婆”式樣的平機(jī),但我們還可以看到多種多樣的來(lái)源于不同形式的土織機(jī),其中尤其以彝族人的織機(jī)最具有自己的形式感,完全不同于漢族的“黃道婆”式織機(jī)。
(二)與生活方式有關(guān)的形式力量
任何一種生產(chǎn)都是為了人的生存,生存也有一定形式,比如說(shuō)各種食物就是生存最初始的事物,但就每一種食物而言,其功能性在科學(xué)上都是一致的,但如何“進(jìn)食”這些食物,就表現(xiàn)了形式的力量。在每一種文明里面,都大致包含了這種形式。
人的生存有幾項(xiàng)最為基本的要素,祖先們歸納為“衣、食、住、行”,其實(shí)還有性。這幾大項(xiàng),每個(gè)文明體中都會(huì)有自己的關(guān)于這方面的形式因素,其中的成員都會(huì)自覺(jué)不自覺(jué)地按照文明體中提供的形式來(lái)“衣、食、住、行”。在這方面,我們有太多的例子。在中國(guó)的苗族中,有幾百種不同的“衣的形式”,即在中國(guó)和其他一些國(guó)家,有苗族人穿著幾百種不同形式的衣服。我們稱這樣的“衣的形式”為服飾文化,也有許多人對(duì)它進(jìn)行研究,但至今沒(méi)有一個(gè)人說(shuō)清楚中國(guó)的苗族到底有多少種“衣的形式”,更不要說(shuō)弄清楚它的文化性質(zhì)了。有的衣服既不方便勞動(dòng),也不方便生活,甚至于與氣候變化相矛盾,但人們,尤其是苗族人卻一直堅(jiān)守著自己“衣的形式”。為什么?我們?cè)谙挛囊撌鲋T谑场⒆ ⑿蟹矫嬉灿羞@樣的表現(xiàn),但對(duì)于形式的堅(jiān)守性就大不如“衣”了。
性的功能在文明體中一般只承認(rèn)其人口生產(chǎn)的一面,不太承認(rèn)生物性?shī)蕫偟囊幻妫⑶矣谩岸Y儀”的形式來(lái)限制其生物性?shī)蕫偟囊幻妗T谶@里,如果這個(gè)文明體對(duì)生物性?shī)蕫偟南拗品潘梢恍沁@個(gè)文明體中的性關(guān)系就自由和開(kāi)放一些,否則就相反。有時(shí)候,人們還會(huì)利用節(jié)日,或者說(shuō)其他特定的時(shí)間來(lái)放松這樣的限制,那在這種時(shí)間里的性關(guān)系也會(huì)自由和開(kāi)放一些。這就是中國(guó)西北的“花兒”,中國(guó)南方一些民族的“坐坡”、“花房”,西方一些國(guó)家的狂歡節(jié)等事物出現(xiàn)的根本原因。
我們前面說(shuō)“與生活方式有關(guān)的形式力量主要體現(xiàn)在生產(chǎn)方式的形式力量與精神觀念形式力量之間的地方”,是深有所指的,它表明,與生活方式有關(guān)的形式力量的運(yùn)動(dòng)處在一個(gè)文明體中間的狀態(tài)中,它既與物質(zhì)性質(zhì)的事物聯(lián)系緊密,也能夠上升到精神乃至于觀念的層面上去,并且成為其中的一個(gè)組成部分。這種中間狀態(tài)的形式力量,有時(shí)候就是物質(zhì)形式力量的體現(xiàn),是主導(dǎo)我們?nèi)说奈镔|(zhì)性的形式力量,但這個(gè)中間狀態(tài)的形式力量還會(huì)在其間出現(xiàn)你意想不到的轉(zhuǎn)化。
出現(xiàn)這種轉(zhuǎn)化的原因我以為有二:一是在人的生存述求上,不僅僅是物性的生存,還有精神生存、觀念生存的一面,人的文化的肇始就是形式觀念的肇始,“自意識(shí)”意識(shí)到的是什么?就是形式,并從形式走向了精神和觀念。也就是說(shuō),處于這一狀態(tài)的人本身就具有二重性。二是人的精神的觀念的事物有多種形式和結(jié)構(gòu),有的精神的觀念的分類,其內(nèi)容上是觀念的,形式上也是觀念的,比如說(shuō)哲學(xué)的、倫理的,但有的精神觀念的分類就一定要有物質(zhì)的形式來(lái)體現(xiàn)它,比如藝術(shù)。而這種物質(zhì)的形式基本上就處于中間的狀態(tài)中,藝術(shù)的精神觀念要尋找形式,就必然在這一層面來(lái)尋找。
與生活方式有關(guān)的形式力量中的物性力量我們不用多說(shuō),基本上都好理解,但在這樣的形式力量中,一般的物質(zhì)性形式力量是如何上升到觀念和精神層面的?我們?cè)嚺e兩例:
第一例為中國(guó)苗族的服飾。在功能性上它與其他的服飾是一致的,保暖、體現(xiàn)審美等,這種一般性的服飾中都有的功能性述求它也有,但苗族的服飾中還有一些述求是一般的服飾根本沒(méi)有的,比如記錄文化、作為族群標(biāo)志、意志體現(xiàn)等等。后者就是從形式力量上走進(jìn)了觀念和精神領(lǐng)域了。作為族群標(biāo)志的苗族服飾是一個(gè)苗族支系外在的標(biāo)志,看到這樣的服飾,就看到了自己的支系族群,看到了同胞,看到親緣和婚姻集團(tuán)的成員了。在有外部力量的打擊和壓迫的時(shí)候,這種苗族的服飾還是一種意志的體現(xiàn),這就完全是一個(gè)關(guān)于族群的精神和觀念的事物了。這樣的“衣”已經(jīng)不是“衣”,而是“旗幟”了。第二個(gè)例子是回族人的食物禁忌。這也是與生活方式有關(guān)的形式力量上升為精神觀念層面的最有力的例證之一。這樣的例證中的事物,都不可以用一般意義上的物質(zhì)功能性意義來(lái)解釋它們。
(三)與精神觀念有關(guān)的形式力量
從我們文化的基本性質(zhì)和根源上講,我們就是“意識(shí)人”,我們不在意識(shí)中意識(shí)到自己的存在,那我們作為“人”也就不存在。這好像是“意志論”哲學(xué)的觀點(diǎn),是唯心主義的,但我不這樣認(rèn)為,這不是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問(wèn)題。“自意識(shí)”的觀點(diǎn)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diǎn),其實(shí),在“意識(shí)人”這一點(diǎn)上,沒(méi)有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是我們?nèi)俗陨淼臓顟B(tài)表述。
這樣的論述表明,我們?nèi)说纳嬷校宋镔|(zhì)性的生存之外,我們還有一個(gè)重要的生存,這就是“意識(shí)人”的生存,精神觀念的生存,并且我們?nèi)艘话愣及阉暈槿说慕K極意義。
今天,人類給予了這樣的生存太多的形式,宗教的、藝術(shù)的、哲學(xué)的、政治的、主義的……每一個(gè)分屬中都有大量的劃分,每一個(gè)劃分中又有許多細(xì)小的劃分,并且這樣的劃分可以無(wú)限,而且每一個(gè)劃分中都有人堅(jiān)守。這種堅(jiān)守有時(shí)候是和平,有時(shí)候是戰(zhàn)爭(zhēng)。這里面是一個(gè)個(gè)的宇宙,但實(shí)際上可能什么也沒(méi)有,只是從某一個(gè)文明中的某一點(diǎn)而來(lái)的一種精神和觀念的形式。但就是這種形式的力量讓人一點(diǎn)也不能小視它。我們可能誰(shuí)也沒(méi)有能力改變它,但我們可以從與精神觀念有關(guān)的形式力量中來(lái)認(rèn)知它。
在我們?nèi)擞凇白砸庾R(shí)”中意識(shí)到自己的存在后,我們一面在用工具開(kāi)拓我們的物質(zhì)世界,也在用我們的意識(shí)建立我們的精神和觀念的世界。這種狀態(tài)是何時(shí)出現(xiàn)的我們說(shuō)不清楚,但在意識(shí)中建立精神和觀念的世界,我們今天卻可以從人類的文明歷史中看到它的基本模式。
“起初,神創(chuàng)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靈運(yùn)行在水面上。神說(shuō):‘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kāi)了。神稱光為晝,稱暗為夜。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神說(shuō):‘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照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來(lái)管理海里的魚(yú)、空中的鳥(niǎo)、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chóng)。’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這是第六日。”這是《圣經(jīng)》上的開(kāi)篇文字,它說(shuō)明了這個(gè)世界的來(lái)源,也說(shuō)明了人的來(lái)源。這只是基督教世界的解釋,只是一個(gè)文明體中的解釋。在世界上的其他文明體中,也有大量這樣的解釋,我們所說(shuō)的世界和人類的起源神話,就是這樣的解釋。這幾乎是人類的一個(gè)普遍性的行為,是人類在所謂的“蒙昧階段”必須要經(jīng)歷的過(guò)程。為什么呢?人類在這個(gè)時(shí)候要急于建立什么?這就是要急于建立屬于自己的文化原點(diǎn),只有構(gòu)建這兩樣?xùn)|西,人類的意識(shí)世界才有自己的文化原點(diǎn)。有了文化原點(diǎn),我們才有可能解釋世界的一切。有了這種建構(gòu),只是人類意識(shí)世界的內(nèi)容,它還要有一定的形式來(lái)確立它,這就是“信仰”的出現(xiàn)。我們?cè)谑澜缟嫌星姘俟值氖澜缙鹪春腿祟惼鹪吹慕庹f(shuō),但“信仰”的形式是不變的。這樣的東西沒(méi)有一樣是唯物主義的,但你不得不承認(rèn)它是精神和觀念的。問(wèn)題的重要性在于,一個(gè)文明體有了這樣的解釋,建立了原點(diǎn)之后,其文明體中的文化形式就要受這種解釋的根本性影響。
我們?cè)谖镔|(zhì)的生產(chǎn)方式和有一半是物質(zhì)性表現(xiàn)的生活方式上,是可以接受其他信仰形式力量的影響,我們可以在這些方面有限度地接受這種改變,但在信仰上,你要保持你的生存基礎(chǔ),其改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shuō),你的先民創(chuàng)造了這樣一種解釋,就為你創(chuàng)造了一種信仰形式,并直接導(dǎo)致你的意識(shí)性生存,決定你的生存形式。
還是來(lái)源于氐羌族群的中國(guó)彝族人,他們的先民給予了他們一種世界的解釋,給予了他們一種信仰和信仰形式——祖靈信仰,即用一根竹筒,經(jīng)過(guò)喪祭中的一系列的儀式,把祖先的靈魂象征性地引入竹筒,成為其已經(jīng)去世的祖先靈魂的居所和象征。這種靈魂形式是典型的“馬背民族”的靈魂形式,但彝族人基本在中國(guó)的西南地區(qū)定居并進(jìn)入農(nóng)耕文明的生產(chǎn)方式狀態(tài)后,這種靈魂形式的力量依舊存在,并且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喪葬等一系列文化的形式表現(xiàn)。
我們?cè)谇懊嬲f(shuō)過(guò),我們精神和觀念的意識(shí)生存有許多的形式,大致有宗教的、藝術(shù)的、哲學(xué)的、政治的、主義的等等。在這些個(gè)大類中,前三種不管你是什么樣的內(nèi)容,其最為極致的部分會(huì)有一種稱為信仰的東西存在,在后兩種大類中,也會(huì)部分存在這樣的東西。宗教中有信仰是不言而喻的,這是它的核心,這個(gè)核心主要是形式的,但有時(shí)候它會(huì)給你一些象征性的實(shí)體。藝術(shù)中有信仰,它也有在宗教中實(shí)現(xiàn)的精神依托的效用,也能在其追尋中實(shí)現(xiàn)自己精神的超越。但這里給你的就完全是形式的力量了。追尋這種力量最為極致的就是表現(xiàn)“形式主義”(如康定斯基),就是直接在藝術(shù)和哲學(xué)上把形式上升到一種精神和意識(shí)的表現(xiàn)高度。人們說(shuō)哲學(xué)是一門(mén)“世界觀的學(xué)問(wèn)”,希望用人的理性認(rèn)識(shí)的方式和能力來(lái)替代宗教中對(duì)于世界起源和人類起源的神話,這門(mén)學(xué)問(wèn)是世界文化的“發(fā)動(dòng)機(jī)”,尤其是現(xiàn)代科學(xué)文化的發(fā)動(dòng)機(jī),但是它仍然繞不開(kāi)文化原點(diǎn)的問(wèn)題,這又落到信仰之上了。信仰是一種形式,是人的一種根本意義,沒(méi)有信仰我們發(fā)動(dòng)這個(gè)世界的運(yùn)轉(zhuǎn)來(lái)干什么?而信仰不就是一種形式嗎?
而這些基本上都是來(lái)自于那個(gè)文化原點(diǎn)的事物,都會(huì)與人類最初的文化建構(gòu)有關(guān),而這個(gè)原點(diǎn)從來(lái)都不是一個(gè)“實(shí)體”性質(zhì)的東西,而是一種形式。這就如我們把時(shí)間中的某一點(diǎn)稱為“紀(jì)元”一樣,這個(gè)紀(jì)元在時(shí)間的基本性質(zhì)上只是宇宙的任意一點(diǎn),對(duì)于宇宙一點(diǎn)意義也沒(méi)有,而對(duì)于人類或者說(shuō)人類的某些個(gè)群體,就意義重大,因?yàn)檫@是它的原點(diǎn),或者說(shuō)原點(diǎn)之一。
這種對(duì)于原點(diǎn)的追根溯源,最終的就是“虛空”,在“微精神分析”學(xué)說(shuō)中,他們說(shuō)到一個(gè)觀點(diǎn),認(rèn)為心理的最大能量在于一種稱為“虛空能動(dòng)”的力量,這是心理學(xué)上的最大的最為原始的力量,比之弗洛伊德的“潛意識(shí)”的力量更大。他們指的“虛空能動(dòng)”的力量就是我們所說(shuō)的文化原點(diǎn)的力量。
在這個(gè)文化原點(diǎn)的認(rèn)知上,西方的神學(xué)在某種意義上是很愚蠢的,在全球殖民主義時(shí)代,他們?cè)?jīng)尋找過(guò)神的全球性證據(jù),特別是尋找過(guò)一神的證據(jù),也就是說(shuō),文藝復(fù)興時(shí)代,他們才開(kāi)始他們的人文性質(zhì)的理性認(rèn)識(shí),而這個(gè)過(guò)程在我們中國(guó)的文化中,老子時(shí)代就已經(jīng)完成了這種人文性質(zhì)的理性認(rèn)識(shí)。老子時(shí)代就坦率地承認(rèn),世界的起源是“無(wú)中生有”的,早就承認(rèn)文化在觀念和精神中的形式力量。這也許就是我們中國(guó)的神話傳說(shuō)不如西方發(fā)達(dá)的原因,因?yàn)槲覀冊(cè)缇驮竭^(guò)了用神來(lái)創(chuàng)造天地和人間的時(shí)代。
三、中國(guó)的文明形式與華夏文化的構(gòu)合
形式有無(wú)所不在的力量,文明的形式力量更是。當(dāng)我們作為某一種文明形式所“籠罩”下的現(xiàn)代人,更是“躲”不開(kāi)它的無(wú)所不在的影響。在說(shuō)到中國(guó)的文明形式時(shí)更是如此。中國(guó)是一個(gè)特定的概念,它與所有的文明自信的范式一樣,都有國(guó)之中心的信念,但有一個(gè)事實(shí)卻不能回避,即華夏文明的演化在歷史上就是圍繞著這個(gè)地理環(huán)境的中心和文化發(fā)生發(fā)展的中心進(jìn)行的。
中國(guó)的華夏文明,其主體是農(nóng)耕文明,是在理順了與農(nóng)耕關(guān)系的歷法,理順了水利的前提下,在黃河流域和長(zhǎng)江流域的廣大地域內(nèi)發(fā)展起來(lái)的文明,它包容了很長(zhǎng)的歷時(shí)性內(nèi)容和很寬大的共時(shí)性內(nèi)容。在農(nóng)耕的總的形式下,它又包含了許多區(qū)域性的具有獨(dú)特個(gè)性的農(nóng)耕支系性的形式。比如說(shuō)北方以黃河流域地區(qū)為主的旱地農(nóng)耕,南方以長(zhǎng)江流域?yàn)橹鞯乃镛r(nóng)耕,其形式就是不一樣。在這兩大支系性農(nóng)耕形式中,又有山地農(nóng)耕與平原農(nóng)耕的形式區(qū)別,也有與游牧文明形式交融的山地“游耕形式”等等。
對(duì)于農(nóng)耕文明,可以說(shuō)是中國(guó)最具有形式感的文明形式。在最初始的時(shí)候,人們耕種土地,也許就是散漫無(wú)序的,但江河水系、山峰溝壑會(huì)給人一種自然的次序,會(huì)自然地把人們匯集在一定的區(qū)域內(nèi),形成一種自然而然的組合。比如“八百里秦川”、“巴蜀之地”等等……這種自然的次序,慢慢地會(huì)生成一種有人文色彩的秩序。方圓九百畝的耕作分布,就是這樣的事物,這在中國(guó)被稱為“井田制”。這種有人文色彩的農(nóng)耕形式,可以說(shuō)是中國(guó)人的一大發(fā)明。這九百畝的四方塊,周八塊屬于8戶人家,每戶種一百畝,而中心還有一百畝稱為“公田”,在每年的春季耕耘中,要求先種公田,而后私田,秋收亦然,這一百畝的“公田”所產(chǎn)屬于“公產(chǎn)”。
這種農(nóng)耕文明的形式存在,使中國(guó)古代誕生了一系列影響最為深遠(yuǎn)的文化事物:一是信仰;二是政治制度;三是鄉(xiāng)村聚落的模式;四是“公”的觀念和“集體”的理念。
(一)信仰
我們中國(guó)的信仰可能有許許多多的表現(xiàn),但沒(méi)有一樣如從土地中誕生的信仰更具有本色。我們中國(guó)文化的一系列的歷時(shí)性存在中,對(duì)土地的信仰在土地的產(chǎn)出對(duì)整個(gè)文明體產(chǎn)生決定性影響的時(shí)候,是最大的信仰,我們的古人把它稱為“社”。這個(gè)“社”的最初就是代表方九百畝的疆域的石頭,至今我們?cè)谫F州的某些民族的信仰文化中還能看到這樣的“社”。這個(gè)“社”在春秋時(shí)是當(dāng)時(shí)國(guó)家、地方、村落都必有的祭祀地方——社廟。這種社廟在春秋的文獻(xiàn)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其中有一則關(guān)于社鼠的故事就是講社廟里的老鼠的。這種“社”在當(dāng)時(shí)的農(nóng)業(yè)國(guó)家中,與谷神一起被稱為“社稷”,土地神和谷神是關(guān)乎于江山的,故又稱為“江山社稷”,即有社稷就有江山,沒(méi)有社稷就沒(méi)有江山了。這是國(guó)家性質(zhì)的信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對(duì)土地神和谷神的信仰,則是地地道道的農(nóng)耕文明的本色信仰。
社神信仰在后來(lái)家、國(guó)一體化的文化演進(jìn)中,逐漸被祖先信仰慢慢替代,各種級(jí)別的宗祠才成為中國(guó)農(nóng)耕文明信仰中的主體,但對(duì)于土地的這種信仰,卻在中國(guó)民間形成了一種“草根信仰”,遍布全國(guó)的鄉(xiāng)村。這種遍布全國(guó)的情形在今天的國(guó)家工業(yè)化的進(jìn)程中,慢慢地龜縮到一些特定的區(qū)域里,成為村口路邊的土地廟了。
在一般意義的信仰中,特別是發(fā)展為一種制度化的信仰中,他們?cè)诮庹f(shuō)了世界的起源和人類的起源后,還要給予人們一個(gè)“彼岸”的描述。中國(guó)人沒(méi)有這種虛擬的或然的描述,但有類似的這種精神性的事物,而且這個(gè)事物也帶有濃厚的農(nóng)耕文明的形式感,即“桃花源”。可見(jiàn),農(nóng)耕文明的形式在中國(guó)文化信仰上的影響力之大。
(二)政治制度
中國(guó)最初的政治制度的建立,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農(nóng)耕文明的形式,這在中國(guó)關(guān)于歷史和制度的研究中有許多的文獻(xiàn),但從文化人類學(xué)角度的研究資料卻比較少。“井田制”好像是政治制度賦予農(nóng)耕的一種形式,但是,這種形式一旦誕生,它也就作為農(nóng)耕文明的基本耕作制度,在形式上影響到國(guó)家制度的形式了,即這時(shí)候的國(guó)家一級(jí)一級(jí)的制度都是在“井田制”的基礎(chǔ)上建立起來(lái)的。其實(shí),這種制度還在于它給予了中國(guó)人一個(gè)政治制度的初始狀態(tài),我們后來(lái)的國(guó)家制度,包括今天的國(guó)家制度也離不開(kāi)這種形式的因素。
(三)鄉(xiāng)村聚落的模式
中國(guó)是世界上鄉(xiāng)村形式最為繁多的國(guó)家,關(guān)于村寨的名詞我們可以數(shù)出無(wú)數(shù),北方的村落和南方的村落千差萬(wàn)別,層出不窮……但有一點(diǎn),它的形式的母體一定會(huì)在“方九百畝”的基本模式中。不管是聚族而居,還是宗親血緣為系,或者說(shuō)以某種編制單位……聚落一定是既定的形式。
(四)“公”的觀念和“集體”的理念
在“井田制”的農(nóng)耕文明形式中,它給予我們的影響在前幾項(xiàng)內(nèi)容中,可能會(huì)由于時(shí)間和環(huán)境的變化,會(huì)有很大程度上的變化,但“公”的觀念和“集體”的理念,卻是我們最難于變化的東西。這不是一種物質(zhì)形式,或者說(shuō)半物質(zhì)形式的影響,而是純粹形式的影響。這樣的東西在我們的文明和精神中,是為歷代的中國(guó)人和中國(guó)的文化基本認(rèn)同的東西,也在后來(lái)的文化中被中國(guó)官方和民間使用了多種多樣的形式,一遍又一遍地放大,是中國(guó)文化中關(guān)于“群”的基本形式。這是外國(guó)人最不明白中國(guó)人的地方,但這是中國(guó)人最為迷人的地方,汶川大地震中展示的中國(guó)文化中關(guān)于“群”的觀念和理念就是一例。
這種可以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被不斷演化發(fā)展的文化之根,就存在于中國(guó)農(nóng)耕文明的最初的形式中。在中國(guó)的華夏文明中,農(nóng)耕文明是決定我們今天文化形式最為根本的文明形式。當(dāng)然,在我們的華夏文明中,還包容了其他許多的文明和文明形式。
從這個(gè)角度講,與中國(guó)的農(nóng)耕文明發(fā)生最為密切關(guān)系的文明形式就是游牧文明形式。在中國(guó)的北方、東北方、西方、西北方、甚至于西南方的一些區(qū)域,歷史上或者說(shuō)現(xiàn)今仍然布滿了以游牧形式生產(chǎn)和生活的文化群體。雖然在這些區(qū)域里,不同的文明形式帶來(lái)的政治制度和意識(shí)形態(tài)上的沖突已經(jīng)不存在了,因?yàn)橛文羺^(qū)域內(nèi)也已經(jīng)具有大量的農(nóng)耕文明形式的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方式,兩種文明形式早就找到了各自的共融點(diǎn)。
但是,這兩種文明形式在中國(guó)的歷史上卻演繹了許多文明形式“決戰(zhàn)”的故事。這兩種文明形式在許多時(shí)候,始終處于一種沖突和矛盾之中,對(duì)于這樣的斗爭(zhēng),我們可以說(shuō)是草原游牧政治集團(tuán)和土地農(nóng)耕政治集團(tuán)在政治和經(jīng)濟(jì)利益上的矛盾沖突,這是根本的,但同時(shí)也是兩種文明形式的沖突。從根本上來(lái)講,土地農(nóng)耕政治集團(tuán)在長(zhǎng)期發(fā)展中,會(huì)直接在土地上向游牧土地?cái)U(kuò)張,這應(yīng)該是歷史上的基本趨勢(shì),這樣,就會(huì)與草原游牧政治集團(tuán)發(fā)生直接的關(guān)于生存空間沖突,反之亦然,草原游牧政治集團(tuán)也會(huì)從土地農(nóng)耕政治集團(tuán)那里爭(zhēng)奪土地。
在中國(guó),華夏文明實(shí)際上就是在游牧文明形式和農(nóng)耕文明形式的不斷的沖突中,一步一步地發(fā)展過(guò)來(lái)的。也就是說(shuō),雖然說(shuō)華夏文明是以農(nóng)耕文明為主體建立起來(lái)的,但它在這種沖突中也包容了游牧文明的諸多因素,中國(guó)的游牧文明也在這種沖突中豐富了自己。在中國(guó)古代,參與華夏文明構(gòu)建的還不僅僅是北方的游牧文明,南方型的農(nóng)耕文明也參與了這樣的構(gòu)建,但這樣的構(gòu)建是同類異形式的沖突,是強(qiáng)勢(shì)文化針對(duì)弱勢(shì)文化的影響。而與北方的游牧文明的沖突,是異形式文化的沖突。
在中國(guó)的華夏文明中,除了游牧文明形式的影響和南方型的農(nóng)耕文明形式的影響外,我們還可以看到更為久遠(yuǎn)的狩獵文化的遺跡。這種遺跡的來(lái)源有兩個(gè)方面:一是在與北方的游牧文明形式的沖突中,受留存于其文明形式中的狩獵文化的影響而來(lái);二是農(nóng)耕文明形式中自身的狩獵文明遺跡的影響。還有,采集文明的遺跡也在我們的華夏文明中有所呈現(xiàn),它也是我們的文明形式的一個(gè)組成部分,至今,我們?nèi)匀辉谀戏降纳贁?shù)民族中看到這樣的文化遺跡。
中國(guó)的華夏文明是一個(gè)包容性極強(qiáng)的文明體,它以農(nóng)耕文明為主體,建立了以農(nóng)耕為基本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體系,建立了基本的信仰體系、精神觀念體系、哲學(xué)體系、藝術(shù)文化體系,以及政治制度體系和文化,并且在歷史上包容了游牧文明、南方山地農(nóng)耕文明、狩獵文明等異形式文明和異類型文明,并且在多種文明形式的沖突中,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化機(jī)制,使我們的華夏文化不但有數(shù)千年不間斷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在今天仍然具有在新的文明形式中自新的能力。
在經(jīng)過(guò)幾個(gè)世紀(jì)的中國(guó)人的努力,在大量吸收了西方現(xiàn)代文明形式力量的基礎(chǔ)上,我們國(guó)家又完成了由農(nóng)耕文明為主導(dǎo)形式的華夏文明向以科學(xué)文明為主導(dǎo)形式的華夏文明的蛻變。同時(shí),我們的華夏文明中,基本的信仰體系、精神觀念體系、哲學(xué)體系、藝術(shù)文化體系基本未變,但包容了更多的東西,使自己變得更為宏大和豐富;以農(nóng)耕為基本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體系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但仍然保持了一定的農(nóng)耕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呈現(xiàn)了此方面的文化多樣性。在政治制度體系和文化上保持了許多根性文化的東西,也包容了更多屬于現(xiàn)代社會(huì)政治制度的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