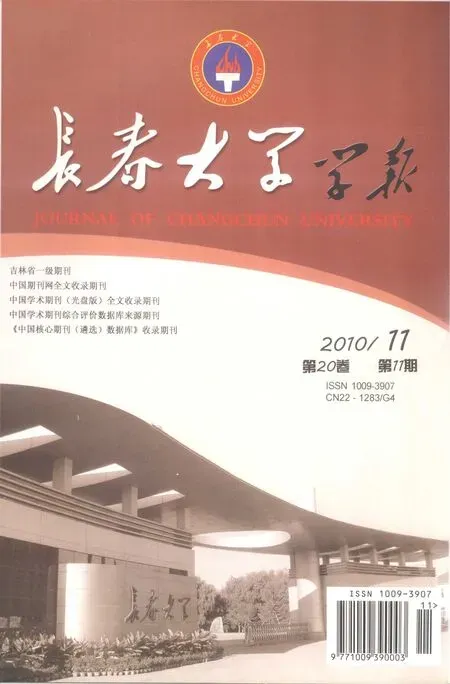認知語境在隱喻理解過程中的作用
路 靜
(長春工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在認知語言學研究中,隱喻認知是一個重要內容。隱喻不再被看作是一種可有可無的修辭方法,而是人類認識世界過程中一種重要的認知模式。它是用一種事物去理解另一種事物,用一種經驗去體會另一種經驗。萊考夫與約翰遜曾指出:“隱喻普遍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不但存在于語言中,而且存在于我們的思想和行為中。我們賴以思維和行動的一般概念系統,從根本上講是隱喻式的。”[1]在隱喻的運作機制中,語境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Ortony針對歷史上種種隱喻定義的缺陷指出:“任何忽視語境因素的隱喻定義都是不完整的。”[2]離開了語境,隱喻的產生和理解都是不可能的,它的強大功能也是無法實現的。一些專家學者曾對語境知識在隱喻理解過程中的作用進行過論述。束定芳教授從語境本身的特點、語境信息的量和人類知識結構三個方面論述了語境對隱喻理解的影響。但傳統的語境概念幾乎是包羅萬象的,本文僅對認知語境在隱喻理解過程中的作用進行探討。
1 認知語境
在人們進行言語交際的過程中,有些現象僅運用具體語境因素是無法解釋的。熊學亮在其著述《認知語用學概論》中曾提到斯高倫做過的一個實驗。斯高倫給一些美國小朋友看一張照片,照片上有一條兩側長著密密樹林的大道。他問小朋友:“這是美國,樹后是什么啊?”小朋友們回答:“是農莊。”他又把同樣的照片給另一組小朋友看,并問:“這是蘇聯,樹后面是什么啊?”小朋友們答:“是軍事基地。”顯然,這些小朋友并未親眼見過蘇聯的軍事基地,他們也并未親身經歷過這樣的場景,所以并不是具體的語境使他們作出這樣的判斷。他們之所以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是由于受到身邊家人、老師以及外界宣傳報道的影響,在他們的知識結構中已形成了這樣的社會心理表征,即“語用者通過經驗已經把有關的具體語境內在化、認知化了。”“原來的具體語境因素,結構化后就變成了認知結構單位和關系。”[3]除了社會心理表征(或意識形態結構),認知語境主要還包括直接場合、語言上下文知識和背景知識。在實際應用中,認知語境是以“知識草案”和“心理圖示”為基本單位進行具體操作的。
2 隱喻的理解
束定芳將隱喻的理解分為兩個階段,即隱喻的辨認階段和隱喻意義的推斷階段。隱喻的辨認是指“聽話者通過明確信號或語義沖突及其性質做出對句子須作隱喻性理解的判斷”;隱喻意義的推斷是“根據隱喻所涉及的兩方事物之間的關系對該隱喻實際意義或說話者真正意圖進行推斷的過程。”[4]
在隱喻的辨認階段,首先要對隱喻涉及的兩個對象進行辨認,看二者是否屬于不同的范疇,因為“差異是構成隱喻的必要條件之一”[4]。在這一過程中起作用的便是知識草案和心理圖示,因為辨認過程實際上也就是對所涉及概念或活動的知識草案和心理圖示進行提取然后比較的過程。“語言自身僅起著激活知識草案的作用,激活后的草案先按有關具體場合的知識形成心理圖示,然后再根據不同的文化知識,在社會心理表征層次上進行交際準則的排列,從而導致不同的推理結果。”[3]比如在理解“婚姻是一場不得分的比賽”這一隱喻時,首先要對“婚姻”和“比賽”這兩個概念進行辨認。“婚姻”的知識草案主要涉及“兩個人共同生活,彼此忠誠,互相照顧”等。而“比賽”的知識草案則涉及“競爭,勝負,輸贏”等。可見二者分屬于不同的范疇并且不具有任何相似性,因此可斷定需對該句話進行隱喻性理解,需要進一步根據語境從其他角度猜測其可能的意義,于是進入隱喻理解的第二階段:根據隱喻所涉及兩方面之間的關系推斷該隱喻的真正意義。
在隱喻理解的第二個階段,讀者或聽者需要調動認知語境內的所有知識對其展開聯想和猜測。如果將隱喻用“S是P”來表達,該過程就是在P的知識草案和心理圖示中尋找可能與S相似之處的過程。由“比賽”隱含的“競爭”可聯想到“較量、爭斗”;由“爭斗”可聯想到“婚姻”中夫妻雙方發生的爭執,于是發現“比賽”與“婚姻”在“爭斗”這一屬性上存在著相似之處。嚴格地說,“爭斗”既不是“婚姻”的顯著特征,也不是“比賽”的顯著特征。但既然二者共處于這一結構中,它們一定有著某種相似之處。只有在二者的知識草案和心理圖示中進行深入查尋和反復比較,才能發現二者共有的但并不顯著的特征。于是原本分屬于兩個不同范疇的本體和喻體在第三個范疇——“屬性范疇”[5]中得到了統一。
有些話語從經驗和概念角度來看,是異常的,違背語用準則的,只有經過認知語境的操作才能被理解。束定芳曾引用過《中外文摘》中的一個例子。“……男青年踩了某作家,非但不道歉,還理直氣壯。作家怒目而視,男青年心慌氣短:‘你還能把我吃了?’作家不慌不忙道:‘不敢,我是回民。’”從字面乍一看來,作家的回答與男青年的問話毫不相關。但根據合作原則,它應該是對對方問話的回答,所以此時就需要在認知語境中搜集所有與“回民”相關的信息。在“回民”的知識草案和心理圖示中最顯著的特征就是不吃豬肉,因此作家的回答與男青年的問話是相關的,他在間接地說男青年是豬。
由于認知語境在隱喻理解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不同的人因其認知語境的不同會對同一隱喻產生不同程度的理解。錢鐘書曾將學生的作業比作臟衣服,剛洗干凈了一撥,下一撥又來了。有過執教經驗的人在理解該隱喻時絲毫不費力氣,因為在他的認知語境中關于“作業”的知識草案和其他人如農民、商人、學生等是不同的。在教師的認知語境中,“作業”的知識草案包括了“臟亂、要經常批改”的屬性,而其他人的認知語境中則一般不會包括這些特點。因此,在隱喻理解過程中存在著個體差異。
3 結語
本文簡要討論了認知語境在隱喻理解過程中的作用。在隱喻理解的兩個階段中,在隱喻的辨認階段,認知語境對隱喻涉及的兩個概念的知識草案和心理圖示進行辨認和比較,發現二者相異后,作出需對其進行隱喻性理解的判斷。然后,在隱喻本體和喻體的知識草案和心理圖示中進行深入查尋和反復比較直至找到二者的相似之處,從而對隱喻的意義進行推斷,完成隱喻理解的第二個階段。脫離認知語境,隱喻理解就無法進行。
[1]Lakoff G,Johnson 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束定芳.論隱喻的理解過程及其特點[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0(4).
[3]熊學亮.認知語用學概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4]束定芳.論隱喻的運作機制[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2(2).
[5]賈志高,程杰.隱喻語言中的范疇化[J].山東師大外國語學院學報,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