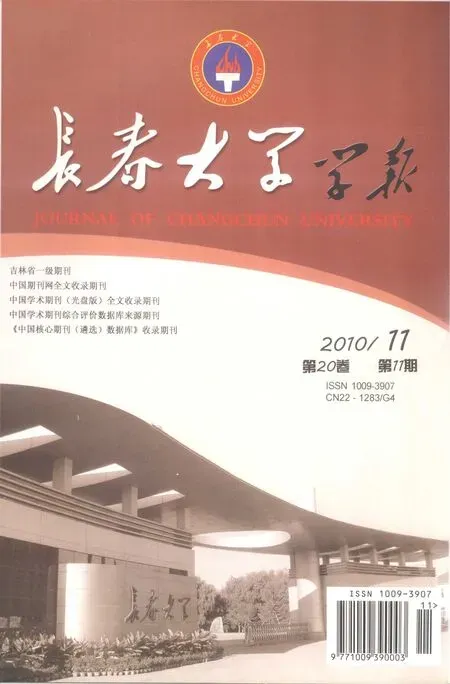論日本町人和中國儒商倫理思想的差異
何 劍
(長春工程學院 人文社科部,吉林 長春 130012)
論日本町人和中國儒商倫理思想的差異
何 劍
(長春工程學院 人文社科部,吉林 長春 130012)
日本町人與中國儒商所處的歷史時期相近,雖然各自倫理思想都具有儒家文化的背景,但是由于價值觀、道德意識等方面的異同,因而導致其各自倫理思想的差異性也較大,對二者的倫理思想等進行深入比較,有助于更加準確的理解二者倫理思想之異同。
日本町人;中國儒商;倫理思想
日本町人是指自中世紀初期至明治維新以前,居住于城市的手工業者和商人,町人占當時全國人口的5% -6%,人數約50萬左右。町人與武士和農民一樣,身份上是固定的,不可自由改變。正因為如此町人才形成了一股力量,而且產生了很多鼓吹町人倫理思想的著作,并逐步形成了倫理思想體系。從而在日本由封建社會向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轉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中國儒商是指有文化教養的,以儒家理念為指導從事商品經營活動的商人。在中國歷史上,儒商的發展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發展過程,在士、農、工、商四民之中,儒為四民只首,而商為四民之末,儒與商有天壤之別。由于封建當權者一直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因此商人備受貶抑,直到明末清初資本主義已經萌芽,這種傳統的儒家倫理對商人的貶抑才有了很大的改觀。“棄儒從賈”蔚然成風,至此才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儒商。
1 町人與儒商對“仁”的理解
在日本的德川幕府時期,對商人有一種偏見,“商社性惡論”。這種偏見也是對商人社會低下的卑視。為此,町人哲學家石田梅巖主張商人之道為仁。他說:不知商人之道者,則貪婪亡家。若知商人之道者,則應離欲心,勉仁心。此乃是學問之德。梅巖提倡商人要離“欲心”,行“仁心”,把“仁”作為商人必備之德。這種思想還是對職業的“行”無貴賤觀點的發揮。梅巖把商人作為“市井之臣”
來輔助君治理天下,商人在社會機能運轉中,具有士農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商人要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就要以行“仁”為道,梅巖特意在“月會”上,以“行仁為本”這一題目,教導他的門人弟子說:我儒以仁愛萬物,不殺無益之物。一家有仁,則一國興仁。堯舜率天下以仁,則民從之。作人處事應以仁為本。梅巖從儒家觀點出發,認為只有行“仁”道,才能治家、治國。
商人作為“市井之臣”,對社會起應有的作用,也必須以行“仁”為本。“仁”字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與精髓,在造就了明清晉商企業及其領軍人物自強不息與民胞物與、厚德載物的優良品格與作風。“力行近乎仁”,晉商的創業者們在商業領域辛勤耕耘,憑著頑強的毅力、不屈的精神,堅毅拼搏,勤苦創業,節儉持家,積累商業財富,歷經數代人、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終于成就了一個個財力雄厚的晉商企業。成功的晉商們力戒為富不仁,堅持“仁厚”之道,如:著名的喬家大院歷代主人幾乎個個樂善好施,關心公益,據光緒八年《祁縣志》記載:光緒三年,山西大旱災,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餓死數百萬,喬家大東家喬致庸在家鄉出巨資賑災,設立粥棚,救濟災民,救民甚眾,受到褒獎;其子喬景儼執掌家業時,慷慨為家鄉捐資興修水利工程,資助祁縣中學堂和太原私立光華女子學院創立,向窮人施舍醫藥等,深得時人贊譽。秉持“仁”道的晉商用自己的“仁”行樹起了明清山西企業的良好公眾形象,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譽度,自然也就贏得了數不盡的有形資產和巨大的無形財富。
如明正德年間,安慶潛山、桐城一帶發生災荒,糧價暴漲。休寧糧商汪平山并“不困人于厄”,將自己蓄儲的谷粟,“悉貸諸貧,不責其息,遠近德之”。清代休寧人吳鵬翔,僑寓漢陽,時值漢陽饑謹,“鵬翔適運川米數萬石至,計之可獲利數倍”,但吳鵬翔為救人于水火之中,“悉減值平巢,民賴以安”。為此,“自大吏至郡縣咸與嘉獎”。清代歇縣商人吳柄也是以“仁心”經商的典型。他“平生仁心為質,視人之急如己,力所可為即默任其勞,事成而人不知其德。其或有形格勢阻,輒食為之不寧”。儒商的倫理思想中“義”是經營立足的根本,“信”是經營興旺的標志,而“仁”則是儒商經營理念的中心范疇。儒家學說創始人孔子認為,所謂“仁”就是“仁者愛人”。這有兩層含義,一是愛親,“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即愛血緣之親;二是愛親情以外的他人,“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人就是尊重人、關心人、幫助人。而要實現仁的要求,就應由近及遠地愛人,由愛血緣之親,推及到非血緣之親的他人。實現仁的途徑,孔子認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者愛人”的倫理道德思想被后來的儒商嫁接到經營管理領域,以“愛人”為出發點,追求人際關系的和諧,形成了以“仁”為中心的儒商經營理念。致使儒商在經商過程中著意塑造商家的仁慈形象,如參與娠災、樂善好施等,培養“潔身自好”“人品端正”的素質以樹立商家的良好名聲和仁者風范。
2 町人與儒商對“義利”的理解
町人的“義利觀”思想的主要倡導者中井竹山,竹山所主張“利即義”的倫理思想中,其“利”是指“上下共利”,其“義”也是指“上下共利”。無論是庶民只為自己的“利”,還是幕藩統治者只為自己的“利”,都只能稱為“私利”,而不能稱之為“義’,尤其執掌政權的統治階級,只有做到“上下共利”才是“義”。竹山這種將“上下共利”視為“義”,而否定歷來官方以所謂“公利”為“義”的思想,意義十分重大。因為它打破了此前將農工商之“利”視為“私”而將幕藩官方之“利”視為“公”的統治階級倫理觀,為建立以庶民大眾為“公”、以庶民大眾之利為“義”的價值倫理,提供了理性主義的理論依據。
在儒家倫理思想中的義利觀,是一種把義、利對立起來的義利觀。孔子強調“見利思義、義然后取”“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荀子明確提出“先義后利”,“重義輕利”“以義制利”。“無商不奸”“無奸不商”的觀念就是在這種思想的背景下人們商人的看法,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儒商義利觀在強調義、利對立的前提下。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義、利的統一性,并且認為主張重義輕利,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不合理性。從這一點來看,儒商的的義利觀,相對儒家傳統的統義利觀來說,有其歷史性的進步意義。
隨后在商品經濟活動的應用過程中造就了儒商“義利兼顧”的商業倫理思想。在商業發展的初期,儒商是崇尚儒家倫理的“義利兼顧”的商人的典型。儒商在追求“利”的過程中,以“義為準繩”,“以義取利”、“見利思義”、“義然后取”。而決不能“見利忘義”、唯利是圖。儒商的義利觀是一種把“義和利”統一起來的義利觀。在一些儒商的傳記中,有不少一邊求利,一邊行仁義的富商大賈。他們在經商過程中能夠自覺的做到是義利兼顧、義利兼得。儒商在從事商業活動時,所關注的不僅是其商業活動是否可以獲利,而且還有其行為是否能夠具有道德上的正值意義。以義統利,義以生利作為基本的行為準則。
而中國儒商的“誠信”狀況,處于不同時期的學者對此有各自不同的估價。但“誠信”確為近世儒商重要倫理。馳騁商界幾百年的晉商和徽商,也都具有誠信的特征。徽商大都奉行“待人接物,誠實不欺”。以“誠信”作為重要的商業經營理念,在商業交往過程中,由于“誠信”能降低交易成本,并促成了儒商的事業成功,同時也促進了社會整體經濟發展,因而在明末清初的儒商群體中對“誠信”認識和理解的歷史進步性應給予充分肯定。在儒商“誠信”道德選擇背后,實在也埋伏著物質利益驅動。康海在《扶風耆賓樊翁墓志銘》中記商人樊現語云:“貿易之際,人以欺為計,予不以欺為計,故吾日益而彼日損。誰謂天道難信哉!”對“日益”的預期,使儒商選擇了“不欺”和“誠信”;而“日益”的效果,又進一步強化了“誠信”意識。為了強調“誠信”合理性和神圣性,又進而將之“天道”本體化,上升到根本性倫理的高度。經濟行為的相應文化支撐,道德支持只是其中之一,“誠信”又只為道德之一。
3 町人與儒商對“儉約”的理解
“儉約”是町人倫理思想的重要概念。町人哲學家石田梅巖的《儉約齊家論》就是其闡述“儉約”的核心文獻。名稱即透出濃厚的儒學特色,梅巖在《齊家論》中論述:町家之事瑣細,難用大道言之。吾以為不然。自上至下,職分雖異,其理則一。得心而行節儉時,則家齊、國治、天下平。此焉非大道乎?所言儉約者,畢竟是為修身齊家耳。《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以修身為本。修身何有士農工商之別!修身以何為主?乃此心也。若以此身之微而喻之,猶如大倉中之一粒米。然而,成天、地、人之三才,唯心而已。"故士農工商雖職分各異,會得一理,則言士之道與農工商通,言農工商之道與士通,何必四民之儉約要分別論耶?言儉約無它,乃天生之正直也。天降生民,萬民皆天之子也。故人乃一小天地,本無私欲,故我物即我物,人之物乃人之物,貸物收領,借物返還,絲毫不為我私,此乃正直也。若行此正直,世間一同和睦,四海之中皆兄弟也。“私欲雖害世,不知此之味而成儉約,皆至吝,為害甚也。吾所言由正直至儉約,則至助人。”“若要守正直,首當遠離名聞利欲。”“儉約非僅衣服財器之事,總之,乃非私曲也。教以正心為志,退而應有工夫。”
這些話的關鍵點,在于將“儉約”與“正直”聯系了起來,并說明“由正直至儉約”,而且區分了儉約與吝嗇。他還有許多論正直和儉約的話,如《語錄》卷十一切忘懷而能守法則為儉約,“圣人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隨心之所欲亦成天下之法。”他不止一次講“隨法”就是儉約。這個“法”既是“物”之所具有的,也含幕府“實定法”之意,反映了石田梅巖思想的多重性與過渡性質。
眾所周知儒家思想對儒商的影響是全方位,多方面。所以對于儒商的“儉約”的倫理思想,還是要從傳統的儒家思想談起,儒家的始祖孔子雖沒有很系統地論述過節儉問題,但他一貫主張節儉消費。奢侈豪華的生活方式是當時奴隸制禮節的一個顯著特點,孔子卻提倡樸素的禮樂制度和道德風尚。在他看來,“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寧固”,他認為人君能否守禮制,節嗜欲和尚節儉,直接關系到國家社極之盛衰存亡。對于一般庶民及士大夫階層,他也同樣強調應該用財有制,克儉持家。他提出“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位”“中人之情,有余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儒家都“儉約”的理解和認識,也是儒商對“儉約”的理解,在現有的歷史資料的記載中,儒商中的晉商和徽商在經商的過程中,也不同程度的認識到“勤儉”“節約”是經商之根本。深明其重要性。
4 町人與儒商的社會生存背景導致差異的產生
從町人和儒商的各自社會生存背景來看,二者的當時在各自的國度里所處的地位和身份基本上相同,都是在當時商品經濟逐漸發展的過程中,重農抑商的觀念逐漸的有所改觀的前提下,才逐漸發展起來的。而町人對“仁”和“義利”的理解與儒商卻有很大的差異。但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町人和儒商對待“誠信”的觀點,確不近相同。雖然二者理解“誠信”的前提都是指在經商的過程中要“誠實守信”,“不欺不詐”,但在深層次的理解方面就有所不同了。町人對“誠信”的理解是把“誠信”在經濟交往的過程中的普遍意義,上升到了道德層面,誠信在維護商品經濟交換安全的同時,也是個人修養和品德的體現。在中國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下,“誠信”無論在圣人的思想中,還是在國人的道德實踐中都不是最基本的道德義務,它必須服從其他的道德原則,信隨義走,“講信”總是和“重義”相聯,“背信”和“棄義”相關。“誠信”總是游離于“義利”之外,因此儒商的對“誠信”的理解并沒有上升到道德層面上來,儒商的誠信道德總體來說是適應自然經濟狀態的誠信觀,儒商講誠信的目地,則完全是為了商品經濟交換的安全,在儒商“誠信”道德選擇背后,實在也埋伏著物質利益驅動。對“誠信”的不同的理解,雖然是在町人與儒商的倫理思想中一小部分的差異,但也深刻的影響著各自倫理思想體系的構建。
[1] 何劍.町人與儒商倫理思想之比較[D].延吉:延邊大學,2007.
[2] 劉金才.町人倫理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3] 姚凱.日本城下町的形成和發展及其原因[M].北京:日本研究,1990.
[4] 潘暢和.中韓日儒學比較論[M].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2005.
[5] 葉坦.中日商品經濟思想比較研究[J].河北學刊,2005(2):35-37.
The differences of ethics between Japanese merchants and Chinese confucian entrepreneurs
HE Jia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Changchu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chun 130012,China)
Japanese merchants and Chinese confucian entrepreneurs are living in the same period,their ethics have the background of Confucian culture,but because of values and moral consciousness,the differences of their ethics are larger.The detailed comparison on both ethics will offer a mor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ethics.
Japanese merchant;Chinese confucian entrepreneur;ethics
B313
A
1009-3907(2010)11-0097-03
2010-10-18
何劍(1977-),男,吉林長春人,碩士,助教,主要從事中日哲學比較研究。
責任編輯:沈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