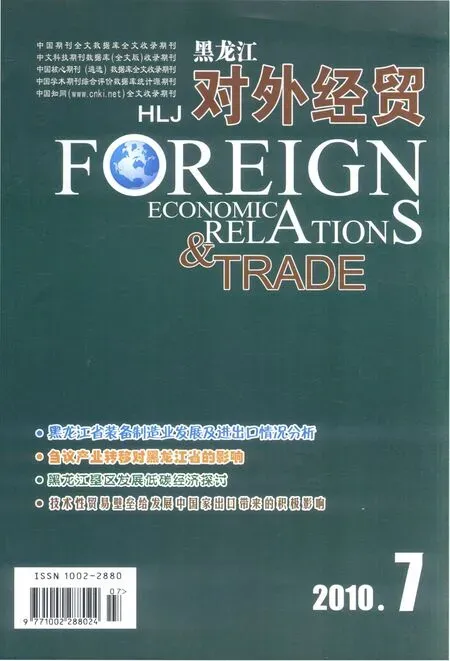對于我國土地農民所有制的思考
楊 陽
(山西財經大學,山西 太原 030006)
一、問題的提出
在目前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下,面對的土地問題主要包括:土地產權主體不明晰、土地使用關系不穩定、土地投資情況持續惡化、掠奪式經營時有發生、土地細碎化現象日益嚴重、征地過程中農民的土地權益難以保障等。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對于我國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紛紛提出了自己的觀點,總體來說主要包括:土地農民所有制(即土地私有制)、土地集體所有制、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和國有永佃制。在這幾種模式中,土地農民所有制無疑是討論最多、爭議最大的目標模式,反對者基于歷史和現實的一些現象和結果,對土地私有提出了很多反對意見。本文對反對土地私有制的各種理由進行了梳理和總結,并從理論和現實及解決現實中所面臨的土地問題的角度出發,對農民土地所有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進行了分析。
我國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選擇標準是判斷土地農民所有制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依據。筆者認為土地制度改革方向的根本選擇標準應該包括兩部分內容:一是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目標;二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則。我國的土地制度改革要以維護農戶的權益為根本出發點,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則,當前所提倡的“效率與公平兼顧”原則過于含糊籠統,應該對兼顧作出具體化的解釋。筆者認為以在有限公平的條件下實現效率最大化作為當前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則較為符合農民意愿和我國國情。所謂效率,就是堅持土地制度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努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所謂公平,就是在當前農民的非農就業途徑不暢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應該充分重視農民的土地財產權利,努力實現其在土地制度改革的初次產權分配過程中的起點公平。
二、對反對土地農民所有制觀點的辨析
學術界對于土地農民所有制的改革方向一直爭論很大,反對者提出了很多的反對意見,其觀點如下:
觀點一:土地私有會導致土地兼并、激化社會矛盾、導致社會危機,甚至會導致農民戰爭。
從歷史上來看,雖然清朝以前土地兼并的具體情況我們不得而知,但是相關學者在研究史料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是所謂土地在一個王朝中由初期到末期越來越集中、在兩千年封建社會中由前期到后期也越來越集中的兩個趨勢并不存在。清朝末年到民國時期的土地兼并情況,很多學者通過測算土地基尼系數指標得出的結論是當時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土地基尼系數都高于中國,我國是地權集中程度最低的國家之一。從世界上來看,飽受殖民統治之苦的印度、拉美國家在實現民族獨立之后,雖然沒有經歷激進的土地制度改革,但在土地私有制下土地集中的現象并未進一步加劇,反而呈現出分散的趨勢。以印度為例,1954年該國土地分配的吉尼系數是0.63,1961年下降至 0.59,如今大約在 0.5左右;而墨西哥作為世界上曾經土地最集中的國家,其土地基尼系數從 1930年的 0.96降到了 1960年的 0.6,仍然很集中,但與過去相比還是有所改變。最后從我國的現實情況來看,當學界還在擔憂土地私有會導致土地兼并的時候,實際的土地管理部門反對土地私有的理由卻是土地私有會導致他們再也無法搞土地批租了,也就說他們再也沒法搞“賣地財政”了。所以說,在沒有“超經濟特權”干擾的情況下,地權歸農和土地自由買賣不是促進了兼并而是有效控制了兼并,“耕者有其田”不會導致“耕者失其田”。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縱觀古今中外,包括我國的傳統社會和印度、拉美,真正意義上的大規模土地兼并不是通過自由交易實現的,而是通過“超經濟強制”的辦法實現的;而社會危機的爆發則是由天災戰亂、賦役負擔過重等原因引發的官民矛盾所引起的。
觀點二:土地保障是對社會保障的代替,是農民最后的保障,土地不能私有是出于社會保障的考慮。
現在,一些學者反對土地私有的另一理由是土地保障作為對社會保障的替代,而社會保障又是不能私有化的,所以土地是不能私有的。這種不允許農民自由處置土地就是“保障”了農民的“土地福利論”實際上是似是而非的。
首先,土地保障是一種社會保障的提法就有問題。因為作為國民收入二次分配的社會保障應該是無償的,而土地與資金、技術、勞動力等其他的生產要素一樣,只有與勞動相結合才能產出財富收入。如果承認農民為城市做出貢獻后回家種田是一種保障的話,那么無異于承認工人在退休后獲得社會保障的方式就是繼續工作。
其次,如果土地不是一種社會保障,那么它是農民最后的保障嗎?顯然也不是。比如說農民生病了,治療需要一大筆的費用,但是他卻不能自由處置據說是他“最后保障”的土地以換得足夠的錢去看病。這種所謂的“保障”實際上只是保證了農民不能賣地,這顯然不是一種保障而是負保障。
還有人拋出“悲慘的出售”問題以反對土地私有,“悲慘的出售”問題是指當普通的農戶無法得到農業生產和銷售保險和家庭最低生活保障時,由于面臨無法避免的風險(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他們往往以極低的價格將土地出售。這意味著當自然災害來臨的時候(或者其他的原因),農戶為了渡過生存的難關而出售土地,當自然條件好轉的時候這些農戶卻沒有能力重新購回土地,從而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誠然,這種悲劇是有可能發生的,但它沒有成為督促政府建立社會保障的理由,反而成了為某些利益集團剝奪農民地權辯護的借口,這種現象顯然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觀點三:土地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不利于土地的合理配置和規模經營。
這種觀點認為平分地權的土地私有制會造成土地的細碎化現象嚴重,嚴重違背土地應該優化配置的原則。然而事實上這種觀點也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土地配置是否達到最優,并不是取決于土地集中的程度,而是取決于土地能否和資本以及勞動自由結合,以避免土地的拋荒或勞動、資本的閑置。國外的現實經驗證明,在所有生產要素均可以自由流動的典型市場經濟條件下,土地是不會排斥勞動和資本的,土地與各種要素的自由流動與組合其結果就是土地的配置日趨優化。與之相反的是,非市場化的制度安排總會使土地與其他要素的組合產生這樣或那樣的扭曲。從我國的現實情況出發,土地私有所導致的土地細碎化實際上正是土地資源得到優化配置的體現,因為在當前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不暢的情況下,土地細碎化代表的正是勞動和土地自由結合的實現,是反映國情的資源最優配置。土地的規模經營應該隨著農村勞動力的不斷向外轉移,通過市場機制自然地擴大。如果單純從提高土地效率的角度出發搞規模經營而把農民趕出土地,帶來的問題只會更多。
三、實行土地農民所有制是解決土地問題的根本途徑
從如何徹底地解決現實中我們所面臨的土地問題的角度出發,闡述實行土地農民所有制的可行性和必然性。
問題一:農地投資嚴重不足,掠奪式經營時有發生。
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農地產權的不穩定性使得農民對自己承包的土地收益缺乏長期的預期,也就說農地對于農民的價值因為私有制的缺失而降低了。從理論上來說,在現有土地制度下,土地對于農民而言實際上是一項風險資產,而且由于農民所擁有的土地產權不完整,農民對待風險的態度一般是風險厭惡型的。在這種條件下,農戶肯定要減少對農地的投資,特別是中長期的投資。如果這種狀況嚴重到一定程度,農業生產對于農地的消耗所帶來的農地生產率的下降將得不到足夠的補償,并最終導致土地質量的下降。而且由于承包土地的頻繁調整,新的土地承包者基于上述原因更加不會對土地進行投資,從而形成了對農地進行掠奪式經營的惡性循環。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如何保障農地產權的長期穩定性。顯然,對于農戶而言,最具有長期穩定性的產權安排是土地歸農民個人所有。
問題二:土地的非市場配置導致土地的細碎化和土地規模經營的無法實現。
農地在村集體內部的平均分配以及農村人口總量的增長導致了我國農村土地細碎化現象的出現。同時我國農民非農轉移的途徑不暢和障礙太多,農民無法真正的從土地中完全抽離出來,離開農村走向城鎮,這又導致了土地細碎化日益嚴重而得不到解決。在現有體制下,雖然政府允許土地流轉,但是由于農地的集體所有制的限制,土地流轉在村集體間的交易成本過高,而使農地只能在集體內部小范圍地流轉,無法形成較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市場,因而也就無法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土地規模經營。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土地細碎化和土地流轉困難都是由于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制度障礙所引起的。如果農地歸個人所有,對土地的處置可以為農民在城鎮的發展提供啟動資金,從而形成農民非農轉移的激勵力量,進而在整體上推動農村人口的轉移和農村城鎮化的發展。另一方面,土地的私人所有和自由交易可以推動大范圍、跨區域的土地租賃市場的形成。制度障礙的破除和土地交易成本的下降將會使土地邊際收益較低的農戶自動地將土地出租給邊際收益較高的農戶,從而使土地越來越集中于種地能手的手中,實現土地的規模化經營。
問題三:征地過程中,失地農民的土地權益難以得到保障。
征地過程中出現種種突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現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著巨大的制度缺陷。在我國目前實行的土地二元所有制下,農村集體所有土地的權屬轉移只能通過征收和征用的方式實現。這種制度設計導致了政府土地管理部門和農村集體之間在土地要素交易過程中的地位不平等。國家給予被征地集體的僅僅是補償價值,而不是市場價值,從而使農民的土地權益在征地過程中受到了極大的傷害,而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在土地價格雙軌制下獲得了巨額的土地收益。
解決政府和農民在土地交易過程中地位不對等和土地價格雙軌制等問題的關鍵是農地產權主體的明晰和土地交易的市場化,根本出路是土地的私有化。因為在私有制下,農民作為土地的供給者可以直接與土地需求者進行談判,并按照市場價格交易土地,獲得土地增值的全部收益,進而從根本上解決現有土地征用制度下存在的種種問題。
四、結論
通過上述正反兩方面的分析,可知以農民土地所有制作為我國未來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可行的。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土地問題的解決可以“一私了之”,因為伴隨著土地的私有化,還有很多諸如保護農民土地產權的法律如何制定、賣地農民的身份轉換機制和社會保障機制如何建立、耕地如何保護等問題需要解決。也就是說,我國土地制度的改革必然要經歷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但是我們更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這場改革的緊迫性,敢于克服改革所帶來的陣痛,努力朝著我國土地制度改革的既定目標前進。
[1]蔡繼明,鄺梅.中國土地制度改革國際研討會論文集[C].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9:151-160.
[2]賀衛,伍山林.制度經濟學[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87-109.
[3]秦暉.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與農民權利保障[J].探索與爭鳴,2002(7).
[4]文貫中.解決三農問題不能回避農地私有化.http://www.people.com.cn,2006-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