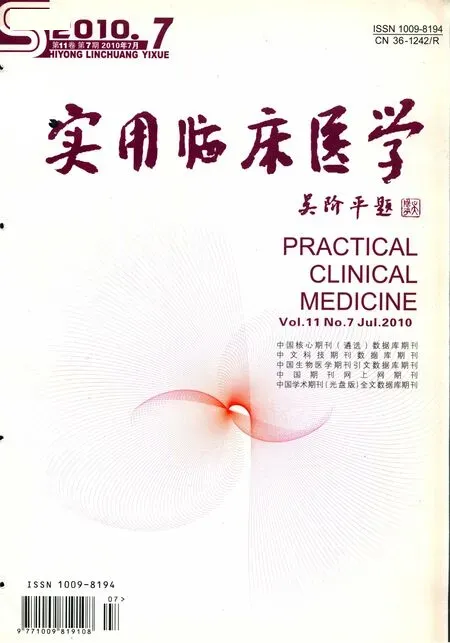谷胱甘肽-s-轉移酶、幽門螺桿菌感染與胃癌關系的研究進展
馬艷春(綜述),趙亞剛(審校)
(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消化內科,廣州 510010)
谷胱甘肽-s-轉移酶(GST)是一種多功能的Ⅱ相代謝酶家族,也是一個同源二聚體酶的超基因家族,普遍存在于各種生物體內。在哺乳動物各組織中均含有不同種類的GST,其含量和活性亦各不相同。GST可分為膜結合微粒體家族和胞質家族2大類。哺乳動物GST至少具有8類同工酶:α、δ、κ、π、θ、ω、μ和內質網膜結合微粒體型。而在人GST家族中有5 種胞漿型同工酶 :同工酶 α、μ、θ、π、ζ。主要組織分布分別為“肝、腎、小腸”、“肝、心臟、肌肉” 、“紅細胞、胃腸道”、“胎盤 、肺” 、“肝、外周血” 。基因分別位于 6p12、1p13.3、22q11.2、11q13、14q24.3;基因位點分別為谷胱甘肽-s-轉移酶 A1(GSTA1)、A2、谷胱甘肽-s-轉移酶 M 1~ 5(GSTM 1~5)、谷胱甘肽-s-轉移酶 T1(GSTT1)、T2、谷胱甘肽-s-轉移酶 P1(GSTP1)、谷胱甘肽-s-轉移酶 Z(GSTZ)。由此可見,不同的基因表型是由編碼基因多態性決定的。本文就GST、幽門螺桿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與胃癌關系的研究進展作一綜述。
1 GST-π
GST-π主要分布在胎盤、泌尿系統、消化系統上皮。π的基因包括人胎盤型GST(GST-π)和大鼠胎盤型GST(GST-P)。1979年Marnervik等首次從胎盤組織中分離出一種酶,并命名為谷胱甘肽s-轉移酶-π,又稱為胎盤型谷胱甘肽s-轉移酶。1991年Reinemer P.等[1]首先從豬肺中獲得GST-π的晶體結構。隨后確定了人胎盤GST-π的晶體結構[2]。GST-π是由2個多肽亞基折疊而成的一種酸性蛋白,相對分子質量為8萬,每個亞基由209個氨基酸構成,編碼基因位于第11號染色體上(11q13),包含7個外顯子和 6個內含子,全長2.8 kb。與其他GST不同的是,GST-π至少有3個底物結合點,即G位點、H位點和Luisa R.等[3]發現的第3個底物結合位點,其氨基酸序列尚未確定。
GST-π的生物學特性:①催化GSH的巰基與各種親電分子(化學致癌物和烷化劑)和巰水性分子結合,產生一種硫醚連接的谷胱甘肽結合物,使其更具極性和更易溶于水,經膽汁和尿液排出體外。②通過非酶結合的方式將機體內各種潛在毒性化學物質及致癌劑、親脂性化合物等從體內排出,從而達到清除毒性物質、致癌物質及解毒和保護DNA遺傳物質穩定性的目的。③當GST表達增強或活性增強,GST通過抑制JNKI和ASKI來調節促細胞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通路。該通路通過蛋白質和蛋白質的相互作用,參與細胞生存和死亡的信號傳導,從而使JNKI和ASKI等誘導細胞凋亡的通路被抑制,細胞化療藥物潴留量明顯減少,產生耐藥性[4]。
2 HP感染與胃癌的關系
1982年澳大利亞學者Warren和Marshall從人胃黏膜中培養出HP,并斷定其與胃十二指腸疾病相關。20多年來,研究人員從流行病學、基礎到臨床方面對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豐碩的成果。公認HP是慢性胃炎、消化性潰瘍的重要致病因素,與胃黏膜相關性淋巴組織瘤(MALT)和胃腺癌的發生密切相關[5-6]。流行病學調查顯示,HP感染與胃癌的發生存在顯著相關。HP感染后,胃癌發生率增加4~9倍[7]。HP與胃癌的Meta分析結果顯示,HP與胃癌關系 OR值一般在 2~4之間[8]。
HP確切致病機制尚不明確,慢性胃炎→黏膜萎縮→腸上皮化生→異型增生→胃癌,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腫瘤的發生是由于基因表達異常,細胞內蛋白質合成紊亂,從而導致細胞的生長、分化和調節失控。
3 HP感染與GST表達
在HP致癌機制的過程中,HP感染時胃黏膜上皮氧自由基明顯增多,而氧自由基又與細胞的生長、分化、增殖、轉化等密切相關,故可推測氧自由基直接參與介導了HP所致的胃黏膜上皮細胞惡變的發生和發展。在腫瘤癌變之前,細胞形態和結構并未發生明顯變化,但細胞的功能和代謝酶卻出現異常。研究發現,GST的保護作用表現為通過酶蛋白自身的氧化清除活性氧和自由基[9]。近年來,GST正在成為一種新型腫瘤標志物,并且其與HP和胃癌的關系受到各國學者的關注和重視。
目前對HP與GST的關系研究尚少,慢性胃炎到胃癌的發生的不同階段以GST所代表的人體解毒系統與HP感染關系密切。HP感染影響胃黏膜GST的表達,削弱其對胃黏膜損傷的保護作用,促進胃內致癌物質的形成和致突變作用。但其在胃黏膜中的表達是上調、下調或不表達,國內外學者意見不一致,并且其具體的致病機制尚不明確。
有研究結果表明,HP感染拮抗GST的表達[10]。其機制可能是由于HP感染導致GST基因缺失或其中某種致病因素抑制GST的活性部位的激活有關,從而削弱了GST的保護作用,有利于各種致毒物質對胃黏膜屏障的破壞。Verhulst M.L.等[11]檢測GST在HP(-)無潰瘍性消化不良、HP(+)感染根治后、HP(+)3組胃黏膜標本中的表達情況,提示GST在HP(+)組中的表達顯著低于其他2組。Kim H.S.等[12]通過對211例胃腺癌患者的胃癌組織和癌旁組織與113例正常人胃組織GST活性的研究發現,HP感染在胃癌組織、癌旁組織、正常組織的發生率分別為45%、69%、44%;在HP感染組織中,GST表達較HP(-)組織明顯降低。表明GST活性降低可能由于HP感染有關。國內學者高會斌等[10]的研究也得到同樣的結論。
然而有的學者發現,HP陽性組在腸上皮化生→不典型增生→胃癌發生過程中,GST的表達呈由高到低的動態變化,且明顯高于HP陰性組[9,13]。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腸化黏膜分泌的酸性黏液易于HP的黏著,HP黏著時間越長,對胃黏膜的損害程度越嚴重。同時其產生的氧自由基會刺激GST的大量產生,從而清除這些氧自由基,保護胃黏膜的完整性。而GST在不同胃黏膜組織中由高到低的表達,可以理解為GST的保護功能由部分喪失到完全喪失,無法抵抗HP的致毒作用所致。
GST的遺傳多態性使其在不同人群中的表達不一致。Izzotti A.等[14]在胃黏膜中誘導氧化DNA損傷。HP和宿主基因多態性的相互關系方面的研究中,通過培養和聚合酶鏈反應檢測119例消化不良患者的胃黏膜組織發現,HP攜帶者GSTM1在胃黏膜的表達沒有顯著升高。從而解釋了細菌和宿主基因多態性的相互作用可能使得胃癌只發生在HP感染的部分人群。
4 GST表達與胃癌的關系
HP啟動自由基反應鏈,產生大量活性氧物質,進一步加重胃黏膜屏障的破壞,引起細胞膜及胞內大分子物質的過氧化損傷。同時HP激活胃上皮細胞及固有膜炎癥細胞,導致炎癥介質釋放,使細胞增殖動力加速,遺傳物質的穩定性降低。因此,氧化應激和DNA破壞是胃癌發病中的重要機制。GST作為自身保護酶,能減少氧化應激,清除氧自由基,穩定遺傳物質。其在生物體內的正常表達是胃癌發生的保護因子。Ruzzo A.等[15]通過對126例HP(-)轉移胃癌患者和144例來自意大利胃癌高發區Marche市HP(-)對照樣本的研究發現,GSTP1、GST T1可能與降低轉移型胃癌風險相關。
由于GST酶和基因家族的多態性,其在胃癌發生、發展中的致病機制尚不明確。印度學者Tripathi S.等[16]收集76例胃腫瘤、67例非潰瘍性消化不良、44例消化性潰瘍和100例健康對照組資料,對其GST T1、GSTM1、GSTP1作為致癌-解毒酶的基因分型在胃腫瘤中的作用進行研究,GST T1、GSTM1采用聚合酶鏈反應(PCR),GSTP1采用限制性酶切片段長度多態性(PCR-RFLP)技術,結果發現,GST T1*0基因型在胃腫瘤患者[30/76(40%)]的比例比消化性潰瘍[5/44(11%);P<0.01,OR 5,95%CI=1/4]和健康對照組[23/100(23%);P<0.05,OR 2,95%CI=1/4)]要高。Saadat M.[17]運用Meta分析再次證實了GSTM1*0和GSTT1*0表達上調是胃癌的危險因子。
在胃癌的發生機制中,腫瘤相關基因啟動區的異常甲基化與胃癌關系密切[18]。GSTP1啟動區CpG島的超甲基化是GST基因失活的重要因素,從而使GST的解毒功能減弱,促使胃癌的發生和發展。Hong S.H.等[19]通過分析細胞修復基因(GSTP1)的甲基化水平及胃癌特異甲基化DNA片段(MINI 25)發現,在胃癌組(n=100)GSTP1超甲基化水平相對與健康對照組(n=238)顯著升高(P<0.01),Kim H.C.等[20]在對早期胃癌GSTP1啟動區甲基化的研究中也發現存在超甲基化現象。
GST過度表達與多藥耐藥(MDR)機制有關。多藥耐藥是指腫瘤細胞對某一種化療藥物產生耐藥性后,對其他化學結構及機制不同的化療藥物也產生交叉耐藥性[21]。化療治療在胃癌的綜合治療中占重要地位,多藥耐藥嚴重影響腫瘤患者的化療效果和生存質量,而且導致化療失敗的重要原因是腫瘤細胞對抗癌藥物的耐藥。另外,GST的表達與胃癌的組織學類型有關。在低、中、高分化腺癌中,GST的表達呈梯度上調,并且GST的高表達與胃癌淋巴結轉移有關[22]。說明高中分化腺癌比低分化腺癌、有淋巴結轉移比無淋巴結轉移更易產生耐藥性。腫瘤的組織類型、有無淋巴結轉移是影響胃癌患者預后的重要因素。由于GST能反應腫瘤的這些生物學特性,所以GST可以作為判斷胃癌預后和腫瘤對化療藥物敏感性的重要指標,從而指導臨床制定個性化的化療方案,提高化療效果。
5 展望
人類腫瘤的發生、發展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環境、飲食、遺傳、炎癥介質的釋放及原癌基因的激活、抑癌基因的失活、酶學的變化等。目前對GST家族的研究還處于初步階段,由于GST家族的遺傳多態性和復雜性,其在腫瘤領域的研究還存在爭議,具體的作用機制尚不明確。通過對GST基因家族與腫瘤易感性、特異性的深入研究,可以為腫瘤的治療提供多角度、多層次的全新思路。
[1]Reinemer P,Dirr H W,Ladenstein R,et al.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class pi glutathione-S-transferase in complex with glutathione sulfonate at 2.3 A resolution[J].EMBO J,1991,10(8):1997-2005.
[2]Reinemer P,Dirr H W,Ladenstein R,et al.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of class pi glutathione-S-transferase from human placenta in complex with S-hexy lglutathione at 2.8 A resolution[J].J M ol Biol,1992,227(1):214-226.
[3]Luisa R,Robertaf C.M onobromobimane occupies a distinct xenobiotic substrate site in glutathione-S-transferase π[J].Protein Sci,2003,12(11):2575-2587.
[4]Townsend D M,T ew K D.The role of glutathione-S-transferase in anti-cancer drug resistance[J].Oncogene,2003,22(47):7369-7375.
[5]Simán J H,Engstrand L,Berglund G,et al.Helicobacter pylori and CagA seropositivity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gastric and oesophageal carcinoma[J].Scand J Gastroenterol,2007,42(8):933-940.
[6]M alfertheiner P,Megraud F,O'Morain C,et al.Current concepts in the managemen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the maastrichtⅢ consensus report[J].Gut,2007,56(6):772-781.
[7]黃莉,楊飛.幽門螺旋桿菌感染與胃癌的相關性研究[J].中華綜合臨床醫學雜志,2008(4):49-50.
[8]劉愛民,趙金扣.幽門螺旋桿菌感染與胃癌 Meta分析[J].中國腫瘤,2006,15(9):583-586.
[9]李巖,梁楓,徐進康.GST-π在不同胃黏膜病變中的表達及其與幽門螺旋桿菌感染的關系[J].中華現代醫學與臨床,2005(5):35-37.
[10]高會斌,齊維娟,于永強,等.谷胱甘肽s轉移酶-π在胃黏膜病變組織中的表達及其與幽門螺旋桿菌感染的關系[J].中日友好醫院學報,2008,22(5):273-275,封4.
[11]Verhulst M L,van Oijen A H,Roelofs H M,et al.Antral glutathione concentration and g lutathione-S-transferase activity i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helicobacter pylo ri[J].Dig Dis Sci,2000,45(3):629-632.
[12]Kim H S,Kwack S J,Lee B M.Alteration of cy tochrome P-450 and glutathione-S-transferase activity in no rmal and malignant human stomach[J].J Toxicol Environ Health,2005,68(19):1611-1620.
[13]王旭光,王蘭,袁媛.甲黏膜腸化中π類谷胱甘肽轉移酶的表達及其與幽門螺桿菌感染的相關性[J].中華醫學雜志,2002,82(15):1033-1036.
[14]Izzotti A,de Flo ra S,Cartiglia C,et al.Interplay between Helicobacter pylori and host gene polymorphisms in inducing oxidative DNA damage in the gastric mucosa[J].Carcinogenesis,2007,28(4):892-898.
[15]Ruzzo A,Canestrari E,M altese P,et al.Polymorphisms in genes involved in DNA repair and metabolism of xenobiotics in individual susceptibility to sporadic diffuse gastric cancer[J].Clin Chem Lab Med,2007,45(7):822-828.
[16]Tripathi S,Ghoshal U,Ghoshal U C,et al.Gastric carcinogenesis:possible role of polymorphisms of GST M1,GSTT1,and GSTP1 genes[J].Scand J Gastroenterol,2008,43(4):431-439.
[17]Saadat M.Genetic polymorphisms of glutathione-S-transferase T1(GST T1)and susceptibility to gastric cancer:a meta-analysis[J].Cancer Sci,2006,97(6):505-509.
[18]Poplawski T,T omaszewska K,Galicki M,et al.Promoter methylation of cancer-related genes in gastric carcinoma[J].Exp Oncol,2008,30(2):112-116.
[19]Hong S H,Kim H G,Chung W B,et al.DNA hypermethy lation of tumo r-related genes in gastric carcinoma[J].J Korean Med Sci,2005,20(2):236-241.
[20]Kim H C,Kim J C,Roh S A,et al.Aberrant CpG island methylation in early-onset sporadic gastric carcinoma[J].J Cancer Res Clin Oncol,2005,131(11):733-740.
[21]Berger D,Citarella R,Dutia M,et al.Novel multidrug resistance reversal agents[J].J Med Chem,1999,42(12):2145-2161.
[22]李秋元,祝森志,陳素鉆,等.C-erbB-2及GST-π基因在汕頭地區胃癌患者中的表達特點[J].廣東醫學,2006,27(6):882-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