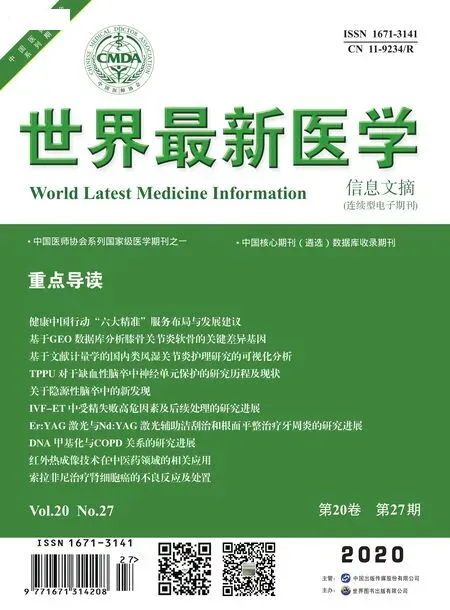淺談可能與雙磷酸鹽藥物相關(guān)的非典型股骨骨折髓內(nèi)釘治療體會1 例
吳治森,鄭臣校
(中山市中醫(yī)院,廣東 中山)
1 病例資料
患者,女性,57歲,因右大腿近端隱隱疼痛3個月,加重1天前來就診。患者3個月前無明顯誘因出現(xiàn)右大腿近端隱隱作痛,臥床休息后疼痛可緩解,未予特別重視,1天前因走路時步伐稍微加快突然出現(xiàn)右大腿近端劇烈疼痛,伴活動受限,不能繼續(xù)行走,遂由120送來我院就診。急診行X線檢查提示:右股骨近端骨折,骨折端明顯移位(圖1)。為進(jìn)一步治療收住院。患者既往有骨質(zhì)疏松癥病史5余年,并且近5年左右一直服用阿侖膦酸鈉抗骨質(zhì)疏松治療,無其他慢性疾病。

圖 1 術(shù)前 X 線
根據(jù)患者病史、癥狀及體征,結(jié)合影像學(xué)檢查(X線片可見骨折端明顯移位,外側(cè)骨皮質(zhì)呈鳥嘴樣增厚,內(nèi)側(cè)骨皮質(zhì)尖銳突起,呈尖刺征。),診斷為右股骨非典型骨折(atypical femoral fracture,AFF),考慮可能與長期服用雙磷酸鹽類藥物有關(guān)。入院后即告知患者停止服用阿侖膦酸鈉,給予適當(dāng)補(bǔ)充鈣劑及維生素D。積極完善術(shù)前檢查,排除手術(shù)禁忌癥,于入院48小時內(nèi)行微創(chuàng)復(fù)位髓內(nèi)釘內(nèi)固定術(shù)治療。
手術(shù)操作步驟及簡要技巧如下:在腰硬聯(lián)合麻醉后,患者平臥于牽引床,行牽引下配合旋轉(zhuǎn)復(fù)位,復(fù)位后透視見位置欠佳,予維持牽引,常規(guī)消毒鋪無菌巾,取與骨折端平齊部位外側(cè)小切口,長約1.5cm,插入骨膜剝離子,置于骨折近端前側(cè)按壓復(fù)位,遠(yuǎn)骨折端插入一枚4mm克氏針推擠幫助復(fù)位,透視見骨折端對位對線良好(圖2),維持復(fù)位下,適當(dāng)內(nèi)收患肢,再以右髂前上棘向后垂直于地面的直線與股骨大轉(zhuǎn)子和股骨干長軸向近端的延長線交點(diǎn)為中心設(shè)計切口,長約2.5cm,切開皮膚、皮下組織,切開闊筋膜,觸摸大轉(zhuǎn)子頂點(diǎn),于大轉(zhuǎn)子頂點(diǎn)稍內(nèi)側(cè)為進(jìn)釘點(diǎn),方向朝向股骨髓腔,插入導(dǎo)針(圖2),套筒保護(hù)下擴(kuò)髓,徒手插入主釘,透視主釘位置滿意后,使用導(dǎo)向套筒打入頭釘導(dǎo)針,測深后擰入近端鎖釘,松開牽引后再使用導(dǎo)向器鎖定遠(yuǎn)端螺釘,最后置入尾帽。術(shù)后拍片結(jié)果顯示復(fù)位固定滿意(圖3)。
2 討論

圖2 術(shù)中輔助復(fù)位并插入導(dǎo)針

圖 3 術(shù)后 X 線
雙磷酸鹽類藥物(bisphosphonates,BPs)相關(guān)的非典型骨折發(fā)生率較低,病例較少,該藥物自20世紀(jì)70年代應(yīng)用于臨床以來,目前已成為治療骨質(zhì)疏松癥的一線藥物,尤其是在預(yù)防骨質(zhì)疏松性骨折方面有著較好的臨床療效。但近年來,隨著大家對該藥物與非典型骨折的逐漸重視,關(guān)于該藥物是否與非典型骨折有直接關(guān)系的研究越來越多,雖然不能明確其之間一定有直接關(guān)系,但基本大多數(shù)學(xué)者都認(rèn)為兩者之間有著某種相關(guān)性。2005 年,Odvina[1]首次報導(dǎo)了與雙膦酸鹽類藥物相關(guān)的非典型股骨骨折,他發(fā)現(xiàn)長期口服阿侖膦酸鈉的患者在無明顯外傷誘因下出現(xiàn)自發(fā)性非典型骨折,且術(shù)后骨折延遲愈合甚至不愈合。2011 年瑞典大規(guī)模臨床流行病學(xué)調(diào)查數(shù)據(jù)顯示[2],人群中應(yīng)用雙膦酸鹽類藥物致非典型股骨骨折的發(fā)生率約為0.05%。以前的認(rèn)識是雙膦酸鹽類藥物能明顯抑制破骨細(xì)胞活性,減少破骨細(xì)胞引導(dǎo)的骨吸收,從而減少骨質(zhì)疏松造成的骨折。但目前有學(xué)者通過動物實(shí)驗發(fā)現(xiàn),骨吸收受到抑制時骨重建也會降低,這樣骨的微損傷很難愈合,從而骨皮質(zhì)韌性逐漸減退,長期使用會影響骨的新陳代謝,骨脆性增加,最終導(dǎo)致應(yīng)力性骨折[3]。AFF 獨(dú)特的病理生理學(xué)特征是前驅(qū)疼痛、雙側(cè)骨皮質(zhì)受累、骨皮質(zhì)增厚、骨折延遲愈合[4],該病例符合前四個特征,而最后一個特征需等隨訪結(jié)果證實(shí)。
非典型股骨骨折是一類特殊的骨折類型,特別是這種與長期服用雙磷酸鹽相關(guān)的非典型骨折,其不同于骨質(zhì)疏松及單純外傷引起的骨折,如果不積極行外科干預(yù),保守治療很難愈合[5]。據(jù)筆者了解,目前的主流觀點(diǎn)仍是髓內(nèi)釘治療,它屬于應(yīng)力分享式固定,其中包括骨折后的髓內(nèi)釘治療以及不全骨折的預(yù)防性髓內(nèi)釘治療,這可能是因為髓內(nèi)固定比較符合長管狀骨骨折愈合的生物力學(xué)要求,后期如果出現(xiàn)骨延遲愈合,還可以考慮行動力化治療。在此不推薦保守治療,其一是因為保守治療時間長,后期并發(fā)癥較多;其二是因為保守治療后發(fā)生骨不連的幾率較高[6]。不過根據(jù)筆者經(jīng)驗,手術(shù)治療后的患者,給予服用活血散瘀、補(bǔ)益肝腎、續(xù)筋接骨類的中藥湯劑,可以明顯提高臨床愈合率。美國骨與礦物質(zhì)研究學(xué)會認(rèn)為,非典型骨折患者應(yīng)立即停用雙膦酸鹽藥物,行手術(shù)干預(yù),并予以適當(dāng)劑量的維生素D、鈣劑、及特立帕肽治療[7]。與此同時,還應(yīng)評估對側(cè)股骨情況,若為不全骨折,可行預(yù)防性髓內(nèi)釘治療或者部分負(fù)重,同時給予特立帕肽治療;若對側(cè)股骨正常,則定期行骨掃描或核磁共振檢查,隨訪觀察治療。
與雙磷酸鹽相關(guān)的非典型股骨骨折多為個案報道,且基本都是回顧性研究,缺乏前瞻性研究,雖然近年來這種病例越來越受到臨床醫(yī)生的關(guān)注,但對于不全或者無癥狀的非典型股骨骨折是否應(yīng)用髓內(nèi)釘行預(yù)防性治療的臨床報道和研究較少;此外,對于如何更好的權(quán)衡和把握在預(yù)防和治療骨質(zhì)疏松的同時防止出現(xiàn)非典型骨折,也是今后需要更進(jìn)一步研究的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