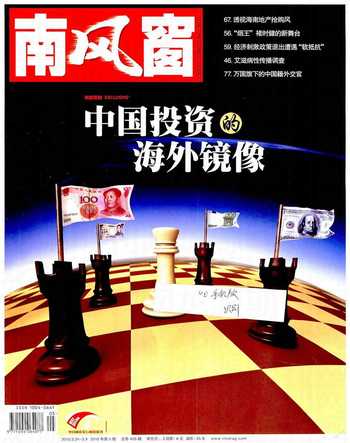人民幣升值倒逼外匯管制改革
林亞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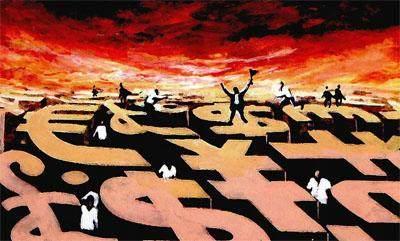
人民幣匯率穩定一定是以犧牲人民幣的購買力為代價的。通貨膨脹預期從年初開始就呈現加速態勢,很可能在下半年就轉變為嚴重現實。
央行1月29日發布的《2009年四季度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報告》稱,2010年,中國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繼續執行2008年末啟動的4萬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然而從近期央行的一系列政策操作來看,貨幣政策趨緊的態勢是比較明顯的,也引發資本市場的大幅波動。
“盡管2010年中國貨幣政策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為適度寬松。但這個度具體到底是多少,人們一直稀里糊涂。而且是適度還是寬松,是可以隨時隨勢靈活解釋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魏加寧研究員表示,央行再次強調政策寬松基調,是真的適度寬松,還是明松暗緊,就很耐人尋味。值得注意的是,在央行發布《報告》之前,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出席達沃斯經濟年會時重申了2010年中央“雙寬”的政策基調。
其實,在央行年度工作會議結束后,央行都沒有設定調控目標和貨幣供應增速,這無疑體現了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靈活性和政策執行中的機會主義路線。
人民幣匯率困局
中國政府在制定人民幣匯率政策時面臨的困境一直都存在:中國龐大的貿易順差要求人民幣升值,但一旦有政府允許人民幣升值的任何風吹草動,都將可能導致大規模的資金流入。
數據也支撐熱錢對于復蘇中的中國市場的偏愛。1月15日,央行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09年全年新增外匯儲備4531億美元,同比多增353億美元,外匯儲備余額近2,4萬億美元,同比增長23,28%:不過,去年12月份104億美元新增外匯儲備數字要遠低于9月份高達617億美元的增幅。外匯占款增勢兇猛,自2009年三季度以來熱錢涌入的態勢明確。
不可否認,國內有部分專家對于熱錢流人大陸導致境內流動性泛濫的現象,還有所爭議。他們的依據是中國資本賬戶還處于管制狀態。“這類觀點不值得一駁,可以看看香港,實際上受制于中國資本管制政策,香港地區已經成為國際熱錢套利中國經濟的橋頭堡。”中央財經大學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自2008年10月至今,流入港元的國際流動資金已經超過6400億元,金額之高前所未有。根據摩根士丹利的資料,截至去年11月香港銀行的貸存比率下降至只有51%,是區內最低的地方,反映銀行的“水浸”情況嚴重。在聯系匯率機制下,香港無法阻止資金流入。
2006年至2007年兩年期間,中國流動性泛濫的根源,就在于外匯占款急劇膨脹,央行不是發票子,而是使勁地收票子,一旦手腳不夠麻利,市場面的閑錢立即泛濫成災。盡管由于嚴格的資本管制政策,中國熱錢滾滾的局面出現的時間,可能晚于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但由于歐美國家寬松貨幣政策和人民幣匯率嚴重低估兩個因素存在,魏加寧預計,“流動性泛濫在中國是早晚的事情,根據2009年12月份各項指標的異常,可以推測出今年下半年,外匯占款可能再次成為流動性泛濫的根源。”
“央行若要在上半年加息,將面臨著很大的制時,目前人民幣事實上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是央行所面臨的最大困難。”郭田勇解釋,根據蒙代爾的“不可能三角”理論,在資本跨境進出無法得到有效控制的情況下,如果央行加息,國外熱錢就會因為較高的利率而大舉流入中國,這反而會使得貨幣流動性進一步寬松,從而給加息的成效帶來沖擊。“也就是說,在美聯儲上半年很可能將繼續保持低利率水平的情況下,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已近似成為央行加息的前提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加息預期逐漸濃厚,美元匯率反彈將會使得部分資金回流美國,從而廣泛影響大宗商品和新興國家資本市場的走勢——這種影響其實已經在今年1月份的國際市場運行中初步顯現,表現為大宗商品和新興股市的下跌。“美國貨幣政策的逐步正常化將使得中國的貨幣政策擁有更大的操作空間。”郭田勇表示,人民幣升值幅度,實際上是中國政府和其他國家的政治博弈結果,但就升值幅度空間本身進行討論,其實是謀一時,而非謀一世。無論市場還是政府,都應該從戰略高度看待目前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問題,要考慮如何逐步過渡到市場浮動匯率機制。
從全球來看,各國都確認了經濟在“逐漸正常化”。而在過去兩年的全球衰退期間,新興經濟體表現出了很強的韌性,業內人士認為,在現階段,各國央行還沒有很快轉入貨幣緊縮的意向。這對于人民幣是絕好的戰略窗口期。
全國社保基金會理事長戴相龍1月9日在中國資本市場論壇上表示,現在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利時機。由中國政府及中央銀行和有關國家的政府及中央銀行通過特定安排,擴大人民幣在境外使用。戴相龍為此提出了具體措施:一是實行雙邊本幣限量兌換。把一部分貨幣互換改為一次性賣出人民幣,買進至少在經常項目上可兌換的外國貨幣,解除因人民幣升值將來更多歸還人民幣的擔憂。二是以人民幣支付我國對有關國家及地區的貿易逆差。這些國家及地區可用人民幣購買中國商品和勞務,也可以用于對中國的投資,也可以兌換為其他國際儲備貨幣。
多選的政策導向
然而,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始終不能夠獨立,1995年以來,央行一直實施著《中國人民銀行法》所規定的“單一”貨幣政策目標: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去年12月底,周小川在公開場合表態央行貨幣政策的多目標制,但這次央行工作會議新聞稿的通告,算是正式公告官方貨幣政策目標的轉變。這意味著,中國央行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將容忍一定的溫和通脹,以確保經濟回暖態勢得以持續,同時防止溫和通脹急劇演變成為惡性通脹,并根據全球金融市場的情況相機決策。不搞信貸額度,是因為通脹已經抬頭,但還沒有失控的威脅,犯不著讓市場人心惶惶。多目標制,實際上是悄然放棄過去的幣值穩定的原則。
現實經濟中,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并沒有太大的決策自主空間。一方面,目前人民幣盯住美元匯率的情況,使得央行的利率調控在很大程度上要跟隨美聯儲的步伐,意味著央行貨幣政策已喪失了部分獨立性。另一方面,中國的央行同樣肩負著“保增長”的任務——這一點周小川并不諱言,表示經濟增長、保持較高就業都是中國貨幣政策運行的目標。不過在很多時候,“保增長”會讓央行的貨幣政策對通脹的醞釀采取姑息政策。
郭田勇表示,市場普遍預期今年銀行業新增信貸為7N8萬億,一季度可能再創出4萬億規模。還有消息稱,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將今年信貸規模大致框定在7.5萬億元。倘若真是如此,這將使2010年國內信貸的寬松程度與去年大有一拼,因為2009年中長期貸款與固定資產投資中約有2萬億元的信貸資金將回流至今年,這對高通脹風險的助推是顯而易見的。
這一點,中國經濟決策者當然刻骨銘心:上個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動蕩,就因惡性通脹而起。這也是為何2007年底中國經濟決策者毫不猶豫搞“雙防”,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初現端倪時,仍是緊縮貨幣不放松。
“在高通脹和緊縮之間如何選擇,學術界對此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利益集團的博弈和政治需求等諸多要素,不可避免要干擾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郭田勇感慨,如果人民幣匯率長期扭曲,那么,毫無疑問會造成中國和全球經濟資源的嚴重錯誤配置,最后帶來很多麻煩。長期以來,經濟學界熱議的全球經濟失衡,就在于此。
在去年12月,中國月度出口規模達到了歷史第四高位,而月度進口規模更是創造了歷史新高,這已經清楚地表明中國外貿的復蘇趨勢已經確立。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為了回應美歐日和出口型國家對人民幣匯率的指責和壓力,而選擇適當的方式來升值人民幣,并能夠緩解境外投資者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如使人民幣真正盯住一籃子貨幣,并形成雙向波動的管理匯率制度,這樣就能夠有效地緩解因央行升息而帶來的熱錢大幅涌入。
吊詭的是,中國金融系統能夠在1998年和2008年兩次全球性金融危機中獨善其身,基本就靠這個資本管制防火墻。一旦防火墻拆除,下次出現滔天巨浪,中國金融系統和決策層對此做好準備了嗎?“人民幣自由兌換和浮動匯率,看似一道政策就解決的事情,背后其實牽扯到諸多市場建設和利弊得失的取舍。這不僅考驗決策層的智慧,也看中國金融系統的發展步伐。”魏加寧認為這是個死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