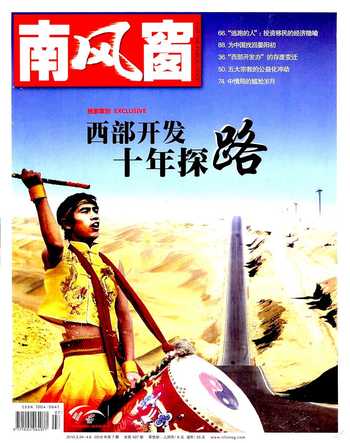中世紀:割裂的“黑暗”
彭 強
真實的歷史一定是延續的歷史,割裂的歷史一定是意識形態的產物。就如我們把新中國和舊中國全然割裂,結果胡適之、錢穆這樣的文化人就從我們的歷史中消失了,以致近年我們還在補課。對西方歷史的認識也一樣,今天大多數人說起中世紀都是“黑暗的”,的確,天主教的政教合一、高度人身依附關系的領主依附制度,都與現代觀念相悖,但對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一面倒的認識也讓我們從歷史的真實中失重了。
“邏輯不是萬能的,沒有邏輯卻是萬萬不能的。”說這話的是6世紀的哲學家波愛修斯,他在獄中寫的《哲學的慰藉》與哈維爾和朋霍費爾的《獄中書簡》并稱為人類文明三大獄中書簡,里面探討的苦難問題,上帝的公義問題直到今天仍然震撼著人們的心靈,被認為是“最后一部堪稱經典的西方著作,是西歐全部文化精髓的來源”。國內有關波愛修斯的著作微乎其微,本書中文版的問世或可補缺。
“淑女的言行舉止,無一不體現出她的節制,她儀表莊重,既不表現得太過莊重,也不會涂抹香水太過招搖。”“可憐的女人,你的眼睛是瞎的,看不到自己處境的危險。因為虛假的榮耀環繞你,你的驕傲使你的心昏昧,你把自己當作了女神。哦,這愚蠢的驕傲!你怎能容忍它在你里面生長?”像不像當代的禮儀大師、心理專家?這來自14世紀法國女作家,也是歐洲第一位專職女作家皮桑的名著《淑女的美德》。這本書被譽為奠定西方淑女觀念的經典,她充滿睿智地勸誡女性:怎樣保持內心寧靜,如何在婚外戀誘惑面前用理性謹慎行事,如何避免嫉妒與毀謗而堅守品格的純正。
這只是我們重新認識中世紀的兩個例子。從文化來說,沒有中世紀后期“自然神學”的確立,歐洲不可能走出柏拉圖式的唯心主義,不可能孕育出現代科學,整個歐洲不可能發展出普遍主義精神。而眾所周知,普遍主義是現代化的根本特點,否則今天談普世價值就沒有任何學理上的合法性。沒有中世紀的教會法體系,也不可能有后來歐洲的司法體系和法律為王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