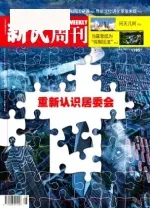房產稅是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張靜
“窮人以為富人將多納稅,歡欣鼓舞。但如果相關配套不成熟、改革不到位,房產稅最終剪掉的,反而是中產階層的‘羊毛。”
中國古代神話中的神仙一般都不食人間煙火,居高臨下為凡人指點迷津。在奧林匹斯的山頭上,諸神卻與凡人一樣充滿了七情六欲,經常卷入是是非非。
近來中國房產稅是否擴征的爭議,就上演了一幕“西風東漸”。
4月底,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表示:“目前是推出房產稅的可操作時機”。5月17日,發改委產業研究所所長助理黃漢權突發驚人之言,被標題黨以“發改委表態3年內房產稅免談”加以傳播,一時間占據各大網絡頭條,引發了人們的強烈詰問:“史上最嚴厲”的樓市調控政策戛然而止?房地產“綁架”中國經濟的預言再度靈驗?房價將迎來新一輪瘋長?當天下午,發改委火速辟謠:“研究人員所發表的意見不代表發展改革委的立場。”有關房產稅的言論“內容嚴重失實,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影響”。整個過程,渾似小沈陽的經典段子:這個沒有。這個可以有。
神仙一打架,凡人便遭殃。股市中的房地產板塊今天躍上漲停板,明天又被重新打入“十八層地獄”;害得大盤的臉色一會兒飄紅,一會兒飄綠。張悟本一不小心成了“豆托”,極具娛樂精神的發改委也惹上了給機構當槍使的嫌疑,頭腦一熱殺進去抄底的小散們又被洗劫了一回。
就在投資者被各色各樣的傳言搞出了“審美疲勞”之時,房產稅卻漸行漸近。5月31日,國務院同意發改委《關于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逐步推進房產稅改革。另據《上海證券報》報道,上海有可能成為首個對部分家庭住宅征收房產稅的城市,有關方案已上報國務院。
“借殼”開征,玄機何在
物業稅一詞最早進入公眾視線是在2003年10月,至今“空轉”的省市已經超過10個。一直聽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繞不開一個法理上的障礙:在我國,土地屬于國有。物業稅是財產稅,而我們住房只有70年的使用權,何以對使用權征收財產稅?
中國有句古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但繼物業稅曝出的“房產保有稅”,便將課征對象僅指向土地之上的房屋部分。
該“創意”實施起來也不輕松。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恒指出:“住房保有稅與物業稅是一樣的,均為房產持有環節的稅種,需要國務院通過、人大立法,由中央統一開征。”
天無絕人之路。早前已有人士敏銳地發現:為了掃除法律上的障礙,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財政部提交并獲得通過的預算報告中,物業稅“借殼”房產稅已露端倪。
房產稅從1986年就開征了,作為地方稅種,可以由地方政府自行制定,報財政部備案就可以了。
雖說“86版”早有明文規定:非營業用房,也就是自住的房子不交房產稅。但據媒體報道,眼下財稅部門儼然傾向于將第三套房以及三套以上的住房定性為經營性住房,納入房產稅征稅范圍。
如此“解釋”,聽起來總有點“指鹿為馬”的意思。為了開征房產稅,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資深業內專家楊少鋒認為,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需要藉此來抑制高房價。
無論中外,凡是想對民眾多收稅的政策,幾乎都會遭到反對。但此次房產稅改革似乎有點“順應民意”,千呼萬喚始出來。究其原因,不外乎房產稅儼然已被當作政府是否有誠意擊潰高房價的試金石和最后撒手锏。發改委之所以措辭嚴厲急忙辟謠,正是洞悉了中央調控的決心。
然而征收房產稅的初衷,并不是為了抑制房價。正如最初提出物業稅的2003年,房價并不高。
一直以來,地方政府熱衷于“賣地”,高度依賴“土地財政”來支付公共品開支。但這種賣地財政體制,已經越來越難以為繼。“城市的規模不能無限的擴張,這是個大趨勢。地方政府把土地都賣完了,收入從哪里來?”經濟學家華生說。
正如全國政協委員梁季陽所言:“分稅制成高房價的幕后推手。”不久前新華社炮轟房地產市場的“六連評”也抨擊道:“瘋狂拿地、推高地價房價的背后,總能看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影子。”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央政府通過改革房產稅,實際為地方政府擴大了稅源,避免GDP變成“刮地皮”,似乎是從根本上解決高房價之道。
然而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輯劉杉指出:“政府此次改革房產稅,巧妙借助了群眾對高房價的不滿。一直受人詬病的‘土地財政問題源于中央與地方的稅收分配比例失衡,此番改革房產稅意在增加地方財力,但并沒有從中央地方收入分配比例著手,而是通過擴大征稅范圍,增加了居民負擔。所以,從公共決策角度看,房產稅改革實際會損害納稅人的利益。”
誠如某報社論所言:政府要辦的“好事”太多,這些事都要通過收稅才能辦好的話,人們的稅負只會越來越重。
“很多官員似乎把‘房產稅當作救命稻草,期待它能解決樓市的一切問題。實際上解決中國住房問題的核心矛盾,只能通過增加供給來解決,讓房地產走向有限市場化。該市場化的完全放開,政府用一個杠桿調節,把大部分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解決中低收入者的居住問題。”楊少鋒說。
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曾明確提出:“開征統一規范的物業稅,相應取消相關稅費”。但在房產稅開征的諸多傳聞中,不知為何,“取消相關賦稅”似乎成了一個被遺忘的角落。
中產:為什么受傷的總是我?
“房產稅現在的狀態是有影響的人紛紛表示沒影響,無影響的人紛紛表示有影響。”該經典語錄的背后折射出兩大涇渭分明的對峙陣營:富人與窮人。一位評論人士認為:“窮人以為富人將多納稅,歡欣鼓舞。但如果相關配套不成熟、改革不到位,房產稅最終剪掉的,反而是中產階層的‘羊毛。”
“我并不是炒房客。”家住北京天通苑的一位業主備覺委屈。在外人看來,這是一位人人羨慕的中產,在一家著名的互聯網公司擔任中層管理者,擁有三套住房,一套在市中心,新買的住房面積高達170平方米。
但他告訴記者:“我和所有的打工族一樣,當初買房的時候囊中羞澀只能選擇偏遠的五環外。等兒子出生,我才意識到一個大問題,郊區沒有好的小學和中學。為了孩子,只好在市中心又買了一套小房子。這就有了第二套房。岳父母的到來讓我們的小家越發擁擠,只好把目前這套房給他們住,我們又去買了第三套房。我只是通過自己的能力,讓一家人生活得更好一點,為什么就成了打擊的目標?”
他說自己之所以買了這么多房子,還有一個比較樸素的想法是抵御通脹。“錢越來越不值錢,我不懂其他的理財方式,身邊人都說買房可以保值增值,我也隨大流。實際上在北京,像我這種情況的中產不在少數。我看起來生活得還不錯,但上面有4位老人,還要養老婆孩子。如果我,或者家人有誰生場大病,生活壓力就會非常大,很有可能因病致貧。”
“政府一開始鼓勵我們買房,并沒有告訴我們,將來要開征房產稅。如果我一早就知道,至少在買第三套房時,我會比較慎重。”
楊少鋒認為北京的空置率并沒有當初易憲容教授騎自行車夜探居民區測算出來的那么“邪乎”。他自住的小區,剛搬進去的時候只有30%的入住率,現在入住已經達到了80%。
“稍有差池,就會造成巨大的社會不公。”時評人士童大煥說。
“房產稅確定稅基時,一樣會遭遇到跟物業稅一樣繞不過去的坎兒。不刨除土地價值有重復征稅的嫌疑,刨除了對房價的影響微乎其微,因為地價上漲才是房價上漲的大頭。”一位無房者告訴記者:“我也希望房價降下來,但我更希望維護一個程序上的正當性。”
稅務人員也撓頭。“如果一個溫州人在上海、杭州都投資有多套房,是不是我們要每年去溫州找他收稅?如何收?上海的房子收稅,杭州的房子不收稅?”
怎么保證房主每年主動去稅務機關繳稅呢?據說上海的方案是會走自行申報的方式,如有超期限瞞報漏報,在未來的交易環節上審查出來,除了補足稅款,還會給予相應罰金。
但正如萬達董事長王健林在兩會上所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增加的稅賦最終都將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人們擔心,最終為房產稅埋單的,會不會是購房人與房客?
“如果收房產稅,我肯定會漲房租。”采訪中,幾乎所有的房東都這么篤定地告訴記者。
與一年前相比,房價還在死扛,租房者卻開始體會郁悶。據某地產市場研究部統計,5月份北京租賃市場平均租賃增加20%,相當于租金整體上漲接近500元。約有30%左右的房客不得不因此選擇偏遠的地區,或者搬去更差的住房。而5月以來,天津、大連、沈陽等城市的房租漲幅也超過了10%。
今年1月至4月,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069元,月均可支配收入為2500元左右。而人均租金負擔已達每月1000元,這意味著房租占收入的比重已接近40%。
“這些年工資從沒見漲,衣食住行都漲價。如果征收房產稅之后再漲租金,我也不得不搬到郊區去住了。”一位房客無奈道。
另據上海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網站的數據,以上海目前的存量房面積,一共1351名評估師大約需要28年才能完成評估,還不包括期間新增房屋面積。除此之外,全國房產交易信息并未聯網。
一則新的傳說似乎讓人暫時松了口氣:只對增量房屋征收,且以每戶家庭名下一定房產面積為“起征點”。但楊少鋒不解道:“如果我原本有10套房,不征房產稅。但我新買了一套,達到3套房的標準,便要征,這似乎說不過去。”
“正因為這么多細節還都沒有公布,所以現在談房產稅究竟會產生多大影響力沒有意義。即使上海率先開征,也只是試點,政策真正落到實處需要很長時間。”楊少鋒說。他認為這么一個關乎到千家萬戶的政策,應該召開聽證,才能保證大多數人的公平和利益。
樓市新政出臺已經有一段時間,可預期中的樓市拐點并未到來。若再次陷入“越調越漲”的怪圈,無疑將是對政府公信力與民眾信心的考驗。在此背景下,逐步推進房產稅改革,更像是一個針對高房價的權宜之計:隱而未發,已足夠震懾。
滅頂之災?
早在“3年內房產稅免談”消息甫出,潘石屹便在微博上說:“猶如瀕臨淹死的人看到海面上漂來一塊木頭。但還是不要樂觀,要做好最壞的打算。”
老潘還舉了日本為例:“日本征收房產稅后,房地產立刻垮了下去,20年的時間內都沒有再起來,經濟也一路下滑。”陽光100集團市場部總監王智中,3月份便賣出了多余的房產,只留一套自住。他認為兩會之后的“三個地王”,給了政策制定者一個耳光,宣告第一輪調控已經失敗。“樓市有多瘋狂,政策就有多瘋狂。對于最新的國務院10號文,我認為根本不值得驚訝,只要調控沒有達到目標,11、12號文件就會出臺,那就是‘房產稅。”
房產稅被認為是高懸在房價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就在5月31日當天,資本市場做出了劇烈反應,地產板塊午后大幅跳水,上證綜合指數也跌破了2600點大關迎來了“二次探底”。
上海市房產稅實施細則,有說按契證上的購房金額為基數進行征收,還有一說是以評估后的房價為基數。
在華生看來,那些資金充裕的炒房大鱷,真正在乎的是一買一賣的差價,百分之幾的稅負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中經聯秘書長陳云峰也認為:“一個中介在一個二手房的轉賣過程中,營業稅加契稅、中介稅,可以達到11%。這個都沒有能夠阻擋高房價的增長,希望通過房產稅調控高房價,不是很現實”。
但楊少鋒認為:“像前年和去年那樣的大跌大漲是不多見的。我認識的溫州炒房客,以租養房的很多,一般都會持有3年再出手。”
以一套100萬元的房子為例,每年8%的房產稅,就意味著每月多支出666元。再加上月供,如果超過租金收入,再加上房價下行的預期,這部分業主可能就會選擇將房子脫手,對房價短期產生比較大的影響。
從中長期效果來看,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朱青對房產稅的效果潑了盆冷水。“2007年5月30日,我國將股票交易印花稅從千分之一調整到千分之三,對股市影響是當天980種股票跌停。但是到了2007年的10月16日,股市還是由4100點猛漲到6124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