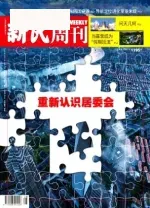首爾G20:又一場空談?
邵樂韻
一年前的G20匹茲堡峰會,各國首腦爭先恐后地討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歡心。但在此次首爾峰會上,誰也不想幫助奧巴馬消除憂愁。
美國經濟史學家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曾說過:“國際協同是應對經濟大蕭條的最后努力。”2年前,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G20的風頭蓋過G8俱樂部,成為實現全球經濟合作的新模式。
如今雖然危機高峰已過,經濟失衡、匯率政策、財政赤字等問題仍然棘手。外界希冀G20能促成進一步的國際協調,避免全球經濟再次陷入更深的泥潭。然而剛剛在韓國首爾閉幕的第五次G20首腦峰會卻顯得乏善可陳,兩天會議下來,成員國之間的意見分歧并不見得彌合多少,《首爾宣言》在實質問題上也是點到即止。
埃森格林對這場后危機時代的會議評論得很直白:“一個完全、徹底的失敗。”其實倒也不用太悲觀,正如《時代》周刊所言,在目前問題重重的環境下,這場被大肆宣傳的國際會晤即使失敗也不意味著世界末日來臨,回頭看看大蕭條,再比較一下今天,似乎還不那么糟糕。
沒有突破,也沒談崩
G20首爾峰會上,對于匯率和貿易摩擦的焦慮主導著會場情緒。會場外,大家都在觀望,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會不會引發匯率大戰,全球性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會不會反彈……在峰會開始前,大家就做好了心理準備:不能抱太大希望。美國依舊發揮了在國際事務中設置議題的能力,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呼吁二十國集團為政府經常項目收支設置量化上限(控制在占GDP比重4%以內),解決全球貿易失衡。但是中國、德國、巴西等國家對美聯儲施行量化寬松政策、自貶美元來刺激美國國內經濟的做法顯然感到相當不滿,在這次G20峰會之前,美聯儲的瘋狂印鈔行為已遭到了不少國家的炮轟。
在首爾峰會上,中美國家領導人之間的隔空喊話成為受人關注的橋段。美國將巨大貿易赤字部分歸咎于中國人民幣幣值過低。奧巴馬在記者招待會上指責中國使用大量金錢維持幣值偏低,擁有大量貿易順差的國家必須改變“對出口的不健康依賴”,匯率“必須反映經濟的現實情況”。美國希望中國在胡錦濤主席明年1月訪美前能讓人民幣升值更多。
胡錦濤主席則呼吁“主要儲備貨幣發行經濟體”應該實施負責任的政策,保持匯率相對穩定。外界解讀,胡錦濤講話中沒有掩飾對美國的批評之意。自從6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經升值3%,目前中國外匯儲蓄達到2.65萬億美元。瑞士聯合銀行集團(UBS)全球經濟研究部主任唐納文(Paul Donovan)說,美國的壓力并不太可能加快人民幣的升值。
美國斯坦利基金會項目官員大衛?肖(David Shorr)說:“在首爾峰會上,圍繞貨幣、赤字、出口等問題的分歧太多,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很難有什么重大突破。”首爾峰會一度陷入僵局,呈現多邊外交角力,但最終“倒也沒有出現談崩的局面”。
峰會在不加掩飾的爭辯中開場,最后卻草草收場。為勾勒出各方都能接受的匯率政策和經濟再平衡“路線圖”,二十國首腦一直討論到11月12日的凌晨3點(距《首爾宣言》發布僅幾個小時)。長達22頁紙的聯合宣言中充滿了高技術含量的用詞,四平八穩的闡述表明,這只能是各方達成的最低程度的共識。
《首爾宣言》表示,與會各方承諾,匯率應反映各國經濟基本面,避免競爭性貨幣貶值。發達經濟體將嚴防匯率過度波動以及失序走勢,并在中期內尋求不傷害經濟的財政整固措施,發展中國家將增加匯率政策彈性。同時,G20支持全面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可給予新興經濟體更大發言權。
最后,峰會東道主、韓國總統李明博宣布,全球性“貨幣戰爭”不存在,并預計,在G20就“努力建立由市場決定的匯率體系”達成一致后,全球匯率將趨于穩定。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認為,聯合公報能就控制經濟失衡達成一致意見,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因為就在兩年前,一些國家連提都不愿提。
但對于如何限制經濟失衡,此次峰會沒有給出具體的目標,界定工作甚至被推遲到明年:G20財長們將在2011年“制定一套旨在衡量經濟失衡和確定相應行動的指示性準則”,IMF將協助評估各國經濟失衡狀況。
分析人士認為,公報模糊了多處分歧,將疑問留給了未來。正如一名美國高級官員所說的,既然現在我們討論的是經濟問題,就必須要有明確的數字,這樣大家才能心里有數。IMF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比喻:“接下來我們得等著看,半年后,一年后或者兩年后我們能不能圍繞著骨頭填充點肉進去。”
除了擔心“議而不決”,G20的另一個問題是,它不是一個正式的國際組織,沒有執行機制——若“決而不行,行而不果”,豈不是又一場空談?
《愛爾蘭時報》評論,G20峰會雖然淡化了貨幣問題,但是“貨幣戰爭”的陰霾并未消去。
在參加完G20峰會后,部分國家首腦又參加了在日本橫濱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也制定了發展戰略,同樣沒有具體的規定和實質性的措施。
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研究外交關系的教授村田晃嗣(Koji Murata)認為APEC峰會熱度不及G20,結果也很模糊,缺乏實質性。金融服務公司Cantor Fitzgerald駐香港經濟學家及亞洲首席策略師帕爾帕特(Uwe Parpart)說“人們切實關心的問題幾乎沒有提及”,會議成果只是“治標不治本”。
后危機時代博弈
抱團取暖的G20倫敦峰會曾超出大眾希望,但是真正的考驗還在后面。隨著危機的逐步過去,國際社會的凝聚力難免有所消退。IMF總裁卡恩認為,當會議上多數人認為危機已經過去的時候,就更難進行合作了。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首爾峰會上說:“過去我們考慮的是如何解決危機,現在我們面臨的是后危機時代G20該如何做。”舊的世界政治秩序正在瓦解,用韓國《中央日報》的社論說,“歷史無法重返G8時代”,但后危機時代的G20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定位。
歐美國家財政赤字高企,失業率困擾著發達經濟體的復蘇進程。眼下最值得擔憂的是愛爾蘭主權債務問題,如繼續擴散,將再次引發歐洲債務危機(遺憾的是,G20峰會并未就此深入討論)。這種情況下,發展中經濟體拉動世界經濟的力量更加凸現,權力東移的新國際格局逐步成形——擺在會議桌上的不僅是經濟再平衡,還有國際政治舞臺角色的再平衡。
美國不再是唯一的全球游戲規則制定者。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治理舞臺上的聲音更響,底氣更足。《華盛頓郵報》稱,“一年前的G20匹茲堡峰會,各國首腦爭先恐后地討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歡心。但在此次首爾峰會上,誰也不想幫助奧巴馬消除憂愁。”
G20為應對金融危機而生,若今后僅專注于討論金融問題,在國際舞臺上的路子必將越走越窄,步入G8俱樂部“獨樂樂”的后塵。
此次首爾峰會無疑是個轉折點,除了關注國際金融監管、金融機構改革等議題,還把“發展”作為G20未來走向的新路標。韓國總統李明博在G20開幕前的一次記者會上表示:“貧困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成為主要議題才能保持G20峰會的正統性和認同感。”
“發展”議題的設置意味著G20將從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應急機制”轉變為引領世界經濟增長的“常態機制”。與此同時,各方利益訴求更加細化,協調成本也更大。摸索中,大家都需要提升妥協的藝術。
但愿今后的G20峰會不再只有好看的民族時裝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