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冠中的三個“敵人”
石建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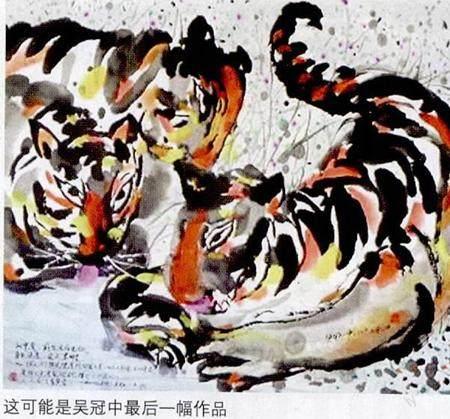
像吳冠中這樣中氣十足的藝術狂人,才能幾十年如一日,為實現自己的藝術理想,同各種勢力或“假想敵”作堅持不懈的斗爭。
2005年我經過與吳冠中的多次深入訪談,寫了一本具有理論研究性質的書籍:《彩面朝天——吳冠中的世界》,初稿形成后我特意去北京將書稿交給吳先生過目。吳先生留下書稿,聊了一會別的事,我告辭后剛回到賓館,他就打電話過來了,對書的內容提了一些非常具體的意見。整個審稿過程就是,他看一章打一個電話,每一個細節都不放過,那種認真一絲不茍的態度令人非常欽佩。同時也使我的這本書提升了質量。
我按照他的要求改動了幾個細節,他打電話過來非常誠懇地對我說:“你寫了我的書,現在就是自己人了,是朋友了,是朋友我們以后就要以誠相待。”老人這番話讓我非常感動。
有一次聊到興頭上,他就跟我說:他的一輩子都為了爭取藝術的自由和理想而奮斗,但是有三股勢力視他為眼中釘。
吳冠中的名望已經很高了,還有人反對他?當時我吃了一驚,連忙問他究竟是哪三股勢力。
老人的話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說:一派是徐悲鴻派的學生,大概以五六十年代中央美院為代表的寫實主義繪畫流派。
我知道,1950年吳先生從法國留學歸國,經同學董希文介紹任中央美院講師。雖然徐悲鴻是吳先生的同鄉,但在藝術立場上,兩人形同冰炭,吳先生的許多文章里并不回避自己對這位院長同鄉的惡感。確實,從近代美術史的發展來看,杭州國立藝專和徐悲鴻派一直是水火不相容的。建國后,徐悲鴻占據了話語權,極力躋身權力中心,大紅大紫,將杭州國立藝專一度收編為中央美院華東分院,當年林風眠、吳大羽等重要人物只得“鳥獸散”。在這一點上,兩個門派之間可以說是有“宿仇”的。不久吳先生就在文藝整風運動中受到批判,被斥為“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堡壘”,1953年被排擠出中央美院,調往清華大學建筑系教授美術基礎課。
還有一派是延安來的一部分“左”的美術干部。這一派建國以后大都在各大美術機構、院校以及文化要害部門掌握實權,他們將吳冠中提出并一貫強調的繪畫的形式美、抽象美等觀念視為洪水猛獸、大逆不道。例如江豐,他就反對傳統的國畫,武斷地認為國畫不能為人民服務,他在美院里一意孤行,調整課程設置,國畫教師幾乎因此“下崗”。1980年,吳冠中在《美術》雜志發表《關于抽象美》一文,引發論戰。江豐對此大為不滿,多次講話中批評了吳冠中,認為馬蒂斯和畢加索是沒有什么可以學習的。在一次美協理事會上,江豐發言攻擊抽象派,因過于激動,突然昏倒。在不久舉行的常務理事會上,江豐講話又攻擊抽象藝術,無法自控地再次暴怒,又昏倒在地,終于沒有救回來。
吳冠中由衷感嘆:“他是為保衛現實主義、搏擊抽象派而犧牲的,他全心全意為信念,并非私念。”他向他的對手致敬。
還有一派是保守的傳統勢力,大致就是指傳統國畫家們。吳先生喝過洋墨水,自覺與他們拉開距離,認為他們太迂腐,太井底之蛙。雖然他早年崇拜潘天壽,跟他學過國畫,一筆“潘體”毛筆字學得惟妙惟肖,但這些后來都被他巧妙地藏起來了。例如他晚年寫字,明明寫的就是書法,其實也不成功。但他偏偏另取花名,美其名曰“漢字構成”。他還故意“挑逗”傳統派,拋出著名的“筆墨等于零”的論調,惹得他們暴跳如雷。張仃等國畫家紛紛起來和他論戰,認為老頭子是嘩眾取寵。其實,吳冠中的戰略倒讓我想起金庸《神雕俠侶》中的楊過最后那種“獨孤求敗”的意思,是故意引國畫家們上圈套的。包括他寫《我讀石濤畫語錄》,對石濤著作重新注解闡述,都是為他宏大的美術戰略而服務的,用另一種方式狠狠嘲笑了因循守舊的傳統國畫家們一把。好像對他們說:喏,你們的眼睛都長在哪里了,老祖宗的藝術秘笈,還要靠我這個“新派”畫家來給你們發掘和發明,你們有什么出息。老頭就是這么頑皮,這么狠。記得《吳冠中全集》出版的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他什么是石濤的“筆墨當隨時代”,吳先生激昂地回答“‘筆墨等于零就是‘筆墨當隨時代”,一個年近九十的老人能說出這樣鏗鏘有力的話來,你看他的氣有多足!
古人講狂者進取,現代人講唯有偏執狂才能生存。可以說也只有像吳冠中這樣中氣十足的藝術狂人,才能幾十年如一日,為實現自己的藝術理想,同各種勢力或“假想敵”作堅持不懈的斗爭。他一生的戰斗精神倒真是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