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商君“強(qiáng)國(guó)弱民”理念
○王子今
商鞅改革成效與他個(gè)人的悲劇結(jié)局成為千百年歷史評(píng)論的主題。如果我們關(guān)注商鞅“強(qiáng)國(guó)弱民”理念在行政實(shí)踐中的成敗得失,可以深化對(duì)中國(guó)改革史的認(rèn)識(shí)。
求國(guó)強(qiáng)而弱民,崇尚專制與強(qiáng)權(quán),的確成功推行了新法,但也暴露出嚴(yán)重的弊端。秦政成敗皆由之。
變法使秦國(guó)強(qiáng)盛,終于滅六國(guó),兼天下;然而在軍事成功的另一面,卻是文化上的“天下大敗”,道德淪喪,風(fēng)俗敗壞。
商鞅變法是促使秦國(guó)迅速崛起的重要的政治轉(zhuǎn)折,也被看作改革成功的實(shí)例。所謂“秦用商君,富國(guó)強(qiáng)兵”(《史記》卷七四《孟子荀卿列傳》),成為后來實(shí)現(xiàn)統(tǒng)一的歷史基礎(chǔ)。商鞅制定的新法除了獎(jiǎng)勵(lì)耕戰(zhàn)而外,又有更具實(shí)效的通過什伍連坐制度將民眾組織在政治網(wǎng)絡(luò)中的內(nèi)容,并且以法令形式強(qiáng)制削殺宗室貴族的政治權(quán)利,“有功者顯榮,無(wú)功者雖富無(wú)所芬華”。據(jù)說正是由于打擊舊勢(shì)力之嚴(yán)厲,“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在強(qiáng)有力的支持者秦孝公去世后,新君即位,商鞅不久竟慘遭車裂之刑。然而正如《韓非子·定法》所說,商君雖死,“秦法未敗也”。商鞅改革成效與他個(gè)人的悲劇結(jié)局成為千百年歷史評(píng)論的主題。如果我們關(guān)注商鞅“強(qiáng)國(guó)弱民”理念在行政實(shí)踐中的成敗得失,也可以深化對(duì)中國(guó)改革史的認(rèn)識(shí)。
商鞅雖死,后世卻遵其法
秦孝公發(fā)起變法的動(dòng)機(jī),是謀求“秦強(qiáng)”。《史記》卷五《秦本紀(jì)》記載,“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qiáng)國(guó)六”,“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guó)諸侯之會(huì)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戰(zhàn)士,明功賞。下令國(guó)中”,宣布:“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jì)強(qiáng)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商鞅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西行入秦,求見孝公,建議“變法修刑,內(nèi)務(wù)耕稼,外勸戰(zhàn)死之賞罰”,得到贊許。于是“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商鞅因變法有效,封列侯,號(hào)商君。
《史記》卷四四《魏世家》說:“秦用商君,東地至河”,“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也說,新法推行9年,“秦人富強(qiáng),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秦國(guó)“富強(qiáng)”的事實(shí),得到了周天子和諸侯列國(guó)的承認(rèn)。按照賈誼《過秦論》的說法:“秦孝公據(jù)殳肴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nèi),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dāng)是時(shí),商君佐之,內(nèi)立法度,務(wù)耕織,修守戰(zhàn)之備,外連衡而斗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的迅速?gòu)?qiáng)盛,在于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nèi),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的雄心,而“商君佐之”,“內(nèi)”“外”均有成功建樹。
蔡澤評(píng)價(jià)商鞅事跡,有“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的感嘆,對(duì)于商鞅之成功的具體內(nèi)容,則說“: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quán)衡,正度量,調(diào)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yè)而一其俗,勸民耕農(nóng)利土,一室無(wú)二事,力田 禾畜積,習(xí)戰(zhàn)陳之事,是以兵動(dòng)而地廣,兵休而國(guó)富,故秦?zé)o敵于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guó)之業(yè)。”(《史記》卷七九《范睢蔡澤列傳》)其終極意義正在于有效“強(qiáng)秦”,實(shí)現(xiàn)了“秦?zé)o敵于天下”的威勢(shì)。
司馬遷在《史記》卷一三○《太史公自序》中使用的總結(jié)性語(yǔ)言,肯定了商君的歷史功績(jī):“鞅去衛(wèi)適秦,能明其術(shù),強(qiáng)霸孝公,后世遵其法。”商鞅“強(qiáng)霸孝公”,實(shí)現(xiàn)了秦孝公“強(qiáng)秦”的夙愿,也完成了為秦的帝業(yè)奠基的歷史任務(wù)。所謂“后世遵其法”,是確定的歷史事實(shí)。殺滅商鞅人身的秦惠文王依然堅(jiān)持商鞅之法,維持了政策的穩(wěn)定性。直到秦末,商鞅時(shí)代制定的法律體系和政策方向仍是執(zhí)政的主導(dǎo)。而《后漢書》卷四○上《班彪傳》、《續(xù)漢書·輿服志上》與《輿服志下》、《三國(guó)志》卷一《魏書·武帝紀(jì)》裴松之注引《魏書》以及《晉書》卷三○《刑法志》等都說“漢承秦制”。《后漢書》卷五二《荀爽傳》又有“漢承秦法”的說法。《史記》卷一○七《魏其武安侯列傳》張守節(jié)《正義》:“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并依秦法。”《漢書》卷七《昭帝紀(jì)》顏師古注引如淳曰:“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漢書》卷八《宣帝紀(jì)》顏師古注引文穎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為律令,律經(jīng)是也。”商鞅參與設(shè)計(jì)的秦的制度似乎延續(xù)著超穩(wěn)定的效能。實(shí)際上直到昭宣時(shí)代,依然可以聽到帝王親自發(fā)布的“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的宣言(《漢書》卷九《元帝紀(jì)》),告知人們秦的法家傳統(tǒng)長(zhǎng)久發(fā)生著政治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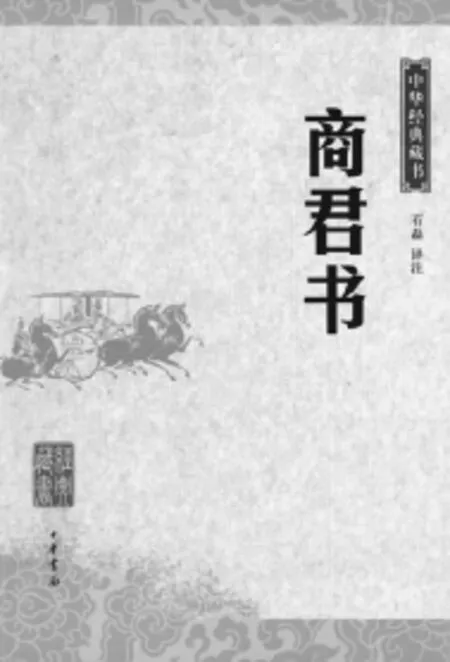
《商君書——中華經(jīng)典藏書》,石磊譯注,中華書局2009年10月版,11.00元
謀求“強(qiáng)國(guó)”,強(qiáng)調(diào)“弱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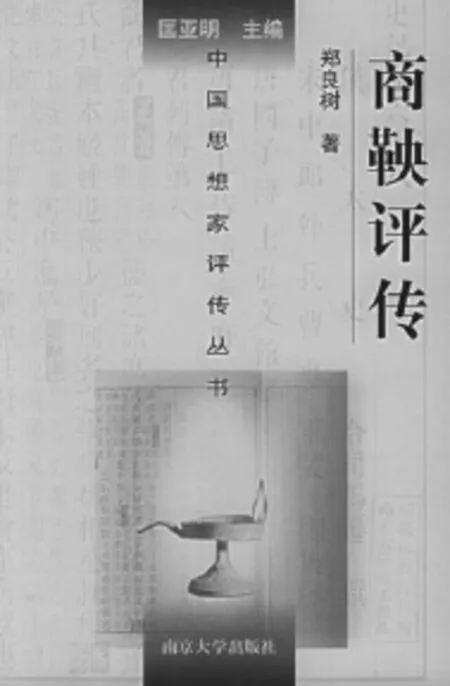
《商鞅評(píng)傳》,鄭良樹著,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12月版,20.00元
商鞅的行政理念有一個(gè)重要的原則,就是在謀求“強(qiáng)國(guó)”的另一面,強(qiáng)調(diào)“弱民”,即壓抑民眾的欲求、智能、意愿、權(quán)利,限制其可能參與社會(huì)管理和國(guó)家行政的條件。
《商君書·墾令》主張的政治導(dǎo)向包括“民不貴學(xué)問”,以為:“民不貴學(xué)問則愚,愚則無(wú)外交,無(wú)外交則國(guó)安而不殆。”又期望“農(nóng)靜誅愚”。俞樾《諸子平議》指出“誅通作朱”,“誅愚”就是《莊子·庚桑楚》“人謂我朱愚”的“朱愚”,“朱義與愚近”。高亨將“農(nóng)靜誅愚”解釋為“農(nóng)民安靜而愚昧”(《商君書注譯》,中華書局1974年11月版,P 25)。商鞅以“愚農(nóng)無(wú)知,不好學(xué)問”作為行政理想,主張徹底的愚民。《商君書·農(nóng)戰(zhàn)》中甚至說:“農(nóng)戰(zhàn)之民千人,而有《詩(shī)》《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農(nóng)戰(zhàn)矣。”民眾中有千分之一的人有一定的知識(shí),也會(huì)敗壞行政主張的實(shí)施。民眾心理簡(jiǎn)單,專心務(wù)農(nóng),就便于管理,易于驅(qū)使:“圣人知治國(guó)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nóng)。歸心于農(nóng),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zhàn)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以賞罰進(jìn)也;壹則可以外用也。”《商君書·壹言》也說“治國(guó)者貴民壹,民壹則樸”。所謂“夫開而不塞,則短長(zhǎng);長(zhǎng)而不攻,則有奸”,按照高亨的譯文,就是說:“治國(guó),如果開導(dǎo)人民的知識(shí),而不加以堵塞,人民的知識(shí)就增長(zhǎng)。人民的知識(shí)增長(zhǎng),而不去攻打敵國(guó),就產(chǎn)生奸邪。”(《商君書注譯》,P 83)
對(duì)于民眾和行政的關(guān)系,《商君書·說民》期望“政勝其民”,期望“法勝民”,認(rèn)為:“民勝其政,國(guó)弱;政勝其民,兵強(qiáng)。”“民勝法,國(guó)亂;法勝民,兵強(qiáng)。”用“政”“法”壓制民心、民欲、民智、民權(quán),則“兵強(qiáng)”。如果反之,則“國(guó)弱”、“國(guó)亂”。
《商君書》專有《弱民》一篇,開篇就提出“民弱國(guó)強(qiáng),國(guó)強(qiáng)民弱”的政治公式,強(qiáng)調(diào)“有道之國(guó),務(wù)在弱民”的主張:“樸則強(qiáng),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qiáng)。”朱師轍《商君書解詁》說,“樸則強(qiáng),淫則弱”應(yīng)作“樸則弱,淫則強(qiáng)”。按照有的學(xué)者的理解,這段文字可以這樣讀:“民眾樸實(shí),就不敢抗拒法令;民眾放蕩,就不把法令放在眼里。不敢抗拒法令,思想行動(dòng)就不會(huì)越軌;蔑視法令,就會(huì)胡思亂想胡作非為。思想行動(dòng)規(guī)規(guī)矩矩,就能聽從役使;胡思亂想胡作非為,就難以駕馭。”(《商子譯注》,齊魯書社1982年10月版,P 142)可以看到,商鞅期求“民弱”,是要讓民眾樸實(shí)專一,簡(jiǎn)單麻木,恪守法軌,服從控制。《商君書·農(nóng)戰(zhàn)》中的說法,就是“民樸一”,“則奸不生”。
《商君書·弱民》又寫道:“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qiáng)。民弱國(guó)強(qiáng),民強(qiáng)國(guó)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qiáng);民強(qiáng)而強(qiáng)之,兵重弱。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民弱而弱之,兵重強(qiáng)。故以強(qiáng)重弱,削;弱重強(qiáng),王。以強(qiáng)攻強(qiáng),弱,強(qiáng)存;以弱攻弱,強(qiáng),強(qiáng)去。強(qiáng)存則削,強(qiáng)去則王。故以強(qiáng)攻弱,削;以弱攻強(qiáng),王也。”這里具體涉及“弱民”的政策導(dǎo)向。這段話的文意,據(jù)高亨提示,即:“政策建立人民所憎惡的東西,人民就弱;政策建立人民所喜歡的東西,人民就強(qiáng)。人民弱,國(guó)家就強(qiáng);人民強(qiáng),國(guó)家就弱。人民所喜歡的是人民強(qiáng);如果人民強(qiáng)了,而政策又使他們更強(qiáng),結(jié)果,兵力就弱而又弱了。人民所喜歡的是人民強(qiáng);如果人民強(qiáng)了,而政策又使他們轉(zhuǎn)弱,結(jié)果,兵力就強(qiáng)而又強(qiáng)了。所以實(shí)行強(qiáng)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國(guó)家就削;實(shí)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強(qiáng)而又強(qiáng),就能成就王業(yè)。用強(qiáng)民的政策攻治強(qiáng)民和弱民,強(qiáng)民是依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強(qiáng)民,強(qiáng)民就會(huì)消滅。強(qiáng)民存在,國(guó)家就弱;強(qiáng)民消滅,就能成就王業(yè)。可見,用強(qiáng)民政策統(tǒng)治強(qiáng)民,國(guó)家就會(huì)削弱;用弱民政策統(tǒng)治強(qiáng)民,就能成就王業(yè)。”(《商君書注譯》,P 161)“民”被區(qū)分為“強(qiáng)民”和“弱民”。在通常的情況下,成就王業(yè),要消滅或者壓制“強(qiáng)民”。實(shí)行“弱民”的政策,就能夠“成就王業(yè)”。秦政的歷史性成功,應(yīng)當(dāng)就是遵循了這一原則。秦政的失敗,也與這樣的政策傾向有關(guān)。
《商君書》并不完全出于商鞅之手。但是作為商鞅追隨者總結(jié)的理論,也是與商鞅的政治理念基本符合的。
崇尚專制與強(qiáng)權(quán)
《史記》卷五《秦本紀(jì)》關(guān)于商鞅變法所謂“法大用,秦人治”,記錄了商鞅之法確實(shí)得以成功推行的情形。《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說,新法施行一年,“秦民之國(guó)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shù)”,甚至“太子犯法”。商鞅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應(yīng)當(dāng)懲治太子,然而“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據(jù)說,“明日,秦人皆趨令”。新的法令得到擁護(hù),“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wú)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鄉(xiāng)邑大治”。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商鞅說,“此皆亂化之民也”,把他們都流放到邊城。于是,“其后民莫敢議令”。商鞅執(zhí)法嚴(yán)厲,甚至禁止人們對(duì)法令的內(nèi)容和執(zhí)法的形式有所議論。
面對(duì)秦末暴動(dòng)的歷史,人們“因民之疾秦法”(《史記》卷五三《蕭相國(guó)世家》)而產(chǎn)生的認(rèn)識(shí),有所謂“秦法重”(《史記》卷八九《張耳陳余列傳》)、“秦法酷烈”(《漢書》卷八七下《揚(yáng)雄傳下》)、“秦法酷急”(《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jì)》張守節(jié)《正義》)、“秦法峻急”(《漢書》卷三○《藝文志》顏師古注引《家語(yǔ)》)等。《鹽鐵論·刑德》:“秦法繁于秋荼,而網(wǎng)密于凝脂。”《史記》卷一二二《酷吏列傳》:“昔天下之網(wǎng)嘗密矣。”司馬貞《索隱》:“案:《鹽鐵論》云‘秦法密于凝脂’。”“秋荼”“凝脂”之說,形容了秦法繁密嚴(yán)酷的程度。
秦統(tǒng)一后,東方新占領(lǐng)區(qū)的政策似乎是失敗的。這是導(dǎo)致秦短促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反秦的“群盜”均出現(xiàn)于東方。當(dāng)時(shí)的關(guān)中,并沒有發(fā)生反秦運(yùn)動(dòng)(參看王子今:《秦王朝關(guān)東政策的失敗與秦的覆亡》,《史林》1986年2期)。然而劉邦入關(guān),宣布約法三章時(shí),有“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的說法(《史記》卷八《高祖本紀(jì)》)。《史記》卷九二《淮陰侯列傳》載韓信對(duì)劉邦語(yǔ):“大王之入武關(guān),秋毫無(wú)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wú)不欲得大王王秦者。”看來,“秦民”對(duì)“秦苛法”的廢除,也是真心擁護(hù)的。《漢書》卷二三《刑法志》稱“約法三章”以致“蠲削煩苛,兆民大說”。《漢書》卷二六《天文志》則說:“與秦民約法三章,民亡不歸心者。”《三國(guó)志》卷三五《蜀書·諸葛亮傳》:“昔高祖入關(guān),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也說“秦民”對(duì)“秦法”的嚴(yán)酷久已反感。
《戰(zhàn)國(guó)策·秦策一》說,“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wú)私,罰不諱強(qiáng)……”于是“兵革大強(qiáng),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qiáng)服之耳”。秦法壓抑民眾“以強(qiáng)服之”者,尤其表現(xiàn)在對(duì)思想和言論的強(qiáng)權(quán)控制。《史記》卷九七《酈生陸賈列傳》:“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wú)類。”《漢書》卷一上《高帝紀(jì)上》顏師古注引應(yīng)劭曰:“秦法禁民聚語(yǔ)。”《漢書》卷一三《異姓諸侯王表》顏師古注應(yīng)劭曰:“秦法,誹謗者族。”都指出了秦法對(duì)思想言論的高壓。由于商鞅的成功,法家思想和主張?jiān)谇氐氐玫捷^為全面的貫徹和落實(shí)。而法家崇尚專制與強(qiáng)權(quán)的傾向,在政治實(shí)踐中最初的表現(xiàn)也暴露出嚴(yán)重的弊端。其典型史例就是商鞅的事跡。李約瑟在《中國(guó)科學(xué)技術(shù)史》第2卷《科學(xué)思想史》中寫道:“(法家)以編訂‘法律’為務(wù),并認(rèn)為自己主要的責(zé)任是以封建官僚國(guó)家來代替封建體制。他們倡導(dǎo)的極權(quán)主義頗近于法西斯……”“法家”和“法西斯”盡管看起來都姓“法”,兩者之間的簡(jiǎn)單類比我們卻未必完全同意。但是法家“倡導(dǎo)”“極權(quán)主義”的特征,卻是確定無(wú)疑的。
關(guān)于商君“刻薄”
司馬遷在《商君列傳》中評(píng)價(jià)商鞅的個(gè)人品性和政治風(fēng)格,有“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的說法,又指出其“少恩”,說:“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zhàn)》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商鞅在秦國(guó)并沒有樹立起正面的政治形象,又長(zhǎng)期成為歷代政論家的批判對(duì)象,確實(shí)是有道理的。對(duì)于“刻薄”,司馬貞《索隱》:“謂天資其人為刻薄之行,‘刻’謂用刑深刻,‘薄’謂棄仁義不悃誠(chéng)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又欺魏將,是其天資自有狙詐。”
明代學(xué)者張燧《千百年眼》曾經(jīng)稱許改革家商鞅其意志的堅(jiān)定果決:“(商)鞅一切不顧,真是有豪杰胸膽!”然而商鞅對(duì)于文化的冷漠,卻長(zhǎng)期受到歷代文化人,特別是儒學(xué)學(xué)者的指責(zé)。班固說:“商鞅挾三術(shù)以鉆孝公。”又說商鞅是“衰周之兇人”(《漢書》卷一○○上《敘傳上》)。所謂“三術(shù)”,按照應(yīng)劭的解說,是“王”、“霸”和“富國(guó)強(qiáng)兵”之術(shù)。可見,商鞅的政治思想是以“術(shù)”即策略方式作為主體內(nèi)容的。而這種“術(shù)”,其實(shí)只是以“富國(guó)強(qiáng)兵”為目標(biāo)的追求短期實(shí)效的具體政策。《漢書》卷六《武帝紀(jì)》顏師古注引用李奇的說法:“商鞅為法,賞不失卑,刑不諱尊,然深刻無(wú)恩德。”后來有人甚至認(rèn)為商鞅應(yīng)當(dāng)為秦國(guó)“風(fēng)俗凋薄,號(hào)為虎狼”承擔(dān)責(zé)任(《魏書》卷一一一《刑罰志》)。朱熹也曾經(jīng)批評(píng):“他欲致富強(qiáng)而已,無(wú)教化仁愛之本,所以為可罪也。”(《朱子語(yǔ)類》卷五六)就是說,只是片面追求國(guó)家“富強(qiáng)”,甚至不惜以文化倒退為犧牲來?yè)Q取“國(guó)強(qiáng)”,因此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歷史罪責(zé)。司馬遷評(píng)價(jià)商鞅行政所謂“刻薄”“少恩”,不只是對(duì)商鞅個(gè)人進(jìn)行道德品性和文化資質(zhì)的分析,實(shí)際上也發(fā)表了對(duì)商鞅改革的社會(huì)歷史效應(yīng)的一種文化感覺。《戰(zhàn)國(guó)策·秦策一》說商鞅推行新法,“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qiáng),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qiáng)服之耳”。所謂“刻深寡恩”,高誘解釋說:“刻,急也。寡,少也。深,重也。言少恩仁也。”
賈誼《陳政事疏》批評(píng)商鞅“遺禮義,棄仁恩”,輕視思想文化的建樹而專力于軍事政治的進(jìn)取,竟然導(dǎo)致“秦俗日敗”,社會(huì)風(fēng)習(xí)頹壞,世情澆薄。家族間的親情紐帶也為實(shí)際的利益追求所斬?cái)唷.?dāng)時(shí)秦國(guó)民間,據(jù)說“借父,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yǔ)”。將耱鋤一類農(nóng)具借給父親,也會(huì)以為施以恩惠而容色自矜,母親取用箕帚一類用物,竟然可以惡言咒罵。秦人自商鞅之后興起功利第一的時(shí)代精神,雖然能夠“并心而赴時(shí)”,致使秦國(guó)強(qiáng)盛,“信并兼之法,遂進(jìn)取之業(yè)”,終于滅六國(guó),兼天下,然而在軍事成功的另一面,卻是文化上的“天下大敗”。道德的淪喪,風(fēng)俗的敗壞,已經(jīng)“不同禽獸者亡幾耳”,原先的“廉愧之節(jié),仁義之厚”,已經(jīng)難以復(fù)歸(《漢書》卷四八《賈誼傳》)。許多年之后,引起人們深切感嘆的我們國(guó)民性中若干陰暗面的消極表現(xiàn),如自私、冷酷等等,或許都可以在商鞅這樣的法家政治家的實(shí)踐中看到早期發(fā)生的因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