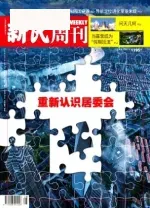李想:永遠都覺得自己長大了
張海律


李想從來不覺得經歷過什么逆境,不會去跟自己較勁,會輕描淡寫地面對一切好與不好,即便是存款只有2萬元時。
作為很早就成名的80后創(chuàng)業(yè)者,李想經常在微博上發(fā)出頗成熟也頗有見地的人生感悟。
比如,“薛總當時跟我講,美國總統(tǒng)該放放假,他也是個正常人,這對我觸動很大。從那以后我、同事、家人的幸福指數就大幅提升。作為管理者,如果我不正常,我就會認為正常的人其實不正常,這樣同事和家人就慘了。”
經過前幾年媒體對80后創(chuàng)業(yè)家的一番熱炒后,李想身邊的一切歸于“正常”:正常的工作環(huán)境、正常的作息時間、正常的家庭生活。如果非要說有什么“不正常”,那或許是“從小就比同齡人甚至比長輩要想事情想得明白”,李想這孩子,一直那么成熟。
天生的管理者
2005年的媒體炒作,造成了一個尷尬的結果:知道李想的人比知道“泡泡網”的人多,知道“泡泡網”的人比知道“汽車之家”的人多,知道李想現在管理著兩個汽車網站的人就更少了。當然,這番炒作多少有點積極意義,個人知名度提升的同時,也帶動公司和網站知名度的提升。
剛出名那會兒,什么樣的采訪都接,漸漸地,李想開始不接受采訪了。風吹過了,媒體的眼睛也自然閃開了,興趣轉移到汽車上的李想,可以踏踏實實地做自己喜歡的汽車網站了。還是評測和導購,跟做泡泡網時類似,5年間陸續(xù)成立了汽車之家和車168兩家網站。廣告,依然是網站收益的大頭,4S店的會員費是另一塊,類似于泡泡網那種按點擊量對經銷商收“攤位費”的渠道服務模式。
如今,李想的全部精力都留給了兩家汽車網,維持其每天的正常運行,管理好下面的300多名員工。而讓其功成名就的“泡泡網”,則在運行順利并被澳洲電訊并購55%的股份后,被李想放手給新團隊去運作了,如今的泡泡網有多大規(guī)模、多少員工,他都完全不清楚了。
他說:“當時覺得能賺上二三百萬就不得了了,很滿足了,但當錢越來越多的時候,錢反而變成次要的東西,最重要的是帶領團隊去實現新的目標。”
李想是個目標感非常清晰的人,而且天生就是做管理的料。去年接管“車168”網站后,他用了一年時間調整和了解團隊,把最有干勁、最優(yōu)秀的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也讓不適合這個團隊的人離開了。
他說,“大家總說我對于產品的要求是像素級的,但我并不是一個愿意細節(jié)管理的人,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比我管得更好,每個人都應該是自我驅動的,并在自己的管理范疇和空間中把自己的價值最大化,而不是變成一個大事小事都聽上級命令的團隊,只有這樣,我才不會成為團隊發(fā)展的瓶頸,我們才更有創(chuàng)造力和價值。”
李想相信,只有讓團隊中的人都“正常化”,都做正常的自己,團隊的“任督二脈”才能被打通,“如果我操勞到要針對不同的團隊用不同的管法,那樣我會人格分裂的。”
興趣,對李想來說不僅僅是最好的老師。因為喜歡電腦,所以做了泡泡網;因為迷上汽車,就有了汽車網站。至于要把一件事做多大做多深,則取決于有沒有用戶需求,這里就藏匿著市場機會。至少現在,沒產生新興趣點的李想還沒看到比汽車更大的市場行業(yè),“現在汽車的產業(yè)鏈非常廣,不能只看到新車銷售,還有二手車、配件、保險、售后、租車、接送等等環(huán)節(jié),可做的事情非常多,我們也遠遠沒做透。是否選擇一個領域去做,要不要深入,最根本的因素是有沒有用戶需求,不能是小眾用戶,必須是大眾。我們自身的優(yōu)勢就是用戶量是所有網站中最大的,所以要選擇進入一個領域,只要客戶還是同一批,都能很快成為相應網站的前三名。”
正常的生活形態(tài)
李想本人并不把結婚當作這5年來最大的生活轉變。“我覺得這是很正常的事,水到渠成。”于是,他從工作的正常平穩(wěn)過渡到家庭生活的正常,等有了小孩后,還將是另一種三人生活的正常。
因為正常,李想如今的工作日有著非常固定的作息,“不再熬夜了,不會去做很多非常具體的事,更多的是對公司制度的規(guī)劃以及跟員工的溝通,每天的會議不超過一個,時間也不長。我和5年前一樣,沒什么應酬,也不會在8小時外見什么客戶,從沒什么事情是非得在晚上去解決的。工作時跟同事們在一起;下班后跟家人和朋友在一起”;周末和節(jié)假日也沒什么特別,好好休息,繼續(xù)上網,買一堆書和雜志,看看電影,出外做講座也是能推則推。倒是想要重新?lián)炱鹬袛嗔艘荒甑淖闱蜻\動。
因為正常,李想非常在意享受活在當下的感覺,并對未來充滿期望。對于過去,也只記住美好的東西,不好的懶得去記憶,因為人沒法改變過去。這些年畢竟還算順利,可遇到逆境時呢?“也一樣會這么想,繼續(xù)享受活在當下,過去所有好的壞的,都會變成經歷。一個人每天在做三種事,對的、錯的和毫無意義的,我不喜歡也不會去做毫無意義的,我可能會做對的會做錯的,把錯的反過來它就是對的,就是這么個最簡單的邏輯。”
因此,李想從來不覺得經歷過什么逆境,不會去跟自己較勁,會輕描淡寫地面對一切好與不好,即便是存款只有2萬元時。
因為正常,李想獲取了另一種外在的自信,不會太注重多余的時尚。有些人可能比較在乎生意對象是否戴手表,把它夸大為一種守時可靠的象征,但不戴手表的李想認為所有的東西必須是實用的,如果累贅不實用,都會立即把它取消,“天天想著別人怎么看,就累死了”。要跟政府官員打交道時,也不會因為他們的方式而改變自己,“我發(fā)現,往往你不需要去裝著繞來繞去時,對方可能更認可你”。
畢竟是電腦時代推出的弄潮兒,李想對前沿的實用科技還一直充滿熱情。運營商糟糕的網絡,讓李想只好把iPhone3GS完全當作移動軟件的運用平臺,而日常的通訊需求不得不回到諾基亞和移動網絡,這番對比,讓李想覺得“就像天天睡在身邊的女朋友,從徐若瑄變成了鳳姐一樣,還天天嘮叨(主要的垃圾短信)”。
而有了iPad3G后,李想也再次被電子產品改變生活習慣,“不需要再買《南方周末》,我會通過客戶端去看,而且還有內容下的評論,這對閱讀者很方便,不會因為下雨就買不著報紙,不會弄得滿手油墨,老頭子和小孩子也都能半小時內學會”。
在與同類創(chuàng)業(yè)者交往的這樣一種穩(wěn)定關系中,李想感覺“永遠都覺得自己長大了,但回頭看,又永遠覺得自己沒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