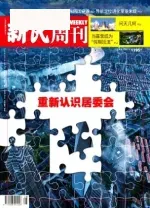稀土背后的政治與地緣角力
石渝

當需求上升到一個臨界點之后,擁有供應和萃取技術壟斷權的就能獲得絕對資源優勢,表現在定價權爭奪上時,這樣的資源戰爭就是全球供應鏈上的資源爭奪戰的一部分。
在門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里,有一片神秘的由17種高熔點金屬元素組成的區域,這些金屬含量稀少,又常以氧化物的“土”顆粒狀態存在,所以就有了“稀土”之說。
“稀土”并不土。當今尖頂武器、激光制導、新能源開發、汽車混合動力等技術開發,無一不與稀土緊密相聯,甚至可以說,“稀土就是高科技”。上世紀60年代曾經喊出“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世界”宏論的基辛格,相信今天也會認同“誰擁有了不可再生資源稀土,誰就掌控了未來”之論斷。
當需求上升到一個臨界點之后,擁有供應和萃取技術壟斷權的就能獲得絕對資源優勢,表現在定價權爭奪上時,這樣的資源戰爭就是全球供應鏈上的資源爭奪戰的一部分。而一旦把壟斷權的作用延展到外交領域,并服務于政治目的,“資源戰爭”就轉化為地緣政治對抗,沖突已是非一般貿易規則能有效平息,這會催生旨在破除資源或技術壟斷的政治和權力板塊重組。稀土當前面臨的處境,正好就是這樣。
一張奇怪的稀土世界地圖
稀土人人有,只是多少不等。在已探明的稀土儲量中,美國人的稀土儲量至少有2700萬噸,占世界的12.86%,以俄羅斯為中心的獨聯體有4000萬噸,占世界儲量的19.5%。這個比例的意義只在于已經勘探并探明的礦區,而對尚未勘探的世界大部分地區,稀土儲量如何,依然是個未知數。其中,巴西、蒙古、澳大利亞、印度、越南、哈薩克斯坦等不斷傳來新的稀土礦探明的新聞,其中印度是世界上第五大稀土生產國。這至少說明,某一地資源的枯竭,還不必然構成世界總儲量的減少。
然而,攤開資源地圖時,我們會驚訝地發現世界最大的稀土礦業處于關閉或半歇業狀態中,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美國的芒廷帕司稀土礦和貝諾杰稀土礦、加拿大的托爾湖和霍益達斯湖稀土礦、澳大利亞的韋爾德山稀土礦和諾蘭稀土礦等。
甚至有80年稀土生產史的歐洲不可一世的法國羅納普朗克公司,也基本上在歐洲和美洲市場看不到影子,它已經改頭換面,潛入到中國大陸,盡管其營業額排行仍居世界稀土生產廠之首。
而僅占世界已探明儲量三分之一、資源日見耗竭的中國,卻承擔著90%出口市場份額,有時甚至高達98%近“一統天下”的地步。似乎人人都要向中國伸手要稀土。
有資源不開采,坐視別人“做大”,這樣的壟斷是我們自己掙來的,還是別人送的,想想也能明白。
稀土礦的開采破壞生態,影響環保。在一個環保要求較低及勞動力較廉價的地方,稀土的大量開采及低價出口,使需求稀土金屬的國家樂得關閉本國污染環境的礦區。
從2007年起,美國幾乎都封存了全國所有稀土礦區,以一種最自然的最廉價的方式實現了稀土資源的戰略儲備。日本也悄然收起了海底探礦的計劃,從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的資源儲備,進入21世紀后再加大幅度,從“夠一個月”的儲備上升到幾乎能滿足20年之用的稀土資源儲備。這些稀土全都是從中國廉價進口的。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中我國稀土出口損失外匯幾十億美元,憑空使日本、韓國等收購儲備了可供20年使用的中國的廉價高質量單一稀土。
仰仗著20年儲備實力和可以隨時解封開采的潛力,只要稀土價格一上升,日本等就以不買或少買來干擾價格。定價權居然沒有落入“資源壟斷者”手里,這也是天下一大奇觀。
自“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的戰略思想之后,中國謀求“資源換技術”,但時至今日,中國依然在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上徘徊,深加工產品及稀土技術產品仍然沒有取得與稀土出口份額相稱的地位。
中國中了圈套?
早在1983年,精明的日本人就預感到總有一天會有“斷供”的可能,所以就出臺了稀有礦產戰略儲備制度,規定國家和部分有關企業必須儲備,規定國家和部分有關企業必須儲備一定數量的釩、錳、鈷、鎳、鉬、鎢等稀有金屬,通常情況下,日本的稀有金屬儲備必須足夠全國3個月左右的需求。這個目標隨著中國169個稀土企業競相壓價甩賣稀土,通過合法進口和出私等手段,已經超額完成。
2009年7月,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發布的“確保稀有金屬穩定供應戰略”(StrategyforEnsuringStableSuppliesofRareMetals),預感到中國資源枯竭后的供應源困境,就提出了來源多元化戰略。然而,困于國內議會阻力,戰略并沒有得到財政支持。
10月26日,日本國會很快通過了3369億日元的追加預算案,加上原來的1000億日元,這筆專款將專門用于和第三國合作開發稀土資源,以及支持國內稀土金屬回收利用技術開發。
日本分別于10月2日同蒙古、10月24日與印度、10月31日與越南達成了稀土開發的協議。盡管印度要價很高,只要日方的萃取技術,不會出口原材料,但日方憑借稀土冶煉和萃取技術上的“壟斷地位”,很快會在印度稀土爭奪中占上風。10月26日日本國會通過的這筆累計4369億日元巨資均投入到了與中國構成地緣競爭關系的國家,加上日本已經開展了業務的哈薩斯坦稀土業,日方憑借“需求優勢”、“資金優勢”、“技術優勢”,沖淡了中國目前在市場份額上的名義“壟斷”。
短短的兩個月,日本把覬覦資源市場的美歐“糊弄”了一把,高呼“來源多元化”的歐美只有眼睜睜地看著日本搶先進入對資金和技術都有需求的國家里。
配額之痛
產能過剩、無序競爭、大量廉價出口,這樣毀滅性的開發,不僅留下了巨大的環保平復成本,也重挫了中國成為稀土強國的決心。2006年前,外部需求不到10萬噸稀土,中國卻生產了20萬噸,價格狂跌,結果刺激美澳加等國封存自己的國內工廠,舉著投資的旗幟,把生產線搬到中國來。
2007年之后,國務院開始執行出口配額制,外部需要為10萬噸的情況下,中國定的配額為8萬噸。這個配額制釋放了一個信息,中國不贊成把他們所有的需要都由中國來承擔的做法,中國也希望他們執行來源多元化。
但中國真正的著眼點,可能不是配額本身,因為配額只適用于原材料出品,歐美所需要的技術性產品或加工產品的稀土不受此限。中國真正要實現的就是綠色技術的提升。
據路透社報道稱,中國在風力發電機組、混合動力和電動汽車以及其他清潔能源創新方面雄心勃勃,這些領域都要用到稀土金屬。
“中國體系最大的推動力是持續的就業和經濟增長。若能通過揮舞稀土的‘大棒,將大量綠色產業中的高端制造業的工作崗位,以及諸多知識產能移往中國,他們是愿意這么做的。”拜倫資本市場清潔能源分析師海卡威說道。
然而,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的約翰·西亞曼則認為,中國突然減少稀土出口可能使外國公司對于遷至中國更加謹慎。“公司本已擔心主權風險,提心生產鏈太過信賴中國。”
由于配額制推行后,經過2008年價格短暫下挫后,2009年迎來大漲。美國議員們正要支持重新開啟加利福尼亞州封存了許久的芒廷帕斯稀土礦。價格杠桿下,中國的優勢或許被侵蝕。
G20會不會再炒稀土?
日本滿世界找替代來源,但這些墨跡未干的協議,離真正落實、執行并產生效益,還有若干年的時間。正如日本《鉆石》周刊10月30日載文評論的一樣,日本的強悍恐只能逞一時,日本包括世界難以擺脫對中國稀土的依賴。的確,日本推動的替代稀土金屬計劃,離技術成熟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11月11日到12日,半年一度的G20峰會就要在韓國首爾舉行。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在海南島與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會見時候再次重申了之前希拉里與中國外長會面時中方的維持稀土供應的承諾。中方稱,中方從來不把稀土視為“經濟武器”,也沒有禁止過出口。中方稱,估計是海關等手續上的問題,導致了出口過程的一些拖延。而對于配額,中方認為,管控稀土資源是中國的主權權利,也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規定。中方稱,全世界都重度依賴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是無能為力的。
中方與美方的及時溝通,或許有助于外界理解中方的立場。在此之前,白宮發言人吉布斯10月26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如果美國政府的安全和經濟主管部門認為有必要,“將毫不猶豫地在G20首爾峰會上提出稀土問題”。此外,美國貿易代表處(USTR)也根據貿易法301條款,調查中國在環保技術貿易和投資方面的相關政策,稀土出口情況也屬調查對象。德國經濟部部長布呂德勒10月26日稱,自由貿易協議必須適用于所有商品,特別是稀土資源。任何國家要保持在國際市場的活躍度,就必須同時開放本土市場。
美方及歐盟已經理解了中方提出的“稀土問題上不能完全依賴中國”,但從貿易層次上,它們對中方的限制甚至禁止出口的手法是否被濫用了,仍然咬著不放。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在10月中已召集美、英、德、法、韓等各主要國駐華大使,聲稱中國的稀土出口規制“存在問題”,要求中國緩和對稀土的出口管制。
從目前G20的議題上看,作為全球經濟合作最高論壇的G20,自然會把當前更熱門更宏觀的議題列入其中,如匯率、平衡增長、IMF投票權改革,韓方也借東道主之便,加入全球氣候、聯合國千年計劃等問題。盡管如此,依然不能排除日本把這個問題強行帶入G20的可能性,就如河內東亞峰會上,中日釣魚島主權爭執被日本炒作成題外題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