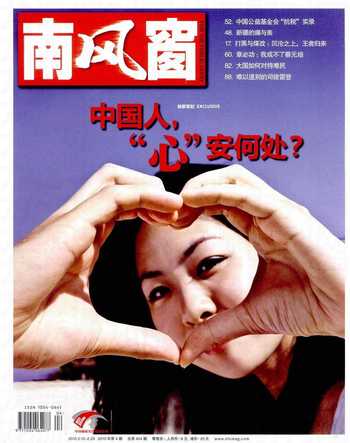誰(shuí)偷走了中產(chǎn)的幸福
甄靜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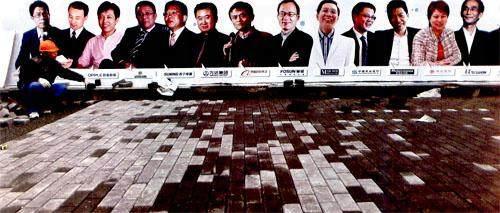
有調(diào)查顯示,中國(guó)70%的白領(lǐng)處于亞健康狀態(tài)。雖然馬上有專(zhuān)家故作輕松地吹著口哨說(shuō),“抑郁只當(dāng)它是個(gè)感冒。”但抑郁到跳樓自殺的人學(xué)歷越來(lái)越高,身份越來(lái)越“中產(chǎn)”。
每當(dāng)華燈初放,霓虹迷離閃爍,屬于都市夜歸族的“生活”才剛剛從暮色中開(kāi)始。Diaan總愛(ài)在加完班的夜晚走進(jìn)深圳那一間間藏在城市迷人燈光下的酒吧,三五同伴推杯換盞,無(wú)非為卸下白天的疲憊和面具。
曾記得1980年特區(qū)成立之初,深圳不過(guò)是大鵬灣畔一小鎮(zhèn),生活悠閑而不起眼。然30年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飛速發(fā)展,北京、上海、廣州、杭州等大城市爭(zhēng)相崛起,作為改革開(kāi)放的窗口,這個(gè)昔年小鎮(zhèn)也成為了高樓林立的都會(huì)。
人們安居樂(lè)業(yè)的心態(tài)被力爭(zhēng)上游的激情所取代。30年間,無(wú)數(shù)人從農(nóng)村涌入城市,又有無(wú)數(shù)人躋身于公務(wù)員、高級(jí)白領(lǐng)、知識(shí)分子、職業(yè)經(jīng)理人等都市新興群體,享受著經(jīng)濟(jì)騰飛帶來(lái)的翻天覆地的都市生活變化。
急奔猛趕的過(guò)程中,沒(méi)人留意燈火璀璨的繁華都市何時(shí)開(kāi)始變成了不夜城。只有當(dāng)醺醺然回到居所時(shí),夜歸的人才清楚體味到,肆意歡愉留給心靈的,是更深的空虛和寂寞。
“中產(chǎn)”的焦慮
截至2008年,北京CBD及周邊集中了朝陽(yáng)區(qū)85%的世界500強(qiáng)投資企業(yè),這里的甲級(jí)寫(xiě)字樓月租金超過(guò)50美元,平方米,堪比紐約。2005年,高林應(yīng)聘一家外企,成為在北京國(guó)貿(mào)大廈上班的高級(jí)白領(lǐng)之一。CBD的繁華,被摩天大樓改變的城市天際線,曾給他以幻覺(jué),仿佛這里離曼哈頓的輝煌已不遠(yuǎn)。
事實(shí)上,中國(guó)復(fù)制了西方國(guó)家的繁華都市后,這幾年又開(kāi)始復(fù)制—個(gè)社會(huì)群體概念——中產(chǎn)階級(jí)。
普遍認(rèn)為,看一個(gè)國(guó)家的發(fā)展水平和富裕程度,不僅看GDP,更重要是看中產(chǎn)階級(jí)的規(guī)模。橄欖型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典型的美國(guó),中產(chǎn)已成為社會(huì)主流,占人口總量80%;與之相比,中國(guó)的中產(chǎn)階層層是否已經(jīng)形成規(guī)模還未有定論,中國(guó)社科院研究結(jié)論顯示,目前中國(guó)中產(chǎn)階層約為總?cè)丝诘?3%左右,處于金字塔結(jié)構(gòu)社會(huì)的中上層,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他們是城市精英的代表。
為了實(shí)現(xiàn)大都市的“中產(chǎn)夢(mèng)”,這些年高林并沒(méi)有少努力。
“以前總夢(mèng)想有天能衣著講究驅(qū)車(chē)進(jìn)出CBD,特別有沖勁去闖。”都說(shuō)中國(guó)的寫(xiě)字樓是全世界最累的寫(xiě)字樓,在西方國(guó)家,老板拿出雙倍加班費(fèi)也很難請(qǐng)求員工留下來(lái)加班;但在中國(guó),像高林這樣的白領(lǐng)很少質(zhì)疑面前堆積如山的工作量是否合理,自發(fā)加班是一種美德——即便沒(méi)有加班費(fèi)已成為潛規(guī)則。
人成為了職場(chǎng)上不眠不休、高速運(yùn)轉(zhuǎn)的機(jī)器,好處是有能力的人盡展所長(zhǎng),短時(shí)間內(nèi)就可以向更高的社會(huì)地位靠近;后遺癥則是,一步步向上游奮進(jìn)后,發(fā)現(xiàn)上游之上總是還有上游,預(yù)期的滿足感難以在心靈長(zhǎng)久駐留。
2005年踏進(jìn)國(guó)貿(mào)大廈,高林非常興奮;2006年,全新的工作和生活被納入按部就班的軌跡;2007年后,他開(kāi)始感到焦慮。“在國(guó)貿(mào)上班又如何?開(kāi)奧迪又如何?”他反問(wèn)自己。依然是日復(fù)一日的加班,不同的只是面對(duì)更嚴(yán)苛的競(jìng)爭(zhēng)和淘汰制度,心惶惶然。
工作至上的觀念幾乎毀掉了他的所有生活空間,結(jié)果,物質(zhì)和社會(huì)地位仍不過(guò)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透支健康,透支情感,透支生活,那到底是為了什么?”
價(jià)值裂變的時(shí)代
這樣的故事正符合臨床心理學(xué)家胡紀(jì)澤在《中國(guó)人的焦慮》一書(shū)中揭示的事實(shí):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和現(xiàn)代化的進(jìn)程越深入,人們的焦慮越嚴(yán)重。
高林的困惑幾乎是城市精英們打拼階段必經(jīng)的心路歷程,他們是公務(wù)員、知識(shí)分子、高級(jí)白領(lǐng)、職業(yè)經(jīng)理人和中小企業(yè)家。
“當(dāng)一個(gè)社會(huì)群體的自我價(jià)值認(rèn)同普遍出現(xiàn)問(wèn)題時(shí),焦慮和抑郁總是最早出現(xiàn)。如果沒(méi)有調(diào)適好,情況就會(huì)進(jìn)一步演化。”臺(tái)灣著名心理學(xué)家許宜銘預(yù)言。
現(xiàn)今,美國(guó)城市里每3個(gè)人里就有1人有抑郁的傾向。雖然中國(guó)沒(méi)有具體的數(shù)據(jù),但我們看到的是,美國(guó)經(jīng)濟(jì)發(fā)展是緩慢漸進(jìn)的,同時(shí)伴隨有兩三百年的西方民主進(jìn)程;而中國(guó)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卻有著突飛猛進(jìn)的特點(diǎn),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的價(jià)值體系在改革開(kāi)放大潮中迅速瓦解,西方價(jià)值觀和后現(xiàn)代思潮猛烈沖擊著傳統(tǒng)的東方價(jià)值觀,卻又來(lái)不及建構(gòu)出新的價(jià)值體系。
在價(jià)值觀轉(zhuǎn)變和心理調(diào)適都跟不上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步調(diào)下,我們僅用30年時(shí)間來(lái)消化西方國(guó)家300年的價(jià)值裂變和心理沖突,中國(guó)人的焦慮和抑郁當(dāng)然更嚴(yán)重。
有調(diào)查顯示,中國(guó)70%的白領(lǐng)處于亞健康狀態(tài)。雖然馬上有專(zhuān)家故作輕松地吹著口哨說(shuō),“抑郁只當(dāng)它是個(gè)感冒”,但抑郁到跳樓自殺的人學(xué)歷越來(lái)越高,身份越來(lái)越“中產(chǎn)”。
“這是價(jià)值觀轉(zhuǎn)變必然產(chǎn)生的陣痛。”許宜銘說(shuō),“從新中國(guó)建立到改革開(kāi)放前,中國(guó)以道德與政治立場(chǎng)為標(biāo)準(zhǔn)的價(jià)值體系一直是很穩(wěn)定的。直到1980年代后,這個(gè)標(biāo)準(zhǔn)受到極大沖擊,社會(huì)重心轉(zhuǎn)變?yōu)橐越?jīng)濟(jì)建設(shè)為導(dǎo)向。”
以往,社會(huì)認(rèn)為個(gè)人價(jià)值應(yīng)該建立在為人民服務(wù)、為大眾犧牲的精神上,當(dāng)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迅猛發(fā)展,資本主義價(jià)值觀沖擊原有價(jià)值體系時(shí),社會(huì)認(rèn)可的個(gè)人價(jià)值又轉(zhuǎn)而與財(cái)富及社會(huì)地位捆綁在一起。
割裂性的轉(zhuǎn)變就這么發(fā)生在一代人身上。
心靈危機(jī)
“人的內(nèi)在有一股原始動(dòng)力,需要證明自己存在的價(jià)值。”
“一個(gè)人真正的自我價(jià)值感是being,我是什么,我對(duì)自己的接納度。但中國(guó)人從不被教育自我接納,相反,我們的文化認(rèn)為,如果你只是你自己,必然不夠好,你必須要成為一個(gè)如何如何的人才夠好。”所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xué)不知義”,本質(zhì)就是把社會(huì)化后的人的價(jià)值放在其本性之上。
也許高林們的“中產(chǎn)夢(mèng)”根本不是他們自己的夢(mèng),只是時(shí)代強(qiáng)加于其身上的一個(gè)“畫(huà)餅”,但他們這般苦苦追逐半生,甚至沒(méi)有想過(guò)為什么。
在西方國(guó)家,有越來(lái)越多的父母對(duì)孩子說(shuō),“你很棒,只因?yàn)槟闶悄悖悴恍枰衔覍?duì)你的期待,也不需要跟那個(gè)第一名相比,你只要是你自己,你就是我最?lèi)?ài)的。”而中國(guó)的孩子從小到大聽(tīng)到的依然是“你看看別人做得多好”。身處這樣一個(gè)社會(huì)價(jià)值觀劇烈變化和沖突的時(shí)代,缺乏自我認(rèn)同教育的國(guó)人難免會(huì)陷入內(nèi)心價(jià)值感的混亂當(dāng)中,進(jìn)而隨波逐流。
于是,在新舊價(jià)值體系的沖突當(dāng)中,老一輩的官員和知識(shí)分子為是否背棄原有的價(jià)值觀下海創(chuàng)富而經(jīng)歷著痛苦的內(nèi)心沖突;無(wú)數(shù)急于證明自身價(jià)值的年輕人則匆忙扎進(jìn)社會(huì),努力按照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標(biāo)準(zhǔn)打造自身。
這當(dāng)然是個(gè)危險(xiǎn)的狀況。人們耗盡心力追求財(cái)富地位,以為可以帶來(lái)安全感和幸福感,殊不知這些價(jià)值認(rèn)同始終依附在外部世界上,越是將個(gè)人價(jià)值牢牢捆綁在物質(zhì)財(cái)富上,越是不安全。因?yàn)橐坏┦チ诉@些東西,人就一無(wú)是處。
2008年金融危機(jī),對(duì)中產(chǎn)階層的自我價(jià)值感無(wú)疑是個(gè)嚴(yán)酷打擊。中小企業(yè)主面臨資金鏈斷裂、停產(chǎn)、倒閉;高級(jí)白領(lǐng)對(duì)無(wú)薪假期,降薪,甚至失去高薪厚職的危機(jī)
束手無(wú)策。
有人開(kāi)始點(diǎn)算未來(lái),這一算,中產(chǎn)階層的優(yōu)越感更是蕩然無(wú)存:職場(chǎng)上再優(yōu)厚的待遇總跟不上物價(jià)上漲,不完善的社會(huì)保障制度讓人看不清未來(lái),醫(yī)療、教育和失控的房?jī)r(jià)“新三座大山”成為了無(wú)休止掠奪中產(chǎn)階層的手段……其實(shí),最讓他們彷徨的并不是個(gè)人經(jīng)濟(jì)真的面臨困境,而是發(fā)現(xiàn)之前盡全力拼搏得到的一切竟是那么脆弱,隨時(shí)可能失去。
“煩躁、失眠、倦怠……”高林形容著,有毒的情緒具有傳染性,人人都有說(shuō)不出的焦慮。而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由自我價(jià)值危機(jī)引發(fā)的關(guān)系危機(jī)進(jìn)一步侵蝕他們的心靈。
寂寞都市的關(guān)系危機(jī)
Diaan其實(shí)不喜歡深圳,這個(gè)移民城市里每個(gè)人都目標(biāo)明確、步履匆忙。
她任職廣告公司,每周一半以上的日子都在加班。“不,我不喜歡加班,但每個(gè)人都這么干,你只好干得比別人更賣(mài)力,否則就會(huì)被擠下去。”
在公司里,Diaan跟每個(gè)人都談笑風(fēng)生,心里卻筑起防范的籬笆。上班戴著面具,回家孤單一人。加班的夜晚,無(wú)法排遣忙碌后的空虛,她就喚上兩三個(gè)朋友去“泡吧”。然而回家后,倒在床上,孤單的感覺(jué)又涌上心頭。
滿大街都是這樣寂寞的都市白領(lǐng),只是他們?nèi)蔽溲b,輕易看不出來(lái)。
近10年,許宜銘每年花大半時(shí)間呆在中國(guó)大陸,他發(fā)現(xiàn)這里的人與臺(tái)灣有個(gè)很大的差異。“即使兩人之間關(guān)系多么好,內(nèi)心深處始終有一份防范,并不傾心信任。”他相信這與“文革”留給中國(guó)的民族創(chuàng)傷有關(guān)。“‘文革沖擊的是華夏文化的根。兒子檢舉親生父母,學(xué)生批斗自己的老師,這給中國(guó)人深層的人際關(guān)系留下了濃重陰影,影響的將不止是一兩代人。”
在近30年物質(zhì)導(dǎo)向的社會(huì)價(jià)值觀中,人的心理世界何嘗不也被污染得一塌糊涂?“小到一個(gè)家庭內(nèi)部爭(zhēng)家產(chǎn),大到長(zhǎng)三角和珠三角經(jīng)濟(jì)區(qū)域的利益爭(zhēng)奪,物質(zhì)始終放在首位,‘關(guān)系都是被犧牲的。”廣州韋志中心理咨詢中心主任韋志中說(shuō),“親情、友情極度疏離。”
但偏偏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注重人與社會(huì)的連結(jié),從小習(xí)慣了對(duì)比,每個(gè)人都需要透過(guò)別人的認(rèn)同才能獲得存在感。因此,中產(chǎn)需要酒吧,需要各色俱樂(lè)部來(lái)排遣心底的寂寞。
去年,Diaan迷上開(kāi)心網(wǎng),通過(guò)鼠標(biāo)點(diǎn)擊去“偷”好友的菜,本是很無(wú)聊的游戲,但城市精英樂(lè)此不疲。“好友里有醫(yī)生、律師、工程師,還有企業(yè)老板。”這些小游戲?qū)嶋H上是一種透過(guò)網(wǎng)絡(luò)衍生的快餐式心理滿足服務(wù),讓人間接短暫地實(shí)現(xiàn)與他人的連接,從而感覺(jué)到自我存在的價(jià)值。
“不少經(jīng)濟(jì)條件和社會(huì)地位都頗高的精英,正是由于沒(méi)有能力經(jīng)營(yíng)好自己的親密關(guān)系,無(wú)法在群體中感覺(jué)到自己的價(jià)值,最終走上放棄生命的不歸路。”韋志中說(shuō)。
一個(gè)單調(diào)無(wú)聊的網(wǎng)絡(luò)小游戲兇猛流行,竟因切中了都市人關(guān)系危機(jī)的要害。
公務(wù)員的幸與不幸
當(dāng)韋志中鄭重提到,“我們正身處一個(gè)中產(chǎn)階層‘幸福感和自我價(jià)值危機(jī)時(shí)代”時(shí),如果說(shuō)還有相對(duì)淡定的一群人,那就是公務(wù)員群體。
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社會(huì)學(xué)所博士后邢占軍曾對(duì)沿海某省主要社會(huì)群體的幸福感作了詳細(xì)調(diào)研。結(jié)果顯示,在工人、農(nóng)民、公務(wù)員、國(guó)有企業(yè)管理者、知識(shí)分子、新興群體和城市貧民七大群體的綜合幸福感排名中,公務(wù)員的幸福感最高,繼而是城市新興群體和知識(shí)分子;而幸福感最低的是城市貧困群體,其次是農(nóng)民。
從大方向看,中國(guó)人的幸福感水平與收入水平基本成正向關(guān)系,城市貧民、農(nóng)民和工人的幸福感大大低于中產(chǎn)與富有階層;但在幾個(gè)中高收入層次群體內(nèi)部,這一表征卻不明顯。這固然反映了政府在民生與社會(huì)保障上的缺位,無(wú)相當(dāng)收入基礎(chǔ)的國(guó)人很難談得上感受幸福;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以追求物質(zhì)的方式滿足幸福感,在一定社會(huì)群體中仍然有效,只是當(dāng)群體的收入達(dá)到一定層次后,效果不再明顯。
“現(xiàn)今的中國(guó)是一個(gè)多元的社會(huì),影響不同階層幸福感的因素也各不相同。”韋志中以物質(zhì)財(cái)富追求的幸福閾限說(shuō)來(lái)分析這個(gè)現(xiàn)象,“當(dāng)實(shí)際的物質(zhì)條件跟通過(guò)物質(zhì)獲得幸福感的心理閾限差距越大時(shí),物質(zhì)帶來(lái)的幸福感振蕩會(huì)越大;而一旦接近這個(gè)閾限,物質(zhì)財(cái)富增加對(duì)幸福感的影響就越來(lái)越小,最終失去感覺(jué)。”
“幸福感嚴(yán)格來(lái)說(shuō)是一個(gè)完全主觀的概念。”邢占軍說(shuō),這些年公務(wù)員群體一直在各類(lèi)幸福感調(diào)查中高居幸福水平首位,與其實(shí)際收^并無(wú)必然關(guān)系。
“穩(wěn)定、福利好大概是公務(wù)員對(duì)現(xiàn)狀普遍滿意的重要原因。”今年31歲的楊邁在廣東某市級(jí)財(cái)政單位呆了8年。要談公務(wù)員的“幸福”,他有點(diǎn)無(wú)奈。“考上公務(wù)員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風(fēng)光,別人在為事業(yè)拼搏、跳槽的時(shí)候,我8年如一日領(lǐng)一份白領(lǐng)級(jí)的工資,沒(méi)升過(guò)職、沒(méi)調(diào)過(guò)崗,現(xiàn)在還是底層科員。”
楊邁形容公務(wù)員是一眼能望到頭的職業(yè)。“不會(huì)暴富,也餓不死。你浮躁也沒(méi)有用,奮力拼搏也不太使得上勁。只能放慢步伐,慢慢來(lái)。沒(méi)有太高的期望,就少點(diǎn)失望和焦慮。”快與慢
“放慢步伐,慢慢來(lái)”,也許就是“幸福”與“不幸福”的分野。
“當(dāng)物質(zhì)滿足到達(dá)幸福閾限,放慢腳步,停下來(lái)思考、轉(zhuǎn)型,將工作的目的從‘物質(zhì)追求向‘享受過(guò)程轉(zhuǎn)變,那么真正屬于自我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的目標(biāo)就呈現(xiàn)了。”韋志中表示,這樣的目標(biāo)聽(tīng)似很空泛,卻可以與現(xiàn)實(shí)工作緊密地結(jié)合起來(lái)。
“我的目標(biāo)是使更多人因心理學(xué)而受益。那么這兩年我就大幅減少心理咨詢個(gè)案的接待,轉(zhuǎn)而做更多的社會(huì)研究和教育工作,建立免費(fèi)心理咨詢熱線。又如一個(gè)建筑設(shè)計(jì)師,可以把目標(biāo)由賺更多的錢(qián),轉(zhuǎn)變?yōu)樽尭嗳私邮茏匀弧⒑椭C、宜居的概念,把這個(gè)目標(biāo)融入自己的設(shè)計(jì)當(dāng)中。”
一個(gè)人的精神痛苦程度往往就是現(xiàn)實(shí)自我與理想自我的差距。更何況東方文化向來(lái)有自我施壓的傳統(tǒng),什么臥薪嘗膽,什么頭懸梁、錐刺股,目標(biāo)遠(yuǎn)大,心理脆弱,一旦目標(biāo)與現(xiàn)實(shí)失衡,就是災(zāi)難性的打擊。
外企和廣告公司的拼搏、追求和快節(jié)奏,讓白領(lǐng)們沒(méi)有時(shí)間停下來(lái)思考,相繼陷入自我價(jià)值和人際關(guān)系的心理危機(jī)之中:公務(wù)員的慢,卻讓楊邁有時(shí)間調(diào)整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的合理距離,避免卷入焦慮的漩渦——當(dāng)然,這也不過(guò)是僅限基層公務(wù)員的小“幸福”罷了。
無(wú)可否認(rèn)的是,中國(guó)經(jīng)濟(jì)依然在飛速發(fā)展,也需要繼續(xù)保持騰飛的速度,中國(guó)社會(huì)慢不下來(lái),作為最具創(chuàng)造性和拼搏精神的城市精英代表的中產(chǎn)階層也不可能真正慢下來(lái),他們只會(huì)嫌自己不夠快。
也許焦慮和抑郁還會(huì)繼續(xù)像感冒似地蔓延,直到中國(guó)有足夠的時(shí)間消化掉轉(zhuǎn)型期的精神陣痛。但這樣的精神轉(zhuǎn)型,更像是聽(tīng)天由命的時(shí)代。有人轉(zhuǎn)型成功,從此笑傲江湖;有人變成了患者,走進(jìn)精神病院;更有人縱身一跳,了斷了自我。
“然而時(shí)代的發(fā)展不容許聽(tīng)天由命。所以接下來(lái)幾年,最可能是中國(guó)宗教和心理學(xué)大發(fā)展的時(shí)期。焦慮的人群需要積攢心理資本,尋找精神信仰的方向和心靈的皈依。”韋志中表示,“而中產(chǎn)階層作為未來(lái)社會(huì)的中流砥柱,也需要有堅(jiān)定的精神信仰,以及對(duì)生命本質(zhì)的辯證思考能力。才能保證社會(huì)發(fā)展不會(huì)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