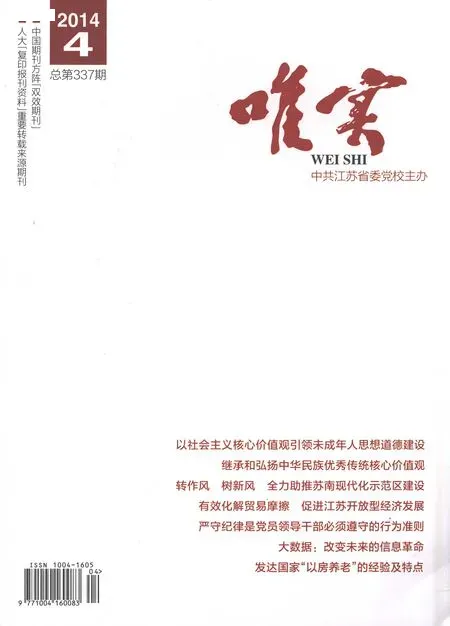文本對象與文本意義雙重致思維度的統(tǒng)一
——也談“如何回到馬克思”
崔永和
(吉首大學(xué) 哲學(xué)研究所,湖南 吉首 416000)
文本對象與文本意義雙重致思維度的統(tǒng)一
——也談“如何回到馬克思”
崔永和
(吉首大學(xué) 哲學(xué)研究所,湖南 吉首 416000)
文本是作者用于傳達(dá)本人思想的客觀存在,雖然是不以讀者意識為轉(zhuǎn)移的特殊定在,但是它之所以成為文本對象的本質(zhì)規(guī)定,就在于它是對象性存在,即一方面是作者的對象性存在,另一方面是讀者的對象性存在;而文本意義則是讀者與作者思想相遇的產(chǎn)物,是讀者與作者“合作”的思想過程或結(jié)果。在這里,離開了作者的文本,也就脫離了文本的意義旨?xì)w;而離開了讀者的能動選擇和重新創(chuàng)構(gòu),就談不上對文本的意義解讀。因此,文本是靜態(tài)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文本意義則是流動的、多樣的、差異紛呈的。
文本對象;文本意義;致思維度
一、文本與文本解讀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
文本是作者用于傳達(dá)或宣示自己意圖和思想的創(chuàng)造成果,因此,文本實質(zhì)上是依托于一定載體的精神存在。但是,文本作為對象性的存在,它一方面是作者本質(zhì)力量的外化或?qū)ο蠡?具有客觀性、特殊性、唯一性或不可替代性,獨立于讀者的意識之外,相對于讀者及其主體意識來說具有優(yōu)先性;另一方面,優(yōu)先于讀者及其主體意識的文本并非永遠(yuǎn)地或絕對地外在于讀者而獨立存在,相反,文本一旦成為讀者的選擇對象而被讀者所實際地選擇和解讀,就必然與讀者的主體意識及其認(rèn)知能力、思維方式、實踐能力和價值選擇能力彼此相互關(guān)聯(lián),具有主體性、實踐性、多樣性或一定的社會生活特質(zhì)。因而,不能把文本視為與讀者無關(guān)的或者外在于讀者的純粹的“客觀存在”,因為一切外在于人的客觀存在都是意義世界之外的不可言說,是“無”。
實際上,文本一經(jīng)被作者創(chuàng)造出來并進入社會歷史領(lǐng)域,它就不再是專屬于作者個人的孤立存在,而成為溝通作者與社會、作者與讀者、作者與歷史的現(xiàn)實中介,它既是作者人生價值生成過程的歷史延續(xù),又是讀者實際發(fā)揮主體意識創(chuàng)造或主觀能動性的客觀依據(jù)。于是,從文本出發(fā),便同時生發(fā)出作者與讀者雙重主體活動的彼此對接與思想交會,即是說,文本作為現(xiàn)實的對象性存在,既不專屬于作者,也不專屬于讀者,而是作者與讀者所共同擁有的對象,是作者的文本維度與讀者的解釋維度具體的歷史的統(tǒng)一。這里存在一個如何全面看待文本及文本意義的方法論問題。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曾經(jīng)批評過一種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的片面方法,他指出:“日常的理智和具有這種理智的大多數(shù)自然研究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作永遠(yuǎn)互相排斥的兩個規(guī)定。一件事物、一種關(guān)系、一個過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兩者兼而有之。”[1]如何正確把握文本及文本意義,它究竟是由作者賦予的,還是由讀者賦予的?對于科學(xué)思維和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思維來說,這個問題只能有一種回答,即要么是前者,要么是后者,而斷然不能是二者“兼而有之”。然而,事實上,在這里卻恰恰存在作者與讀者“兼而有之”的關(guān)系,即文本意義是作者與讀者所共同賦予的。
近來,有論者把張一兵的兩部著作(《回到列寧》與《回到馬克思》)的不同理解范式加以比較之后,認(rèn)為:“‘回到馬克思’的解釋學(xué)立場,肯定理解既然有客觀的對象,理解的目的和結(jié)果便是把握文本的意義或作者的思想”,“而‘回到列寧’的解釋學(xué)立場,認(rèn)為理解的對象是由理解主體建構(gòu)起來的,文本沒有自身固有的不變的意義,文本的意義是由讀者賦予的,文本的意義隨著讀者的變化而變化”,據(jù)此便得出結(jié)論:《回到列寧》較之《回到馬克思》,是一個“后退”[2]。在這里,從《回到馬克思》到《回到列寧》,其解讀方式究竟是“退步”,還是“進步”?只要正視文本與文本解讀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尊重文本解讀的真實邏輯行程,那么,正確的答案顯然不是前者,而是后者,是進步,而不是退步。
按照哲學(xué)解釋學(xué)的觀點,解讀本身不僅是讀者對文本的理解與繼承,而且是讀者在文本基礎(chǔ)上的重構(gòu)與創(chuàng)新。例如,在伽達(dá)默爾看來,解讀活動中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諸如成見的限度、理解不可還原對象、理解不可窮盡對象等情況,其中透射出哲學(xué)解釋學(xué)的原則與范式的主觀創(chuàng)造性本質(zhì)。正如有學(xué)者早就指出的那樣:“理解不是追求作者的原意,而是通過‘視界融合’去擴大意義和尋找新的意義的過程,實際上是人的世界經(jīng)驗的基本模式。”[3]面對文本,如果單方面用“客觀性”原則來規(guī)定文本解讀,那就必然在所謂的尊重文本和尊重作者原意的原則下使解讀過程成為鸚鵡學(xué)舌式的重復(fù)思維,甚至令解讀蛻變?yōu)榻虠l主義的文本搬家的模仿思維、刻板思維或“剽竊思維”。如果在尊重文本、尊重作者原意的基礎(chǔ)上,同時兼顧和尊重讀者所置身于彼此差異和實際變化了的具體歷史條件,兼顧和尊重讀者的價值選擇和能動創(chuàng)造,那么文本意義就必然是一個多樣化的差異紛呈的思維過程。這樣一來,多元化創(chuàng)新的文本意義就既包含作者的原意,又包含讀者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由此看來,《回到列寧》較之《回到馬克思》就不僅不是什么“退步”,而且是一個可貴的、具有時代創(chuàng)新意義的進步。
文本解讀實質(zhì)上是讀者的精神生產(chǎn)過程,不過,這種精神生產(chǎn)活動是站在作者的肩膀上、以文本作為先在前提和客觀參照,構(gòu)建出一個特殊的中介情境(有人稱之謂“構(gòu)境”也未嘗不可),這個中介是作者與讀者的思想交流與意義對接的橋梁,是作者的歷史時代與讀者的社會實踐相互參照、相互影響與相互作用的橋梁,是作者的生活情境與讀者的生活情境彼此比較與溝通的橋梁。通過這樣的中介,一方面,繼續(xù)延伸著作者思想的歷史價值,另一方面,生成著讀者的思想意圖和生活情境,從而引領(lǐng)、創(chuàng)造和豐富著讀者所置身于其中的社會生活,更新著歷史時代的步伐。這種現(xiàn)實構(gòu)境是讀者的創(chuàng)造,同時,也內(nèi)含著作者的貢獻(xiàn)。
二、有沒有一成不變的文本意義?
對文本的基于實踐經(jīng)驗的解讀,既不能沒有邏輯,也不能沒有領(lǐng)悟,但從思維活動的實際運思過程來說,領(lǐng)悟比邏輯更重要。對于文本意義的領(lǐng)悟常常是基于生活的歷史變遷、基于讀者主觀創(chuàng)造的多樣化價值選擇過程,因此,一切文本意義就必然是多變而常新的,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僵死教條。
我們強調(diào)讀者解讀文本過程中的創(chuàng)新意義,但這決不等于說讀者對文本的解讀可以隨心所欲,相反,它必須遵循以下基本的解讀原則:
第一,尊重文本的原則。解讀既然是讀者對文本的重新理解和領(lǐng)悟,那么文本作為解讀對象就是首要的前提和依據(jù),離開文本和作者原意去想當(dāng)然地自說自話,就失去了解讀的基本規(guī)定,或者不再能被稱為解讀,甚至不客氣地說,這種所謂的解讀就等于篡改。例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用如下的名言表達(dá)了他們的歷史觀:“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chǎn)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lián)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4]面對這一經(jīng)典文本表述,我國學(xué)術(shù)界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一種解釋認(rèn)為,此處的文本原意在于強調(diào)只有社會(即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發(fā)展了,才能有個人的自由發(fā)展,因此,社會的發(fā)展是個人發(fā)展的前提、依據(jù)和目的;另一種解釋則與之相反,認(rèn)為此處的文本原意是強調(diào)“每個人自由發(fā)展”的優(yōu)先地位,在此條件下,才談得上社會的發(fā)展,即是說,個人的發(fā)展是社會發(fā)展的前提、依據(jù)和目的,兩種不同的解釋一直延續(xù)和影響至今。這里的關(guān)鍵顯然在于如何正確理解“個人”與“社會”、“每個人”與“一切人”的關(guān)系問題。這里的“每個人”并非指少數(shù)個別的或特殊的“個人”,而是指所有實際存在的個人,或者說,是一切從事實際活動的個人。于是,當(dāng)現(xiàn)實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毫無例外、不分高低貴賤地得到了自由發(fā)展時,社會也就有了發(fā)展的現(xiàn)實條件或根基。這就意味著,一旦每個人都得到了自由發(fā)展,與一個個具體的、特殊的個人相對應(yīng)的一般意義上的“一切人”或社會自然而然地就會得到發(fā)展。顯然,前一種解釋違背了文本原意,因為它把社會當(dāng)作個人棲身的依賴,甚至把個人當(dāng)作毫無個體能動性、難以脫臍于社會的消極附屬物;后者堅持了文本原意,因為它在人與社會的關(guān)系中堅持了人是社會的主體和能動性根基,堅持了人是目的的原則,這不僅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從事實際活動的人”的理論出發(fā)點,而且遵循了這樣的歷史邏輯:“要不是每一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也不能得到解放。”[5]644
第二,立足現(xiàn)實的原則。任何文本都不是靜止不動的定在,而是具有歷史流動性的思想資源。在人類歷史的實際行程中,常常會出現(xiàn)任何文本都難以窮盡的、受隨機因素影響的新情況。這時候就要求讀者根據(jù)自身所面臨的實際境遇來解讀文本,進行適合自己生活需要和價值選擇的創(chuàng)造或重構(gòu),對文本作出重新理解并賦之以新的意義。于是,文本的某些原意或者會隨之而被放大,或者隨之而被縮小,或者隨之而被修正和發(fā)展……,總之,在這里將會充分展現(xiàn)讀者對于文本解讀的時代特點和生活意義。正是在文本不可能把握或窮盡歷史的隨機因素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文本不僅不可能剪裁未來的社會實踐和人的現(xiàn)實生活,不可能嚴(yán)格規(guī)定或制約讀者的思想,相反地,卻注定要被變化著的現(xiàn)實生活所改變,被讀者所重構(gòu),但這又決不意味著文本和文本意義的消失,而是以不斷變化著的內(nèi)容和形式延續(xù)著特定的文本及文本意義。誠如恩格斯所曾經(jīng)指出的那樣:“至于說到每一個人的思維所達(dá)到的認(rèn)識的至上意義,那么我們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談不上的,而且根據(jù)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經(jīng)驗看來,這些認(rèn)識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東西,無例外地總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確的東西多得多。”在這個原則面前,任何作者都莫能例外。如果有人宣布自己已經(jīng)創(chuàng)造出或掌握了萬古不變的文本或“永恒真理”,那就等于“實現(xiàn)了可以計數(shù)的數(shù)不盡的數(shù)這一著名的奇跡”[5]427。可見,雖然作者和文本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但卻不是不可以超越的,所謂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長青。
第三,革命批判的原則。馬克思主義理論創(chuàng)立的價值追求和歷史使命在于使整個現(xiàn)存世界革命化,從理論上為人的解放創(chuàng)造條件、指明道路。為此目的,對馬克思的文本解讀就須堅持辯證的革命批判原則和方法:“在對現(xiàn)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xiàn)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xiàn)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zhì)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馬克思的文本從來不是供人固守或迷信的教條,其文本意義只是在實踐中、在讀者的解釋中不斷更新的思想過程。文本是創(chuàng)造,對文本的解釋也是創(chuàng)造,但卻都無不具有暫時性和相對性,因而都不是最終的、最后的或不可超越的創(chuàng)造。于是,在人類思想的歷史過程中,無論是文本還是文本解讀,都是特定的思想環(huán)節(jié),它既繼承和吸收已有的思想成果,又為人類思想的演進提供特殊的思想成分和創(chuàng)新成果。
著名哲學(xué)解釋學(xué)家伽達(dá)默爾曾經(jīng)指出:“不應(yīng)該把理解設(shè)想為好像是人的主觀性行動,理解是將自己置身于傳統(tǒng)的一個過程之中,在這過程中過去和現(xiàn)在不斷地融合。”[7]258可見,面對文本的讀者,并非置身于文本之外的消極靜觀的旁觀者,而是主動參與文本之中,在重新體驗和重構(gòu)文本構(gòu)境的實際生活與現(xiàn)實活動中,成為能動地傳承文本原意和創(chuàng)構(gòu)文本新意相統(tǒng)一的特定主體。按照這樣的思維邏輯行程,任何對于文本的真正解讀都必然地內(nèi)含著文本的意義指向和意義對象。伽達(dá)默爾曾經(jīng)借助于對語言的分析,透視人與對象世界的關(guān)系,他認(rèn)為,語言是理解得以普遍實現(xiàn)的媒介,它既規(guī)定了理解對象,又規(guī)定了理解活動本身,從而語言本身就從交往工具而成為人的存在的一種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說,讀者怎樣解讀,怎樣言表,也就怎樣生活;同時,每一種語言又因為能夠帶給人一種對于世界的特定態(tài)度和關(guān)系,所以“在每一種世界觀里都蘊含了世界自身的存在”[7]404。因此,文本意義無論經(jīng)受讀者如何全新的重構(gòu),它都內(nèi)含著而不是完全擺脫文本自身的意義旨?xì)w。
三、文本意義的生命力何在?
一般說來,文本是關(guān)于實踐經(jīng)驗的理論總結(jié),因此,文本及文本意義就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tǒng)一。與之相對應(yīng),不同的讀者對于同一文本就既可能有彼此一致的共識,又可能有各自獨特的解讀內(nèi)容。比如,由于馬克思創(chuàng)造了享譽世界的文本,所以逝世百年后的馬克思在世界思想家排名中仍然屢次居于榜首,體現(xiàn)了不同的人群對馬克思一致的肯認(rèn),但這并不妨礙不同的人們對馬克思的文本作出彼此存有差異的解讀。事實上,不同的讀者對于同一文本的不同解讀,那是歷史上和現(xiàn)實中常有的事,而一切理論的分歧和爭論的是非問題只有在不斷的社會實踐中才能夠逐步地得到澄清或解決。
對于作者說來,文本意義是作者的歷史價值的表征,是作者不在場的特殊“出場”,是作者借助于讀者的解讀實現(xiàn)自己的思想、意圖和人生價值的歷史過程。作為思想家的馬克思,其文本的邏輯定格既非亞里士多德式的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思維,也非黑格爾式的唯心辯證思維,而是基于人的對象化實踐活動過程的解釋性思維,這種特定的思維范式以“從事實際活動的人”為出發(fā)點,從而把人看成能動的實踐主體。這就是自洽的或自我規(guī)定的能動存在,而這種能動存在的生成過程既包含客觀的物質(zhì)性的創(chuàng)造因素,也包含主觀的精神性的創(chuàng)造因素;他的文本不是關(guān)于有限性問題的科學(xué)思維,而是關(guān)于無限性問題的觀念思維;它所提供的不是解決具體問題的知識,而是引導(dǎo)人們不斷創(chuàng)新的思想資源。因此,在馬克思文本的解釋面前,便為人們留下了充分而廣闊的主觀創(chuàng)造空間。
一定文本的生命力主要取決于以下因素:其一,文本的文化神韻。這是文本具有歷史穿透力和積極引導(dǎo)作用的重要條件。其二,文本的理論覆蓋面。這是文本之所以能夠被多數(shù)人選擇的本質(zhì)規(guī)定,正如同“月映萬川”的“月”須有“光明”才能夠在萬川中得到映照一樣。其三,文本意義的多樣化解讀。文本只要能夠不斷地得到讀者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選擇、重構(gòu)和解讀,這便是它不絕的生命力之所在的根本原因。馬克思文本意義的生命力從根本上說取決于人們在自己的社會實踐中對它的選擇、重新理解和重新創(chuàng)造。由此說來,馬克思文本的生命力不在于把文本當(dāng)作一成不變的教條一味地向人們灌輸,而在于文本是否能夠被人們所選擇,是否能夠隨著歷史的行程而繼續(xù)內(nèi)在于人的實踐和生活,是否能夠融入現(xiàn)實人的價值選擇和價值生成的實際行動之中。假如過分地強調(diào)文本的客觀性、過分地突出文本及其文本意義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定在,那么,文本的生命力就必然被規(guī)定為對文本的固守堅持,并為此而致力于把文本的原意外在地向人們灌輸,認(rèn)為這種灌輸?shù)牧Χ仍綇姟⒈还噍數(shù)娜巳阂?guī)模越大、人數(shù)越多,文本就越具有生命力。這種曾經(jīng)長期束縛我們的教條主義的解釋方法不是把馬克思的文本當(dāng)作探索未知、不斷解決新問題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資源,而是視之為可以到處解決具體問題的萬應(yīng)靈藥或具體知識,從而用科學(xué)主義的知識論思維范式扭曲馬克思的文本及其文本意義,窒息了人的主觀創(chuàng)造精神。
在泛科學(xué)主義盛行的今天,跟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世界潮流,人們在不知不覺中邁進了工具理性時代。在這里,無論什么理論、學(xué)說,都要在經(jīng)濟的天平上接受審視,經(jīng)受“是否有用”的經(jīng)濟標(biāo)準(zhǔn)的裁決。然而,馬克思的文本意義是不可證實的,可證實的不是意義,而是科學(xué)。近代以來,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的進步,人們的物質(zhì)生活越來越豐裕,物質(zhì)享受的方式也越來越豐富多彩,人的自然本能不再遭受壓抑,人的官能刺激的需要便越來越能得到預(yù)期的滿足,在這種被譽為“發(fā)達(dá)社會和幸福時代”的情境下,人們“沒有時間進入深層的精神生活,藝術(shù)、哲學(xué)和宗教不再被人需要,也就更沒有人去建設(shè)它們。由此可見,科學(xué)理性不但不能促進人類精神生活的進步,反而是在消滅真正的精神生活”[8]165。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和豐富多彩實際上并不亞于物質(zhì)生活領(lǐng)域,只是在人類歷史的早期和稍往后的時期,由于生產(chǎn)力的低下和物質(zhì)生活資料的極度匱乏,人的自然生理需求常常難以得到滿足而危及到人自身自然生命體的存在,因此,人的活動也就幾乎長期局限于謀生的物質(zhì)生產(chǎn)領(lǐng)域。然而,隨著生產(chǎn)力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需求將逐漸趨于豐富和全面,人的自由發(fā)展的條件將逐漸從主要依賴于物質(zhì)生產(chǎn)領(lǐng)域轉(zhuǎn)向主要依賴于精神活動領(lǐng)域或?qū)徝李I(lǐng)域,這時候,人的精神生產(chǎn)和主觀創(chuàng)造活動將越來越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義。
值得認(rèn)真反思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就是,在人類歷史上的一個相當(dāng)長的時期里,人們對于經(jīng)濟利益和個人經(jīng)濟權(quán)利覺醒的意義曾經(jīng)給予了過高的估價,對于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也曾經(jīng)過多地強調(diào)“社會物質(zhì)財富的極大豐富”的決定性意義。這種估計,如果在欠發(fā)達(dá)社會還有一定的實際意義的話,那么在發(fā)達(dá)社會就值得重新審視了。近代以來的大量經(jīng)驗事實證明,人類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并不與社會物質(zhì)財富的增長成正比,甚至伴隨社會物質(zhì)財富的增長,反而引發(fā)出許多新的社會矛盾和復(fù)雜的社會問題,這也許正是西方世界理論界長期重視分配正義問題的原因之一。
概略說來,馬克思文本的全部意義在于對人的存在方式或活動樣態(tài)發(fā)揮積極的指導(dǎo)作用。然而,在人的存在方式或活動樣態(tài)的實際歷史生成過程中,將始終面臨著難以完全預(yù)見和把握的偶然事件或隨機因素,與此相聯(lián)系,馬克思的文本也將面臨著不同地域、不同國家、不同民族和不同人群彼此差異的選擇與解讀。于是,馬克思文本的歷史延生過程也就是不斷探索未知、破解人生新問題的過程,其中蘊涵著“從主體出發(fā)”、“從人的感性活動出發(fā)”的能動創(chuàng)造的方法論特質(zhì),與此同時,則不斷地排除和超越“從客體出發(fā)”、從既定對象出發(fā)的消極宿命的形而上學(xué)傳統(tǒng)。一百多年來的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充分展示和證明了馬克思文本意義的豐富多彩和眾家紛呈,諸如“西方馬克思主義”、“東方馬克思主義”、“生態(tài)馬克思主義”、“后現(xiàn)代馬克思主義”,等等,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派別都在一定程度上、從一定側(cè)面透射出馬克思文本的特殊意義。馬克思晚年曾經(jīng)認(rèn)為,人在物質(zhì)生產(chǎn)活動領(lǐng)域中所能獲得的自由是極其有限的,而在精神創(chuàng)造和審美領(lǐng)域則存在著未來文明人類無限廣闊的生活空間。“事實上,自由王國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規(guī)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于真正物質(zhì)生產(chǎn)領(lǐng)域的彼岸。”[9]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在解讀馬克思文本的過程中,只有進一步弘揚人的主觀創(chuàng)造精神,才能真正有利于人的生活的全面提升,才能有利于人的全面發(fā)展,從而也才能有利于我們真正尊重馬克思的文本,真正與馬克思交流、對話,真正“回到馬克思”。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24.
[2]王金福.“回到列寧”與“回到馬克思”:兩種對立的解釋學(xué)立場[J].唯實,2009(11).
[3]張汝倫.解釋學(xué)在二十世紀(jì)[J].國外社會科學(xué), 1966(5).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2.
[7]伽達(dá)默爾.真理與方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
[8]張志偉.是與在[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 2001:165.
[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6.
責(zé)任編輯:戴群英
book=32,ebook=149
C31
A
1004-1605(2010)04-0032-05
本文獲湖南省普通高等學(xué)校重點研究基地“差異與和諧社會研究中心”資助。
崔永和(1942-),男,河南清豐人,河南師范大學(xué)教授,吉首大學(xué)特聘教授,碩士生導(dǎo)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唯物史觀、價值哲學(xué)和環(huán)境倫理學(xu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