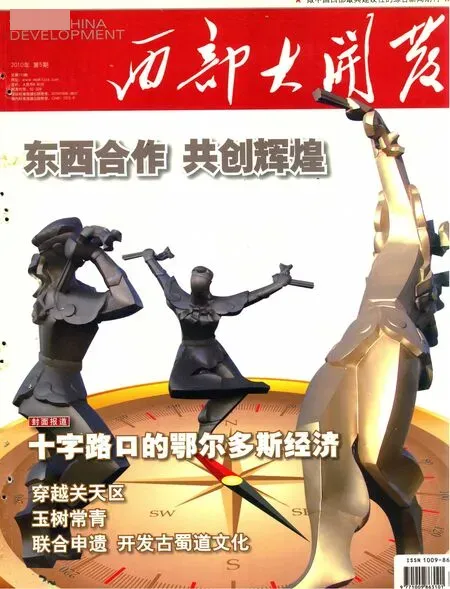十年崛起之路
世界經濟增速最快的是中國,中國增速最快的是內蒙古,內蒙古增速最快的是鄂爾多斯,鄂爾多斯的人均GDP將超過香港。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內蒙古大學校長連輯在第八屆中國企業家領袖年會上表示。
鄂爾多斯地處中國最大的煤炭富集區的核心地帶,這條煤炭帶東起陜西榆林,然后一路向北,經神木、大柳塔,過陜蒙邊界,跨越烏蘭木倫河到內蒙古上灣,折向西縱貫鄂爾多斯全境,直達與阿拉善交界的烏海。幾百公里的狹長區域,是我國最重要的能源走廊。
在鄂爾多斯8.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48%是無法居住的沙漠,而70%的地層下,都埋藏著煤礦。已探明儲量1676億多噸,預計儲量近1萬億噸,約占全國總儲量的1/6。每天,全國煤炭所需總量的1/8就來自鄂爾多斯。除此之外還有7504億立方米的天然氣,約占全國總探明儲量的31.8%。我們每向前走一步,腳下都是財富。
所謂羊(羊絨)煤(煤炭)土(高嶺土)氣(天然氣)構成了鄂爾多斯富足的資源體系。如同大風堆起沙丘,中國經濟大氣候使鄂爾多斯迅速崛起,在短短幾年的時間內積累起了巨大的財富。那些埋藏在地下已經億萬年的黑色礦產,從未像今天這么值錢。在2005到2009年的4年中,它直接推動了鄂爾多斯的發展奇跡——GDP與財政收入都翻了近兩番。GDP從2005年的550億元增長到2009年的2100億元;而財政收入,2005年只有93億元,2009年增長為365.8億元。如果再將時間推至2000年,我們驚奇地發現,鄂爾多斯的經濟總量是在以9年14倍的速度膨脹。
暴富式成長
鄂爾多斯的地名形成于15世紀。蒙古語鄂爾多斯的意思是 “眾多宮殿”。清朝時,這片地區被稱為伊克昭盟,到民國時,下屬的7旗1縣已經沒有一個叫鄂爾多斯的地名了。直到原伊盟羊絨廠改名“鄂爾多斯”,無意間挽救了一段塵封的歷史。
本世紀初,隨著鄂爾多斯羊絨的品牌影響力不斷擴大,羊絨不僅成為內蒙古的一張名片,鄂爾多斯更是成為伊克昭盟的代名詞。2001年2月26日,為發揮這種品牌效應,伊克昭盟更名為鄂爾多斯市。
很長時間以來,鄂爾多斯的羊絨產品成為鄂爾多斯人的送禮佳品。以羊絨起家的鄂爾多斯集團給鄂爾多斯帶來了名聲與榮譽,但真正帶給鄂爾多斯人財富的,是近幾年來興起的“黑金”經濟——煤炭。
但在十年前,當隔壁的山西人已經靠煤炭發家時,多數的鄂爾多斯人還只能依靠草原和羊毛吃飯。那個時候,鄂爾多斯的土地上除了草和沙,一無所有。
鄂爾多斯煤炭業的發展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光緒年間。早在上世紀50年代,這里已經被發現了大規模的煤層,只是囿于當地的開采條件和技術,未能真正大規模開發,50年代初全市只有十幾處小煤礦。
上世紀80年代初,由新華社發出有關本地區發現巨大煤海的信息后,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鄂爾多斯依舊寂寂無名。中央大型企業更多選擇了山西與東北作為能源基地,規模化開采。因為這兩個地區距離工業中心更近,交通也更便利。
“8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了‘有水快流、大中小并舉’的發展策略,地方民營煤礦開始大量出現。” 鄂爾多斯煤炭局辦公室主任郝建軍回顧說。但當時煤礦規模很小,大的也只有十幾萬噸,大量由私人投資的鄉鎮煤礦是開采主體。地方政府難以爭取到中央大企業的進駐,更多的是鼓勵本地企業發展。本地煤炭巨頭伊泰集團董事長張雙旺,就是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放棄副處長的職位下海創業。他從政府借款5萬元,從銀行貸款30萬元,帶領30名冗員自謀出路。而政府唯一指望的就是,他能夠把5萬元借款還上,并且把政府分流人員養活。
當地官方稱,2000年之前,鄂爾多斯轄區內小煤窯和被稱作“饅頭窖”的土煉焦爐子,遍布山溝和河灘。高峰時期,這些小煤窯曾多達1901座,年產量不足9萬噸的占到了95%以上。
這種相對落后的發展狀態,形成一段時間內的央企真空。反倒使鄂爾多斯的私營煤炭企業勢力強大,后期改制也更加徹底。并陸續培育出了伊泰、億利、伊東、匯能、烏蘭、滿世等地方大型礦企。這與山西中央企業主導的產業格局有較大不同,使得此后鄂爾多斯財富的民間化程度也更高。“2009年全市產煤3.3億噸,其中2.1億噸是本地民營企業開采的,只有1.2億噸由央企神華集團開采。”郝建軍說。
隨后中國最大的國有煤礦企業——神華集團的入駐,為鄂爾多斯的煤業發展推波助瀾。神華集團到來之后,合并整治小煤窯成為當地政府的首要行動之一。而神華集團開礦筑路,也給當地帶來了完整的煤礦產業鏈。后來神華集團的觸角更是伸入了鄂爾多斯經濟的多個角落——從煤礦開采到洗煤、運輸、銷售,從商場到酒店、到房地產開發。
2003年之前煤炭的價值并沒有很快顯現,隨著中國經濟進入一輪爆發周期,尤其是以重工業、重化工業為代表的二次工業化發展迅速,對能源需求日益強烈,東部城市拉閘限電嚴重。中國的煤炭行業也迎來巨大轉機,煤炭價格急劇攀升。
鄂爾多斯人腳下的黑煤開始變成“黑金”。“但大多數本地人對此無所察覺。”郝建軍說,“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為什么就發財了。”
2004年前后,大量的南方人來到鄂爾多斯收購煤礦,他們提前看到了能源價格上漲的趨勢。“北部普通煤礦一下子可以賣幾百萬元,南部精煤區的礦甚至可以賣到2000萬元。鄂爾多斯人祖祖輩輩都沒見過這么多錢,大量本地人就在這個時候把礦賣掉了。”郝建軍說。

康巴什新區有了氣勢恢宏的骨架,但其血肉尚未豐滿
幾乎一夜之間,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在鄂爾多斯陸續出現。
煤炭行業井噴之際,正是鄂爾多斯人坐擁財富之時。整個2005年都充滿了投機與暴富的氣息。從年初到年底,煤礦被層層炒賣,不斷倒手,增值了10倍。“南部精煤區的礦都賣到了上億元,礦主更換頻繁。”郝建軍說,“我們下到礦里去,隔了十幾天礦主就不認識了。”一個個暴富神話被口耳相傳不斷放大。
“他們買到礦后,不會加大投入,就是賺一點現實利益,然后等待下一個買家的到來。但對地方經濟來說,更需要正規的行業和企業,需要長遠規范化的發展。”郝建軍說,“在這種情況下,搞煤礦不是做實業,而是投機游戲,根本無法擴大生產,提高功效,提高安全水平。”
另一方面,政府也已經看到,經濟景氣周期到來,煤炭價格進入了上升通道,只有提高產量才能夠為地區帶來持續穩定的財富。于是鄂爾多斯政府做出一個超前而又大膽的決定,繼續對剩下的552家煤礦重組,淘汰落后產能,提高資源利用率,進行大范圍的技術改造。這項措施比相鄰的山西省早了4年。

只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原來的552座煤礦關閉了整整50%,只留下了276座。到2007年底,剩下的276座煤礦全部實現了正規化、機械化開采。與此同時,煤炭的財富效應開始在社會管道中逐級傳遞。
2005年,鄂爾多斯煤炭產量只有1.17億噸,到2009年則達到了3.3億噸,在4年的時間里,產量增長了近兩倍,而價格則增長了7~8倍。煤炭開始成為這座城市經濟的巨大動力,煤礦的規模不斷擴大,從幾萬噸到上千萬噸,大型機械代替了人工采掘。每天有超過10萬輛重型卡車奔波在鄂爾多斯到包頭的公路上。煤炭從鄂爾多斯的土地下挖出,沿著鐵路運到秦皇島裝入海輪,再經渤海、黃海、東海進入長江口,輸送到東部工業基地。另有20%的煤炭,就地轉化為電力或者甲醇、二甲醚、烯烴等工業原料,甚至成為柴油和汽油。重化工業、裝備制造業正在成為這里的支柱產業。
發電廠、化工廠、大型機械廠、汽車生產線也如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從2007到2009年,固定資產投資超過了3000億元。
鄂爾多斯的經濟“馬車”,就如同當地的車牌“蒙K”——當地人習慣稱為“猛開”一樣,迅猛地行駛在高速路上。財富的增加,除了那些傳說中一夜暴富的發跡者,更體現在經濟社會暴富式成長。
2006年,劉宇東來到了鄂爾多斯,此前他在北京經營著自己的咨詢顧問公司。他的一位大客戶是鄂爾多斯老板,當他第二次來到這里時,就決定接受甲方的招安,成為老板旗下路橋公司的副總經理。“到處都在施工,修路、蓋樓,興建廠房,我感到到處都是機會。”劉宇東說。
2007年,鄂爾多斯機場建成使用。此前,劉宇東一直在包頭下飛機再轉乘大巴。“起初,一架航班只有十幾個乘客,有時候還沒乘務員多。”劉宇東說,“但很快,飛機就被填滿,而且從不打折。”大量的冒險家、投資客擁入淘金,同時本地的富人們成群結隊地前往大城市消費、置業。短短的兩年多時間,一座航站樓已經不堪重負,第二座航站樓的修建已提上日程。
財富如同落入沙漠中的雨水,迅速進入到每一個社會細胞之中。這座城市有1800輛出租車,但是通過路虎旗艦店賣出去的越野車就超過了2000輛。在東勝鐵西新區,到處都能看到洗車行。在每個洗車行門前,總會看到價值百萬元的豪車在排隊洗車。50元一次的洗車價格絲毫阻擋不了洗車的熱情。
高檔餐飲業的繁榮順應自然。鮑參肚翅是高檔酒樓的標配,而且價格更高。“開車去包頭吃飯也要比鄂爾多斯便宜很多。”劉宇東說。食客的口味也愈加挑剔,酒店的總廚更換頻繁。我們所居住的酒店與一家香港餐飲集團合作,專門請來了香港師傅料理鮑魚。每天早餐時,都有操著粵語的廚師,在一旁觀察食客的口味。高端服務業人才炙手可熱,這家酒店的餐飲負責人剛剛被另一家煤老板開的飯店挖走,身價是50萬元的年薪外加一輛奧迪車。
由此,鄂爾多斯講述了一個特殊的中國故事,她甚至顛覆了我們以往30年延續的梯度發展理論,形成了一個“反梯度”的案例。
財富與社會變遷
現為鐵西新區主體的羊場壕的農民們也因此一夜暴富。鄂爾多斯市一位官員給這些被征地農民講課,當他問在場的農民,家有存款100萬元以下的請舉手時,竟然沒有什么人響應,而當問到存款100萬元以上的時,幾乎全都舉起了手。
這在鄂爾多斯市區是平常不過的事情。鐵西新區里高樓林立,盡管冬季的夜晚這里冷冷清清,但并不妨礙羊場壕人享受他們的暴富式生活。在小區里,寶馬、奧迪等一輛輛高檔私家車驗證了這種財富。
這些過去以種菜為生,甚至連大糞都要哄搶的農民,在一夜之間變成了當地話所說的“抖達得不行”的有錢人。他們如今靠錢生錢、靠房賺錢,住著別墅,開著豪車,很多人閑得發慌,靠打麻將和去商場購物來打發時光。
關于鄂爾多斯人炫富性消費的傳說不斷。從悍馬、英菲尼迪、帕杰羅到奔馳,無論是多么名貴的越野車,都很容易在鄂爾多斯找到它們的蹤跡;鄂爾多斯的女人打著飛機去廣州或北京購物;近三年來,“鄂爾多斯購房團”的足跡,遍布了青島、威海、大連、三亞等沿海城市。
除了暴富起來的普通民眾,當地政府的大手筆投資同樣高調。
2006年鄂爾多斯市委、市政府搬到了離東勝城區25公里左右的康巴什新區。除了有通勤卡的公務員,人們從東勝到康巴什坐K21路車需要花費7元錢。
在康巴什新區市政府大樓前,耗費巨資的博物館、歌劇院、圖書館、文化中心等建筑堪稱中國建筑藝術新的實驗場。造型怪異的博物館更是被一些人稱為像被割了四肢的丑八怪。不過當地人也自有自己的樂趣, “原本以為只有北京等大都市才有的怪建筑,原來在鄂爾多斯也能看到。”當地居民說。
但對于絕大多數的鄂爾多斯人來說,這些公共建筑與他們的生活并沒有多大的關系。盡管不缺錢,但如果不是免費,他們也很難有意愿坐在里面欣賞高雅藝術。正如一位來鄂爾多斯的外地人所說:“你很難想象,在星巴克里和臉上依然帶著高原紅、尚未脫去牧民氣質的鄂爾多斯人,坐在一起喝咖啡會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而對此,當地政府卻有著另外的理解。這些公共建筑被當地稱為民生工程的內容之一,與此相關的一些建筑還是當地產業轉型的內容之一。
財富的快速聚集,使鄂爾多斯處于劇烈的突變之中。所有的變化都是以躍進的方式運行,而非循序漸進。新城市、新產業、新經濟模式、新需求、新富階層與新生活方式,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幅有趣的社會圖景。而這種自由度和可能性,恰恰是當下中國眾多城市所不具備的。充裕的資本在這塊土地上左沖右突,尋求出路。財富之外衣下,是一場深刻而劇烈的社會變遷。
事實上,鄂爾多斯的財富故事并非坐擁富礦那么簡單。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積累后,如何使用財富、駕馭財富,就成為政府與“煤老板”們共同面臨的問題。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的概括,叫做“資源詛咒”,指的是過分依賴資源,反而限制經濟的發展。初級資源型產業的大規模發展,導致人力資本的積累和科技能力的提升受到限制。在某種意義上,破除“資源詛咒”即是對自身生存模式的革命甚至顛覆,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氣。
內蒙古的“香港”
“不要迷戀鄂爾多斯,鄂爾多斯只是個傳說。”這是連輯“鄂爾多斯人均GDP超香港”豪言出臺之后,鄂爾多斯當地民眾在論壇上套用時下流行的網絡語言寫下的句子。
2009年12月5日,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內蒙古大學校長連輯在第八屆中國企業家領袖年會上表示,世界經濟增速最快的是中國,中國增速最快的是內蒙古,內蒙古增速最快的是鄂爾多斯,鄂爾多斯的人均GDP將超過香港。但這條“未來時”的信息后來被誤讀為“完成時”。2009年香港人均GDP折合人民幣約為20.5萬元,比鄂爾多斯尚多出6萬元。
事實上,完整的表述應該是,5年內鄂爾多斯的人均GDP將超過香港。一個中國西部沙漠中的城市,她創造財富的能力將有可能與香港比肩。而后者,作為東方之珠、亞洲金融中心,是中國城市仰望30年的經濟制高點。
統計數據顯示,按常住人口160萬人計算,鄂爾多斯2009年人均GDP達10萬余元,同比增長19.9%。超過全國 2008年人均GDP2.3萬元近5倍。香港總人口680萬,2008年人均GDP為3.07萬美元,約合人民幣20萬。
一石激起千層浪。很多鄂爾多斯人聽后,內心充滿了驕傲。而對于鄂爾多斯政府而言,卻多少有些尷尬——連輯的言論并沒有贏得太多掌聲——媒體對鄂爾多斯資源型發展模式的質疑不斷;更有媒體稱,這樣的炫耀不值一提。
當地的官員向記者強調,連輯的本意并非如此。鄂爾多斯市聯興拍賣公司副總經理王峰也是這么認為,他說,連輯在那樣的場合說這樣的話,本意是想向在場的企業家們宣傳鄂爾多斯的投資環境。
事實上,連輯的話的確起到了一定的宣傳作用。一位溫州商人得知記者在鄂爾多斯時,很興奮地詢問鄂爾多斯的情況。他已經計劃近期赴鄂爾多斯考察投資環境。“聽說他們人均GDP已經超過香港了。”這位溫商說。
在鄂爾多斯2008年的GDP結構中,第一產業對GDP的貢獻率為2.2%;第二產業對GDP的貢獻率最高,為65.7%;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率為32.1%。而香港2008年的GDP中,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最高,為92.3%。
有專家論斷,香港發展了160多年,鄂爾多斯才起步10年,香港不僅有著在全世界也極具競爭力的金融和服務支柱產業,而且有著成熟的交通、住房、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體系。鄂爾多斯是資源富集地區,再加上人口分布稀疏,GDP“突飛猛進”實屬正常。但以資源為主導絕非長久之計,一旦資源趨于枯竭,經濟增長將難以為繼。相比而言,香港以第三產業為主導,以自由競爭為保障的增長模式,才是較為持久而健康的。雖然鄂爾多斯不斷在數據上刷新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極限,然而要真正超越香港,鄂爾多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