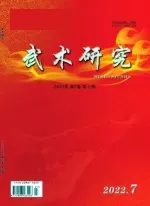全球化時代中國武術的生死抉擇:或者對話,或者死亡
張君賢
(蘇州大學體育學院,江蘇 蘇州 215021)
全球化時代中國武術的生死抉擇:或者對話,或者死亡
張君賢
(蘇州大學體育學院,江蘇 蘇州 215021)
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讓“失語”的中國武術漸入“獨白”的困境。這無形中制約了中國武術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承。文章分析認為:這種狀況是武術傳承者作用于全球化時代的大背景下而集體“無意識傳承”的結果。這將導致中國武術面臨“死亡”的危機。當務之急,唯有“對話”才能讓中國武術走出困境,而“對話”不僅是針對中國武術自身,還應當在“和而不同”文化理念的指導下,實現全球化時代的和諧“對話”。
全球化時代 中國武術 對話
在不知不覺中我們已經跨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在人類的精神領域,出現了全球意識、生態意識、對話意識、文化意識、非實在論意識、親證意識等等。世界上各個國家、民族、地區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聯系空前緊密的同時也日益面臨著許多共同的全球性問題,如環境問題、能源問題、人口問題、和平利用空間問題等等。這些現象的出現是全球化時代所帶來的結果,而它反過來又強化著全球化的趨勢。
全球化在給民族文化發展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挑戰。西方文化作為一種強勢文化正無情的沖擊著有“東方瑰寶”之稱的中國武術,甚至使得中國武術的發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為此,探尋全球化時代中國武術困境的突圍與超越之路,掌握中國武術的時代話語權,成為時代的召喚,成為民族的責任。
1 “獨白”:全球化時代中國武術傳承的致命傷
對于一種文化的傳承,大抵上有兩種方式:“無意識的傳承”和“有意識的創造”。在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文化一直在被無意識的的傳承著。傳統社會里的各種優秀傳統文化,如中國武術、中國醫學、中國書法、中國戲曲等等,在文字、交通、信息不發達和外來文化沖擊小的原始社會與農業社會里,人類多是運用口口相傳或是模仿沿襲的方式“無意識”的傳承著。這種傳統被無意識的一代代傳承下來,其結構相對穩定,變化相應緩慢,但并非一成不變。每一代個體在繼承上一代人的傳統時,都會本能地或不自覺的加入或多或少的個性化理解和篩選,甚至會在不同個體自身的生活體驗和經驗下進行主觀更新、變異和再創造,這即是“有意識的創造”。
誠然,不論是“有意識的創造”還是“無意識的傳承”,文化的傳承均是在時代的大背景下無意識的進行著。客觀的講,所有傳統都是作用于外來文化而源源不斷地被生產、被繼承和被發明的。因此,對于傳統文化的傳承而言,傳承不停,更新不止。
中國武術作為古老的民族優秀文化,在傳承方式上也不例外。無論是原始社會還是農業社會,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野蠻社會還是文明社會,“口傳”、“身授”、“體驗”與“再創造”,一直都是中國武術傳承最主要的方式。如果說“口傳”、“身授”是中國武術“無意識傳承”的最主要表現,那么,“體驗”與“再創造”就是中國武術“有意識創造”的進化過程。
眾所周知,武術自產生之日起,便蘊含著野蠻與血腥。與其說是武術創造了技擊,抑或是技擊創造了武術,不如說是時代創造了武術。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和特定的環境下,會誕生特定的事物,即時代的產物。中國武術便是在這種特定而復雜的背景下應運而生。它的產生是時間的需要,是地域的需要,是文化的需要,是社會的需要,也是時代的需要。簡言之,中國武術產生于被需要時代并在被需要時代中得以繼承和發展。因此,在被需要的歷史時代中,中國武術“無意識的傳承”和“有意識創造”的過程是不自覺的,也是不間斷的。
那么,中國武術究竟是被什么時代所需,并得以良好的傳承與發展的呢?從宏觀上說,是冷兵器時代。在漫長的冷兵器時代里,中國武術不斷的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洗禮,不斷進行著從量變到質變的進化過程。從微觀上看,冷兵器時代人類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充斥著武術文化,武術的生活化和生活的武術化相輔相成,武術受到個人和集體認可并賦予了重要的技擊職能。而武術的“口傳”、“身授”、“體驗”與“再創造”的傳承過程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不斷進行著。
“口傳”,是人類通過聲音(言語、發聲等)的方式描述武術技能的一種方式。而“身授”則是對肢體記錄的武術技擊方法的傳習過程。在這種“口傳”、“身授”的傳承過程中,無論是“口傳”還是“身授”均由于時代的需求而賦予武術技擊對象以濃厚的色彩。這種傳承方式不僅要求武者自身對“武技”的掌握和提升,更強調這種技能根植于“技擊對象”。
誠然,時代也給武術提供了“體驗”的實踐機會,這是對武術“技擊對象”的又一著重強調。通過“體驗”,武者與“對象”進行肢體上的“交流”與“對話”,并對結果進行經驗性地總結和“再創造”。這就是中國武術傳承的方式,它蘊含了太多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這也應該是中國武術傳承的方式,“技擊對象”貫穿武術傳承的始終,并形成良性循環,滋養中國武術,促其茁壯成長。
這種狀況一直按部就班的持續著,直到人類社會在不知不覺中步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新的時代打破了武術千百年來習以為常的一種狀態,也打斷了武術良性循環的進化鏈。這頓時讓中國武術的處境變得十分尷尬,無形的壓力讓中國武術漸漸“失語”,也迫使中國武術不再與人“交流”,悲壯的走上了一條“獨白”之路。
“獨白”是全新時代的中國武術;“獨白”是中國武術“英雄無用武之地”;“獨白”是拋棄技擊對象的中國武術;“獨白”是目光短淺于自我的中國武術;“獨白”是自言自語的中國武術;“獨白”也是語無倫次的中國武術。
在現代傳承過程中,由于“體驗”這一步驟的缺乏與不被需要,中國武術的傳承方式在被動順應時代的的情形下,逐漸對武術“技擊對象”輕描淡寫。這種無意識的傳承方式淡化了“技擊對象”在武術中的核心地位,而強化了武者對于自身形體動作的主觀性。此時的武術是在全新的時代背景下無意識傳承而衍生的新武術,是偽武術,也是被異化的武術。在這種大的時代背景下,傳承中國武術的武者們集體無意識。
這種現象在現代武術傳播中隨處可見:武術傳承者們在“口傳”、“身授”過程中,無意識的總先強調武術動作的路線、方法、方位、要求等等,這種傳承方式所導致的結果就是充分讓習武者的目光專注于自身形體動作的表象,從而忽略了這些技擊動作的根源——“技擊對象”。這也是現代武術技擊“意識”缺乏,“精、氣、神”丟失和武術“體操化”的癥結所在。
2 “對話”:全球化時代中國武術的救贖
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讓思想界風起云涌。美國社會學家羅蘭·羅伯森指出:“作為一個概念,全球化指世界的壓縮(Compression),又指認為世界是一個整體的意識的增強。”壓縮,側重能夠與空間維度的考慮,那就是伴隨著交通運輸、信息傳播等的飛速發展帶來了時空意識和時空觀念的變化。“整體意識”則意味著隨著金融資本、商品人力資源和信息資源等的跨國流通所帶來的整個世界的高度組織化和一體化趨勢,以及人們在觀念上的全球性意識的形成。各種整體意識、全球意識、地球村意識等精神現象的出現,皆源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特殊性。
在全球化時代中人類生活的全面全球化和高科技化讓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文化連為一體,各種文化元素錯綜復雜的交織,形成前所未有的碰撞、交流與對話,甚至是沖突、對立和融合。這樣的時代背景,是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代表之一的中國武術所面臨的前所未有之變局,對于中國武術而言,既蘊含著重大機遇,亦有重重危機顯露。確切地說,中國武術已經走進了“全球對話的時代”(The Age ofGlobal Dialogue),即由過去的“獨白”走向今日的“對話”,而且中國武術今日面臨的近乎是丹麥王子哈姆雷特般的生死抉擇——“或者對話,或者死亡”(Dialogue or Death)。
2.1 有意識的創造:建立全球化時代中國武術技擊的對話語錄
全球化時代下包括中國武術在內的所有民族文化、區域文化、地方文化等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無處躲藏,如果任其自然,聽之任之,終難逃邊緣化的命運。在這緊要的關頭,對中國武術的傳承,更多的或者說是需要一種“有意識的創造”。客觀地說,任何傳統無不是在不斷和外來文化的接觸中被生產和被發明的。沒有更新的傳統是沒有生命力的傳統,而沒有變異的傳統也終將難逃被淘汰的命運。我們堅信,今天的傳統是過去的時尚,而今天的時尚也是明天的傳統。世界上原本就不存在絕對的時尚和傳統。
那么,我們究竟應該“有意識的創造”什么,才能讓中國武術在全球化時代中具有生命的活力?如何創造呢?
首先,我們應當充分認識中國武術表現技擊的特質,它是區別于其他文化個體的特性,是武術賴以生存的根基,也是武術魅力之所在。而創造,正是基于此展開。倘若我們的創造是建立在拋棄,甚至是違背武術本質特征的基礎之上,那么,我們的創造無異于扼殺,武術也將面臨“死亡”的困境。
因此,為了武術能夠更好的表現技擊,在技擊對象缺乏的時代中,我們需要有意識的創造“技擊對象”,建立中國武術獨特的技擊話語。并通過這些技擊性的“對話”向世人展示一種特殊的技能,展示一種文化,一種精神,一種美。
進而,基于此,我們需要有意識地創造技擊對象來改變當前武術傳承的方式方法。無論是“口傳”還是“身授”,先從技擊對象入手。有了技擊的對象,中國武術就不再“獨白”,不再自我,也開始有了“對話”的端倪。因此,創造并培養“對象意識”理應是武術傳承的第一步,它應該被鄭重而反復的強調。這一步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恰恰是這至關重要的一步,卻正在遭受著武術傳承者們前所未有的遺棄。
隨著“對象意識”的逐漸形成,武術技擊性的“對話”也由此展開:我們講解正確的動作方法,是為了讓技擊變得有效;我們示范正確的動作路線,是為了讓技擊變得合理;我們拆分正確的動作結構,是為了讓技擊變得精準;我們展示精妙的動作節奏,是為了讓技擊變得強大……
所有這一切,都是圍繞技擊的“對象”而展開,這就是中國武術應有的技擊性“對話”。如此一來,中國武術這一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便在不知不覺中經歷了時代的更新和文明的洗禮,從而,也經歷了一次全面的藝術化升華。
2.2 和而不同:樹立全球化時代中國武術的話語權
全球化時代,人類生活的變化翻天覆地。全球化不僅僅意味著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迅速流通,新的科技手段跨國界的運用,以及經濟的一體化,同時更意味著我們越來越多地獲得了一種世界性的視野,越來越切近的認識到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緊密關聯,也越來越深刻的體會到了前所未有的碰撞與交流。在這個豐富多彩且變化多端的時代下,如何保護和弘揚中國武術的民族性,并讓其融入世界的大家庭之中讓世人共享,是我們當代人的責任。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因為世界一體化越強烈,全球共性的東西越多,世界對多元文化的需求也越大。因此,文化多樣化將是全球化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
中國武術作為中國優秀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時代的傳承過程中,應遵循“和而不同”的基本原則。關于“和而不同”,《左傳》中講述過這樣一個故事:齊國的大王對他的大臣晏嬰說:“我與大臣們相處得很和諧。”晏嬰問:“是怎樣一種和諧呢?”齊王說:“我說對了,他也說對了,我說錯了,他也說錯了。”晏嬰說:“這不叫‘和’,這叫‘同’”。那么,“和”與“同”有什么不同呢?晏嬰說:“比如在做菜時,需要加各種佐料才能好吃,若不斷地加水就不好吃;音樂,比如說彈琴,總是一個音調那是沒法聽得,而需要各種不同的音調和諧起來才好聽。‘和’才能促進事物的發展。‘同’總是一樣的事物怎么會發展呢?”(《左傳·昭公二十年》)
“和”與“同”,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對重要范疇。“和”是指不同性質的東西相摻和,它反映的是一種有差異的平衡或多樣性的統一。“同”是指相同的事物的堆積,它反映的是無差別的同一或抽象簡單的同一。就當今全球化時代而言,“和”即是經濟、政治,人們觀念、意識等的一體化。“不同”則是各國、各民族、各地區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因此,“和而不同”是一個辯證統一體。它的基礎首先是“不同”,只有有了“不同”,經過交流、溝通和協調,才能達到相容、和諧的境地。
中國武術在追求“和而不同”的世界文化交往中,堅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原則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我們必須發掘、凸顯和傳承中國武術的精髓,堅持武術的技擊對話精神與民族精神,并將它貢獻給世界。
第二,在傳承過程中,我們要有效的保護中國武術這一民族文化遺產,防止它的異化與被同化。
第三,我們要避免以為只有中國武術才是最優秀的民族文化的傾向,敞開心扉,以包容的心態向外來文化學習。
最后,我們要堅定民族信念,不屈服于壓力,不屈服勢力,不屈服于霸權,做到不卑不亢,有容乃大。
3 結語
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給中國武術帶來了危機感的同時,也帶來了機遇。新的時代攪渾了中國武術的“一池”清水,給沉睡的中國武術敲響了警鐘,也一時混淆了我們的視聽覺。但是,當浮華散去,喧囂沉寂,雜質沉淀之后,中國武術的魅力將再度呈現,明白這一點,對于中國武術今天所面臨的處境和命運,對我們如何認識和對待這一處境和命運,都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1]羅蘭·羅伯森.全球化——社會理論和全球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陳旭光.從沖突、對話到融合——全球化時代中西藝術交流和中國電影文化傳播策略的思考[J].現代傳播,2009(3).
[3]易紅霞.全球化時代粵劇的傳承與發展[J].中國紅豆,2007(6).
[4]趙振宇.和而不同:全球化時代的中西方文化傳播[J].現代傳播,2004(2).
[5]王 崗.中國武術文化要義[M].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
[6]溫 力.原始人類的技擊需要促進了武術的產生[J].武漢體育學院學報,1999:33.
[7]葉獻丹.全球化時代中國武術文化認同及其策略反思[J].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07:22.
[8]王 崗,吳 松.中國武術:一種理想化的技擊藝術[J].體育文化導刊,2007(2).
[9]劉樹軍,李通國.論武術套路的表現性技擊[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05(10):29.
[10]戴國斌.武術技擊觀的“解咒”[J].體育與科學,2002(1):23.
[11]徐保國,趙 霞,歐衛軍.關于全球化時代共存智慧的思考[J].科協論壇,2007(8).
[12]楊 明.全球化及其時代特點[J].體系與動力,2007(3).
[13]桑全喜.全球化背景下我國民族傳統體育的時代抉擇[J].體育科技文獻通報,2007(10).
[14]彭修銀. 回歸東方走向世界——全球化時代的東方美學[J].天津社會科學,2006(6).
[15]王克兢.淺談全球化時代背景下中國傳統文化的建設[J].傳承,2009(4).
[16]魏 瑋,張未靖,劉東升.論全球化時代體育文化作用力的傳播方式[J].沈陽體育學院學報,2008(3).
[17]王 韜.“普世理想”與民族性——探討中國文學在全球化時代的出路[J].學報,2003(4).
[18]鞏緒發.全球化時代中國書法的使命與愿景[J].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
[19]胡 一.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自覺與文明對話[J].福州大學學報,2006(2).
[20]鐘淑潔.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跨文化對話[J].黨政干部學刊,2004(12).
[21]汪飛舟.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傳播策略[J].現代傳播,2001(5).
[22]肖 琴.全球化時代文化交流的哲學思考[J].湖南行政學院學報,2007(6).
[23]黃佑琴,劉慶華.論技擊在高校武術教學中滲透[J].軍事體育進修學院學報,2008(4).
[24]朱清華. 武術教學方法新探 [J]. 搏擊·武術科學,2009(12).
[25]傅 謹.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戲劇[J].藝術百家,2008(6).
[26]韓 雪.少林武術:應對全球化時代發展的思考[J].搏擊·武術科學發展研究,2005(11).
[27]李 龍,虞定海.全球化時代中國武術教育發展的思考[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09(4).
[28]申 亮.全球化時代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選擇[J].搏擊·武術科學,2008(4).
The Key Choice of Chinese Wushu in Globalization Time:Dialog or Death
Zhang Junxian
(The School of P.E.and Sport,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Jiangsu 200483)
The arrival of the Globalization time makes the"aphasia"Chinese Wushu gradually enter the"monologue"difficult position.This has restricted Chinese Wushu inheritance imperceptibly around the world.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finds that,this kind of condition is the result of Wushu heirs with collective"unconsciousness inheritance"under the big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time.This will cause Chinese Wushu to face the crisis of"the death".Urgently,only are"the dialog"able to let Chinese Wushu go out of the difficult position,but"the dialog"not only aims at Chinese Wushu itself,but to realizes the harmonious"dialog"in globalization time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cultural idea of"friendly but different".
globalization time Chinese Wushu dialog
G85
A
1004—5643(2010)12—0005—03
張君賢(1981~),男,碩士,講師。研究方向:武術理論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