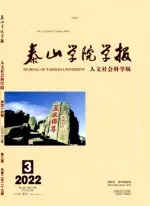論明代胡應麟《經籍會通》的編輯學術特色
梅煥鈞,閻現章
(1.泰山學院學報編輯部,山東 泰安 271021;2.河南大學學報編輯部,河南 開封 475001)
在編輯出版、科學研究和古籍整理的學術文化傳播活動中,對于史料和古代流傳的書籍之真偽進行辨別,去偽存真,由此而形成了一門專門的辨偽學學問。辨偽就是控制文獻信息傳播的失真,把文獻中的偽信息揭示并汰出傳播過程,保證真實信息的傳播,它是控制或避免文獻傳播失真的一種有效方法。而對于古書的真偽進行科學的辨偽,也是編輯出版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辨偽學的學術發展歷史上,明末胡應麟撰寫的《四部正訛》,是我國古代第一部辨偽專著。胡應麟在總結前人辨偽成就的基礎上,并結合自己實踐建立了考辨偽書的理論和法則,從而使辨偽學成為了一門專門的學問,同時他對歷代圖書編輯源流、散失混雜、刻印收藏等進行綜合性和比較性研究后,撰寫的《經籍會通》是一部隨筆性的編輯筆記,也同樣具有較高的文獻史和編輯史的價值,這對于學術研究和圖書出版傳播業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一、胡應麟的編著學術活動
胡應麟(1551-1602年),字元瑞,明代浙江蘭溪人。《明史》在《王世貞傳》中簡單附記說:“胡應麟,幼能詩。萬歷四年舉于鄉試,久不第,筑室山中,購書四萬余卷,手自編次,多所撰著。”據吳晗先生在《清華學報》1934年第 1期發表的《胡應麟年譜》所載,胡應麟“晚更字明瑞,嘗自號少室山人,已而慕其鄉人皇初平叱石成羊故事,更號曰石羊生。又號曰芙蓉峰客,壁觀子。兒時肌體玉雪,眉目朗秀”。
他好學成性,幼年時代就留心經籍。《少室山房類稿》卷 92《二酉山房記》說:“始余受性顓蒙,于世事百無一解,獨偏嗜古書籍。七齡侍家大人側,聞諸先生談說文典,則已心艷慕之,時時竊取閱。”嘉靖四十四年 (1565年),他 15歲時就編輯諸小說為《百家異苑》。他深受其父的影響,喜好書籍,并節衣縮食搜求圖書,在收藏圖書和學術研究中十分艱辛。隆慶六年 (1572年)胡應麟 22歲,《胡應麟年譜》據《少室山房類稿》卷 92《二酉山房記》記載,是年“夏,束裝南返,便道還里中。宋宜人顧從宦日久,田園蕪。又先生素羸,因請留處家,而副憲公入楚督漕糧。命下束裝日,宦橐無錙銖,而先生婦簪珥亦罄盡,獨載所得書數篋,累累出長安。自是先生奉母宋宜人里居十載,中間以試事入杭者三,入燕者再,所涉歷金陵吳會錢塘皆通都大邑,文獻所聚,必停舟緩轍,搜獵其間,小則旬余,大或經月,視家所無有,務盡一方乃已。市中精綾巨軸,坐索高價,往往視其乙本收之。世所由貴重宋梓,直至與古遺墨法帖并,吳中好事者懸貲購訪。先生則以書之為用,枕藉攬觀,今得宋梓而束之高閣,經歲而手弗敢觸,其完好者不數卷,而中人一家產立盡,亡論弗好,即好之胡暇及也,至不經見異書,倒庋傾囊,必為己物,親戚交游上世之藏,帳中之秘,假歸手錄,卷帙繁多,以授侍書,每耳目所值有當于心,顧戀徘徊,寢食俱廢,一旦持歸,亟披亟閱,手足蹈舞,驟遇者率以為狂,而家人習見,弗怪也。自先生為童子至今,年日益壯而嗜日益篤,書日益富,家日益貧。副憲公成進士,剔歷中外滋久,乃敝廬僅僅蔽風雨。而先生所藏書,越中諸世家顧無能逾過者。蓋節縮于朝哺,輾轉于稱貸,反側于寤寐,旁午于校讎者二十年于此矣”。[1]其藏書搜求之艱辛,于此可見一斑。
胡應麟搜求和收藏圖書以實用為主,在藏書的同時主張進一步去閱讀和進行研究,來獲取新的知識信息進行學術創作。他的《少室山房筆叢》卷 1《經籍會通》就是在收藏圖書過程中,對歷代圖書編輯源流、散失混雜、刻印收藏等進行綜合性和比較性研究后,撰寫的一部隨筆性編輯筆記,具有較高的文獻史和編輯史的學術價值。
他反對那種藏書而不讀書和不研究的方法,對于藏書與讀書的關系,在《經籍會通》(四)中針對洪景廬“以博洽名,而早列清華,或未曉此曲折,諸家亦鮮論及”的情況,他明確指出:“博洽必資記誦,記誦必藉詩書,然率有富于青緗,而貧于問學,勤于訪輯,而怠于鉆研者。好事家如宋秦、田等氏弗論,唐李鄴侯何如人?天才絕世,插架三萬,而史無稱,不若賈耽輩之多識也。揚雄、杜甫詩賦咸征博極,而不聞蓄書,雄猶校讎天祿,甫僻居草堂拾橡栗,何書可讀?當是幼時父祖遺編,長笥胸腹耳。至家無尺楮,藉他人書史成名者甚眾,挾累世之藏而弗能讀,散為烏有者,又比比皆然,可嘆也!若劉氏父子,張、陸諸人,庶幾兼之矣。”因此,胡應麟把藏書家劃分為“好事家類”和“賞鑒家類”兩種,他接著說:“畫家有賞鑒,有好事,藏書亦有二家。列架連窗,牙標錦軸,務為觀美,觸手如新,好事家類也。枕席經史,沈緬青緗,卻掃閉關,蠹魚歲月,賞鑒家類也。至收羅宋刻,一卷數金,列于圖繪者,雅賞可耳,豈可謂藏書哉!”有的藏書家,比如唐李鄴藏書多達三萬余卷,但卻很少翻看,圖書新如手未觸摸過一樣。對于這種藏而不讀,胡應麟在《經籍會通》(四)的結尾議論說:“夫書好而弗力,猶亡好也,故錄廬陵《集古序》。夫書聚而弗讀,猶亡聚也,故錄眉山《藏書記》。夫書好而聚,聚而必散,勢也。曲士諱之,達人齊之,益愈見聚者之弗可亡讀也,故錄易安《金石志》終焉。”鑒于此,胡應麟才把藏書與讀書和研究相互結合起來,他的《經籍會通》正是其在整理圖籍和系統研究以及考察圖書出版傳播情況后的編輯作品。
胡應麟癖嗜古籍圖書,若遇到稀世刻本,雖解衣典質也不惜。比如張文潛的《柯山集》100卷,胡應麟舊藏僅有 13卷,屬于抄合類書刊刻者,并非原著的舊版本,“余嘗于臨安僻巷中,見抄本書一十六帙,閱之,乃《文潛集》,卷數正同,書紙半已漶滅,而印記奇古,裝飾都雅,蓋必名流所藏,子孫以鬻市人。余目之驚喜,時方報謁臬長,不持一錢,顧奚囊有綠羅二匹代羔雁者,私計不足償,并解所衣烏絲直掇青蜀錦半臂罄歸之,其人亦苦于書之不售,得直慨然,適官中以他事勾喚,因約明旦。余返寓,通夕不寐,黎明不巾櫛訪之,則夜來鄰火延燒,此書倏煨燼矣,余大悵惋彌月。因識此,冀博雅君子共訪,或更遇云”。[2]由此可見,胡應麟對于稀刻典籍的重視程度,以至于該書被大火燒后“悵惋彌月”。
胡應麟藏書筑室山中,取名二酉山房藏書樓,王世貞曾作《二酉山房記》,對于胡應麟嗜書,讀書和搜集收藏圖書的情況進行了描述。“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書籍,少從其父憲使君京師,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書故,有所購訪,時時乞月俸,不給則脫婦簪珥而酬之,又不給則解衣以繼之。元瑞之橐,無所不罄,而獨其載書,陸則惠子,水則米生,蓋十余歲而盡毀其家以為書。錄其余貲以治屋而藏焉。屋凡三楹,上固而下隆起址,使避濕,而四敞之,可就日。為庋二十又四,高皆麗棟,尺度若一。所藏之書為部四,其四部之一曰經,為類十三,為家三百七十,為卷三千六百六十。二曰史,為類十,為家八百二十,為卷萬一千二百四十四。三曰子,為類二十二,為家一千四百五十,為卷一萬二千四百。四曰集,為類十四,為家一千三百四十六,為卷一萬五千八十。合之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元瑞自言,于他無所嗜,所嗜獨書,饑以當食,渴以當飲,誦之可以當韶,覽之可以當夷施。憂藉以釋,忿藉以平,病藉以起色。而是三楹者無他貯,所貯亦獨書。書之外,一榻、一幾、一博山、一蒲團、一筆、一研、一丹鉛之缶而已。性既畏客,客亦見畏,門屏之間,剝啄都盡,亭午深夜,坐榻隱幾,焚香展卷,就筆于研,取丹鉛而讎之,倦則鼓琴以抒其思,如是而已。故人黎惟敬以古隸扁其楣,曰二酉藏書山房,而屬余為之記。……今元瑞以匹夫之致,而阛阓之守,僅十余年,而至四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卷,不亦難哉!雖然,世有勤于聚而倦于讀者,即所聚窮天下書,猶亡聚也;有侈于讀而儉于辭者,即所讀窮天下書,猶亡讀也。元瑞既負高世之才,竭三余之晷,窮四部之籍,以勒成乎一家之言。上而皇帝王霸之猷,賢哲圣神之蘊,下及乎九流百氏,亡所不討核,以藏之乎名山大川,間以余力游刃,發之乎詩若文,又以紙貴乎通邑大都,不脛而馳乎四裔之內,其為力之難,殆不啻百倍于前代之藏書者,蓋必如元瑞而后可謂之聚,如元瑞而后可謂之讀也。噫,元瑞于書,聚而讀之幾盡矣。”[3]胡應麟在萬歷四年 (1576年) 26歲時中舉,參加鄉試以經義中式成孝廉,后也曾赴京參加會試。但他并未進入仕途,而是醉心于古籍的收藏和研讀,并對所收藏的 4萬多卷圖書整理編輯目錄,在 38歲前著書 18種,輯書 6種,編輯類書 4種,是明代中期一位著名的博學家,與楊慎、陳耀文、焦竑齊名。
其著作集有 120卷的《少室山房類稿》、48卷的《少室山房筆叢》等于世流傳。萬歷三十年(1602年)病逝于家中,享年 52歲。他“髫齡事學,即已馳譽兩都,長而跋涉南北,所與游多一時名下士,達官巨卿,均折節與交。中年與王世貞兄弟汪道昆游,盛得獎掖,益自力于著述,雖間以病廢,且性好游,足跡遍南北,而其著述之富,猶復前無古人。王世貞、汪道昆歿后,先生稱老宿,主詩壇,大江以南皆翕然宗之,諸詞客裹糧入婺者莫敢有異同。……身后極蕭條……所筑二酉山房歸同邑武進士唐驤家,改顏曰古梿書屋。藏書俱散逸無存者”。[4]
二、《經籍會通》的編輯學術特色及其成就
胡應麟正是在這樣的搜書、求書、讀書和編輯整理的校讎、考證實踐中,以及在對前人關于偽書鑒別豐富經驗的總結基礎上,于萬歷十四年(1586年)二月撰寫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辨別偽書的著作——《四部正訛》,從而建立起了一門專門的辨偽學學問。《四部正訛》的問世,標志著圖書辨偽學的正式建立,對于古籍的編輯出版和整理都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萬歷十七年 (1589年)七月,他撰寫了具有重要編輯學術價值的著作《經籍會通》。
胡應麟的《經籍會通》共四卷,關于此書的寫作原委,他在自序中說:“凡前代校綜墳典之書,漢有《略》,晉有《部》,唐有《錄》,宋有《目》,元有《考》,《志》則諸史共之,肇自西京,迄于勝國,紀列纂修,彬彬備矣。夫其淵源六籍,藪澤九流,繹百家,溯洄千古,固文明之盛集,鴻碩之大觀也。昭代綦隆,鉅儒輩出,諸所撰造,比跡黃虞,惟是經籍一途,編摩尚缺,概以義非要切,體實迂繁,筆研靡資,歲月徒曠耳。夫以霸閏之朝,草莽之士,猶或拮據墳素,忝竊雌黃,矧大明日揭,萬象維新,豈其獨盛述鴻裁,彪炳宇宙,而脞談冗輯,闊略曩時哉!輒不自揆,掇拾補苴,間以管窺,加之棁藻,稍銓梗概,命曰《會通》,匪直寄大方之嚬笑,抑以為博雅之前驅云。”[5]可見,胡應麟鑒于當時對于歷代圖書出版傳播的“編摩尚缺”,以及“概以義非要切,體實迂繁,筆研靡資,歲月徒曠”的主客觀原因,靜下心來“脞談冗輯”,對于所藏之圖書進行編輯整理和編輯論證,“掇拾補苴,間以管窺,加之棁藻,稍銓梗概”,在進行編輯記載和考論的過程中,他繼承了中國古代“會通”的編輯思想,因此將其編輯整理和考論的著作以“會通”名之。
一般認為,該書是胡應麟考論書籍的撰著、傳播和收藏情況的,是一本對歷代書籍編纂源流、散失混雜、刻印收藏等情況作綜合性、比較性研究后的成果,也是一種議論與記載合編、考辨與傳聞共存的古代文獻史筆記。其實,從出版傳播學的角度來看,該書也是一部反映古代圖書出版傳播歷史的專書。該書的編寫體例,除了總序外,每一卷也都有簡短的序文(序例)來闡發本篇章的內容,其分門討論,有條不紊,結構合理。“述源流第一”(卷 1),主要對于歷代圖書傳播收藏和散佚情況,結合有關資料進行述論。“墳籍之始,肇自羲黃,盛于周漢,衍于梁晉,極于隋唐。一燼于秦,再厄于莽,三災于繹,四蕩于巢。宋氏征求,力倍功半,元人裔夷,事軼言湮,聚散廢興,概可睹矣,述源流第一。”其“述類例第二”(卷 2),主要對歷代圖書編輯分類的發展變化歷史結合有關史料進行述論,并對目錄圖書的編輯分類原則和方法進行探討,都具有很強的針對性。“經史子集,區分為四,九流百氏,咸類附焉,一定之體也。第時代盛衰,制作繁簡,分門建例,往往各殊,唐宋以還,始定于一。今稍掇拾諸家,撮其大略,以著于篇,述類例第二。”其“述遺軼第三”(卷 3),主要對于古今的一些圖書進行辯駁誣謬,其中以子書為主。“古書歷世,兵革洊更,間有殘編裂簡,僅以空名,寓于載籍。輯錄之家,存而不論;博雅之流,論而不議;釣奇之士,顧有取焉。編摩之暇,辯駁誣謬,聯絡遺亡,與癖古者共之,述遺軼第三。”其“述見聞第四”(卷 4),主要敘述胡應麟所見的明代圖書出版傳播的史實。“古今墳籍,梗概略陳,然率綜核陳編,未遑近跡。余九齡入燕,往來吳越,垂三十載,涉歷賓游,脞言鄙事,時有足存,輒綴大都,附于簡末。后之博雅,征求故實,萬一在焉,述見聞第四。”
從出版傳播學的角度來看,《經籍會通》的成就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編輯、編錄、摘編了歷史上及明代有關圖書出版傳播和收藏的重要文獻資料,具有重要的出版傳播史和文獻史意義。同時,該書也附有編者對有關問題的議論考辨和編輯點評,將歷史記載與編輯個人的評論兩者合而為一,富有特色。
比如對于陸子淵的《統論》、歐陽修的《集古錄序》等文章全部編錄。陸子淵家多藏書,所著別集中有記述古今圖書傳播簡況的《統論》,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胡應麟就予以編錄。“自古典籍興廢,隋牛弘謂仲尼之后,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為一厄,王莽之亂為一厄,漢末為一厄,永嘉南渡為一厄,周師入郢為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于劉向父子之所《輯略》者,為書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校定,才七萬七千余卷,則是重復猥雜,張其數耳。《七略》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群撰具焉。南朝盛時,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余卷,尚有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為四庫,開元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余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二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后,備加搜采,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余卷,自后削平諸國,盡收圖籍,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實爾。慶歷《崇文總目》之書,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顧有不及,參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書邪。洪《容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十亡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多不存,因以為嘆。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詔并下,四方奇書,有此間出,見于著錄者,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館閣。高宗渡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淳熙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于《崇文》,而新籍兼之。至于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6]以上是胡應麟所編錄的陸子淵所記古今書籍的梗概。緊接著,他在編輯點評中認為:“頗為簡明,大都本馬氏《通考》所載而節略之。然《隋書》三十七萬,柳顧言等除去猥復,止得三萬七千,見《通考》甚詳,而此以為七萬余卷。梁任昉、阮孝緒等目錄,大約不過三萬,雖云釋典在外,要不過二萬余。元帝收集煨燼,乃得七萬,未必無重復也,唐《志》開元書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學者自為,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共八萬余。陸所言釋老之編雜出者三萬余,迄不詳何所指,考新舊《唐書》咸不合。宋嘉定中,續得一萬八千余卷,陸亦未及載也。”于是,胡應麟又在后面附有“漫識”性的考論,并提出了歷代圖書在傳播的過程中曾經遭遇有“十厄”。
他說:“牛弘所論五厄,皆六代前事。隋開皇之盛極矣,未幾皆燼于廣陵。唐開元之盛極矣,俄頃悉灰于安、史,肅、代二宗,洊加鳩集,黃巢之亂,復致蕩然。宋世圖史,一盛于慶歷,再盛于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后,復有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為十厄矣。”對于古今書籍的聚散傳播狀況,他評論說:“等而論之,則古今書籍,盛聚之時,大厄之會,各有八焉。春秋也,西漢也,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太和也,慶歷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時也。祖龍也,新莽也,蕭繹也,隋煬也,安、史也,黃巢也,女真也,蒙古也,皆大厄之會也。東京之季,纂輯無聞 (班《志》率西漢東京甚希,他無校集者),魏晉之間,采摭未備,卓、曜諸兇,摧頹余燼,于聚于厄,俱未足云……大抵歷朝墳籍,自唐以前,概見隋《志》,宋興而后,《通考》為詳。第其卷帙之數,往往異同,緣諸家輯錄,或但紀當時,或通志一代,或因仍重復,或節略猥凡,故劉、班接跡,繁簡頓殊,三謝并興,多寡懸絕,即博洽之流,勤于論核,而疑似之跡,未易精詳。”鑒于這種情況,胡應麟“繹群言,旁參各代,推尋事勢,考定異同”,[7]對于從西漢到宋代的圖書聚散之數結合史書材料,進行了精細的考證。
第二,綜合分析歷代反映圖書傳播歷史的史志目錄、官修和私編目錄之成就和缺失,并對各家目錄書的書目編輯得失和編輯分類 (即類例)進行評論,因此該書也是一部記載中國古代書目編輯史和編輯提要史的重要歷史文獻。
在綜合評論書目和類例的編輯得失時,胡應麟一般都有節錄和分析。他認為,“觀其類例,而四部之盛衰始末,亦可以概見矣”。從對圖書編輯分類的檢閱中,就可以看出編輯分類相互承繼創新的狀況,考察出圖書編輯盛衰的發展歷史。比如劉歆的《七略》,“一曰《六藝》,一曰《諸子》,一曰《詩賦》,一曰《兵書》,一曰《術數》,一曰《方技》,而首之《輯略》,以總集諸書之要,則分列品題,實六略耳。班固《藝文志》,增入五家,而省其十家,共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歆原數三萬三千九十卷,固節其猥冗,僅得十之三四,大概新莽之亂,焚軼之余故也。然《七略》原書二十卷,班氏《藝文》僅一卷者,固但存其目耳。向、歆每校一書,則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近世所傳《列御寇》、《戰國策》,皆向題辭,余可概見,因以論奏之言,附載各書之下,若馬氏《通考》之類,以故篇帙頗繁,惜今漫無所考,詳其義例。《六藝》,經也,《諸子》、《兵書》、《術數》、《方技》四略,皆子也,《詩賦》一略,則集之名所由昉,而司馬氏書,尚附春秋之末,此時史籍甚微,未足成類也”。[8]
對于王儉的《七志》,“一《經典》,二《諸子》,三《文翰》,四《軍書》,五《陰陽》,七《圖譜》”,他認為“前六志咸本劉氏《六略》,但易其名,而益以圖譜及佛、道二家,名雖曰七,實九志也,然不述作者之意,但于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于卷首,蓋亦《輯略》之意。按經不曰《六藝》而曰《經典》,則史固漸備矣,隋《志》謂其文義淺近,遠非歆、向倫。余謂儉,齊相佐命,百事填委,故無暇此,浮剽其名耳”。阮孝緒《七錄》,“一《經典》,二《紀傳》,三《子兵》,四《文集》,五《技術》,六《佛》,七《道》。又本王氏而加《紀傳》,并《諸子》、《兵書》為《子兵》,《陰陽》、《術藝》為《技術》,又益以佛、道二家,史書至是漸盛,與經子并列,而佛、道二家之言,大行中國矣”。
胡應麟認為書目文獻的編目分為四部,“實魏荀勖始之,一曰甲部,紀六藝、小學等書。一曰乙部,紀諸子、兵術等書。一曰丙部,紀史記、皇覽等書。一曰丁部,紀詩賦、圖贊等書。此時史、集二部尚希,故王、阮二目,更從劉氏分七類,至唐大盛,于是史居子上,次經、佛、老附子,次史,而終之以集,定為四部,宋氏以還,遞相沿襲,而作者之意,未有所明。馬氏始仿劉向前規,論其大旨,體制骎骎備矣”。[9]
胡應麟通過對《七略》、《七志》、《七錄》以及荀勖《晉中經簿》四部分類和唐代元行沖《群書四部錄》的綜合分析,認為“前史所述魏晉諸家書目,條流僅舉,詮次靡詳。惟阮氏《七錄》始末,備載《弘明集》中,余睹其分門創義,損益前規,綜核之功,勤且力矣,隋、唐《志》率沿此。”他對于《七錄》的書目編輯成就予以肯定,此外,對《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也都有所評述,大致比較科學地總結了明代以前目錄圖書編輯發展的歷史。
第三,對于明代中期以后圖書的刻印傳播情況,根據其所見聞進行了記載,這對于研究明代圖書出版傳播業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胡應麟在《經籍會通》(四)中,比較詳細地記載了明代中葉后圖書刻印傳播的狀況。他說:“余自髫歲,夙嬰書癖,稍長,從家大人宦游諸省,遍歷燕、吳、齊、趙、魯、衛之墟,補綴拮據,垂三十載。近輯山房書目,前諸書外,自余所獲,才二萬余。大率窮搜委巷,廣乞名流,錄之故家,求諸絕域,中間解衣縮食,衡慮困心,體膚筋骨,靡所不憊,收集僅茲。至釋、道二藏,竟以非力所及,未能致也。”詳細地講述了自己求購書籍的艱苦歷程。
他根據自己所歷所見,認為明代“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內舟車輻輳,筐篚走趨,巨賈所攜,故家之蓄,錯出其間,故特盛于他處。……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東南之會,文獻之衷,三吳七閩,典籍萃焉。……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巨帙類書,咸薈萃焉。”
對于圖書交易傳播的書肆,如燕中書肆、武林書肆、金陵書肆的具體位置以及書肆的盛況也都有所描述。“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于場前,每花朝后三日,則移于燈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則徙于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
當時刻書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越、秦、楚,今皆有刻,類目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
刻印書的紙張,“永豐綿紙上,常山柬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為下。綿貴其白且堅,柬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柬,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黧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篋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
通過對書籍的比較,胡應麟認為:“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抄刻,抄視其訛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
同時,胡應麟又結合葉少蘊關于雕版印刷的說法,進行考論和發揮。
“葉少蘊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書者精于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后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于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對此論,胡應麟說:“此論宋世誠然,在今則甚相反。蓋當代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鉅,必精加讎校,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抄錄之本,往往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束之高閣而已,以故謬誤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抄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抄本咸廢不售矣。(今書貴宋本,以無訛字故,觀葉氏論,則宋之刻本患正在此,或今之刻本當又訛于宋邪,余所見宋本訛者不少,以非所習,不論。)”
葉少蘊說,“天下印書,以杭為上,蜀次之,閩最下”。到了明代則有所變化,胡應麟說:“余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諸方與宋世同。(葉以閩本多用柔木,故易就而不精,今杭本雕刻時義,亦用白楊木,他方或以烏桕板,皆易就之故也。)”
應當指出的是,胡應麟由于對一條史料記載認識的失誤,從而導致了他誤認為雕版印書始于隋代。“葉少蘊云,世言雕板始自馮道,此不然,但監本始馮道耳。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陸子淵《豫章漫抄》引《揮麈錄》云,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后至宰相,遂踐其言。子淵以為與馮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玭后也。載閱陸河汾燕閑錄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 (593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板,此印書之始,據斯說則印書實自隋朝始,又在柳玭先,不特先馮道、毋昭裔也,第尚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本矣,唐文皇胡不擴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抄書。何邪?余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經像,蓋六朝崇奉釋教致然,未及概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后,始漸以其法,雕刻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于今而極矣。(活板始宋畢昇,以藥泥為之,見沈氏《筆談》十八卷,甚詳。)遍綜前論,則雕本肇自隋時,行于唐世,擴于五代,精于宋人,此余參酌諸家,確然可信者也。然宋盛時,刻本尚希,蘇長公《李氏山房記》,謂國初薦紳,即《史》、《漢》二書不人有。《揮麈錄》謂當時仕宦,多傳錄諸書,他可見矣。”
對于胡應麟誤認為雕版始于隋朝的說法,《四庫全書提要》指出:“又云刊板當始于隋,引開皇十三年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板為證。然史文乃廢像遺經,悉令雕造,非雕板也。”
就圖書的制作、傳播技術和方式而言,胡應麟對比古今說:“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書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簡,冗重艱難,不可名狀。秦漢以還,浸知抄錄,楮墨之功,簡約輕省,數倍前矣。然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裹,常兼數番,且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閱展舒,甚為煩數,收齊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抄錄一遍而為印摹,卷軸一變而為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溯而上之,至于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士生三代后,此類未為不厚幸也。(又前代篆隸,與今楷書,工亦有難易也。)”[10]
胡應麟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博學者,也是一位頗有見識的編輯家,他取得成就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就主觀上來說,他富有遠大的志向,廣泛搜求書籍,藏以致用,并對圖書進行細致深入的研究和考辨;就客觀上來說,圖書編輯出版傳播業到明代已很發達,各種書籍車載斗量,這為他成就的取得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對于胡應麟的學術成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說:他“與李維楨、屠龍、魏允中、趙用賢稱末五子……而記誦淹通,實在隆萬諸家上,故所作蕪雜之內,尚具菁華,錄此一家亦足以為讀書者勸也”。《四庫全書》的《少室山房筆叢》編輯提要評價說:“其中征引典籍極為豐富,頗以辨博自矜,而舛訛多不能自免”,比如沈德符《敝掃軒語》、王世禎《香祖筆記》、張文嵐《螺江日記》多有駁正,有人駁正則說明了胡應麟的學術思想引起了學界的重視并得到了傳播,這是一種健康的學風。“沈德符等之所糾,蓋捃摭既博,又不復自檢點,抵牾橫生,勢固有所不免。然明萬歷以后心學橫流,儒風大壞,不復以稽古為事,應麟獨研索舊文,參校疑義,以成是編,雖利鈍互陳,而可資考證者亦不少。朱彝尊稱其不失讀書種子,誠公論也。”[11]
[1][4]吳晗.胡應麟年譜[A].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81,425-426.
[2]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A].經籍會通 (3)[M].北京:中華書局,1958:51.
[3][8][9]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 [A].經籍會通(2)[M].北京:中華書局 1958:33-35,21,22.
[5]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 (甲部)[A].經籍會通·引言[M].北京:中華書局,1958.
[6][7]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 [A].經籍會通 (1) [M].北京:中華書局,1958:6,7-8.
[10]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 [A].經籍會通 (4) [M].北京:中華書局,1958:55-61.
[11]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 (子部雜家類)[A].四庫全書總目提要[M].北京:中華書局,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