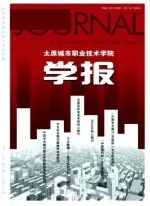略論韓愈的哲學思想
陳黎
(1.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2.太原大學旅游系,山西 太原 030009)
略論韓愈的哲學思想
陳黎
(1.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2.太原大學旅游系,山西 太原 030009)
面對中唐時期儒學社會地位和學術地位的衰落,韓愈提出了儒家“道”的傳承體系,明確了儒家學派的正統地位;進而在總結前人人性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性情三品說”,使性情統一于一體,將仁義充實于性中,為宋明理學以儒家倫理為本位的本體論構建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韓愈;儒家;道統;性情;人性
儒學自孔子創立以來,幾經興衰。漢時董仲舒使儒學成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唐宋間,儒學復興,其間作為儒學理論創新的先驅,韓愈當之無愧。正如史學大師陳寅恪在《論韓愈》一文中對韓愈做出的評價:“綜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為前后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后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于政治、社會、經濟者如此,關于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學術史上承先啟后、轉舊為新關折點之人物也。”
韓愈倡導儒學復興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中國哲學自魏晉以來,形成了儒道釋三教并立的格局。到了韓愈所在的中唐,佛教勢力達到了頂峰;道教的影響也是相當之大,唐皇以老子為其祖先,因此道教在政治上領先于儒教和佛教。除此之外,先秦儒學在經過秦始皇“焚書坑儒”后,通過董仲舒的復興和發展,使儒學成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同時也使儒學喪失了活力,無法應對佛、道在理論層面上的挑戰。
對于儒學面對的危機,韓愈試圖在繼承先秦儒學理論的基礎上,恢復儒學的社會正統地位。韓愈繼承孔孟的“仁義”學說,通過對儒家“道”的論述形成了以“仁義”為核心的“道統”論;繼而在繼承前人人性論的基礎上提出“性三品說”;最后在如何進行心性修養上,韓愈提出了“教化”以“明明德”,以此開創其“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路。
一、韓愈以“仁義”為主體的“道統觀”
韓愈看到了佛道兩教理論在指導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的不足,開始運用和發展儒家學說來彌補兩者之缺憾。仿照佛老的“佛法”、“道法”,韓愈提到了“道”的理論。關于“道”,韓愈首先提出了他對“道”的定義:“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兇有吉。”指出了“仁義”為實,有固定的內容;“道德”為虛,儒佛道均可有自家之“道”,儒家為“仁義”,佛家為“頓悟”,道教為“養生”。之后,韓愈分析了儒家之“道”和道家之“道”的區別: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在韓愈看來,只有“仁義之道”方為天下之正道,佛老之“道”則只是為一人之“道”。在這里,他明確了只有繼承孔孟之說的“道”才是“天下之公言”。
最后,韓愈提出了“仁義之道”所能達到的理想社會模式,并提出了“道統”之說。關于社會理想模式,他說:“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
韓愈構建了自己的理想社會,以“四書”為教化之本,以“四法”為治國之本,將人民分為四種等級,將社會關系分為五種形式,人民吃穿食都有保障。然后,韓愈立足中華正統的立場上提出了“道統”之說:“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在這里,韓愈首先將道統的源頭指向了堯舜,這樣就不僅在學術創建時間上大大早于佛老兩教,在面對諸如佛老的“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的詰難時可以從容應付,提高了儒學的學術地位;再次,定義佛教是夷狄之教,使佛教在和儒教的論戰中喪失了道義的主導權;最后,韓愈對認為“道統”在孟子之后中斷,在韓愈看來自己才是孔孟之后儒家道統的真正繼承人,這樣就將自己納入了儒學傳統體系之中,其弘揚的儒學有了正統的理論基礎。
當然,在韓愈這里并沒有能夠建立完善儒家的“道統”,但他畢竟是在形式上構建了以孔孟“仁義”學說為基礎,涵蓋文法民位服居食七個社會層面的儒學傳承體系,從而起到了承接由兩漢經學和宋明理學的重要作用。在韓愈之前,在漢儒那里,“天”“人”關系是研究的主題,“天”是“人”的主體,這樣就達到了一個形而上的高度,使儒學建立在了“天命”之上,而其過分重視和強調天命的后果也導致了儒學經學化神學化。在韓愈之后,在宋儒那里,他們希望能將形而上的天拉回人間、拉到心性之中,這樣就將儒家道德建立在了“心性”之上。由漢儒到宋儒,從“天命”到“心性”的理論關注的轉變由韓愈開始的。雖然韓愈的“道”還停留在前秦的理論范疇之內,在很大程度上無法擺脫先秦天命觀的影響,但他提出的儒家的“道統說”使儒學得以凝聚力量發展,使儒學能夠在佛老興盛的中唐保持自己正統的地位。同時,他又總是有意地將儒家的本體建立在“道”上,而形而上的“道”,是由形而下的“仁”“義”構成,這其實也就將天命和人道、宇宙論和人倫道德連接了起來,從而也為由兩漢經學到宋明理學的轉折提供了基礎。因此我們看到,正是沿著韓愈“仁義”為本體的“道”,宋明理學結合佛教的“心”,形成了宋明理學的道德本體論,成就了儒學的復興。
二、韓愈的“性情三品論”
漢代之后,儒家的心性論學說幾乎處于停滯階段,韓愈時這種狀況并未得到改觀。韓愈意識到儒教與佛老在理論上的差距,于是,他在繼承和發展孟子以道德作為本體的人性論的基礎中,吸收兩漢人性論的思想,創建了“性情三品說”。
先秦時代關于人性論主要是集中在人性善惡的問題上,孟子屬于性善論,道家屬于性無善無不善論,荀子屬于性惡論,而孔子并沒有系統地論述人性問題。孟子以“先天為善”為基礎構建了心性合一的心性論。在他看來,道德才是人的天性,生理欲望的產生并不是人的天性。他又將道德說成是人生而有之的善端,并將其擴張為“仁義禮智”四端,這樣就形成了“道德由心而發,天生自成”的心性一體論。對于孟子的心性論有一個漏洞:人性為善,那惡從何來?這樣荀子針對這個漏洞提出了“性惡論”,而“性惡論”也存在同樣的悖論:人性為惡,善從何來?后來的儒家學者試圖調和孟子與荀子之間的分歧。在董仲舒之后到韓愈,儒家人性說就幾乎沒有發展。
韓愈并不滿意儒家人性說的這種現狀。在《原性》一文中,他對孟子荀子揚雄的人性論思想進行了批判:“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也。”
他認為他們的人性學說都有缺陷,僅僅看到了人性的一個方面,于是,韓愈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提出了“性情三品說”:“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性之于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于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于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于性視其品。”
人性由“性”、“情”兩方面組成,這是韓愈“性情三品說”的前提基礎。這樣的思想在董仲舒、荀悅的人性論中也有論述。董仲舒認為“性”“情”均為先天生成,他將五行陰陽納入其人性論之中,又把兩者定義為陰陽對應的關系。認為性的本質是善,情的本質是惡,根據情的不同,人性可以分三類:情少的圣人之性;有情的中民之性;情多的斗俏之性。同時董仲舒認為心能夠控制情,只有教化,才能使中性之民為善;荀悅認為“形神為性”“善惡多少非情也”,只承認先天命運的不同,而認為善惡是由性情的后天環境決定的。
韓愈的“性情三品”之說,是對孟子心性論和兩漢三品說的總結和創新,他直接繼承董仲舒的“性”“情”兩分法,賦予了二者新的概念:“性”為先天所有,它所展現的品級有上中下三品,構成“性”的要素有仁、禮、信、義、智;“情”為后天生成,情也有上中下三品,由喜、怒、哀、懼、愛、惡、欲七種感情組成。由此可以看出,韓愈的三品說的結果和董仲舒的三品說是一樣的,兩者都是調和了“性善”“性惡”“性混善渾惡”三種學說的矛盾和不足,將“性善”論,“性有善有惡”論及“性惡”論統一在“性三品”說之中。
但在具體的內容及論述之中,兩人有著很大的不同。在董仲舒看來“性”由“情”定,“性”善“情”惡,情多即性惡,情少即性善。“性”“情”均是先天注定,是善是惡,生而自成,所以圣人之性因情很少而為善,斗魈之性由于情很多而為惡,這兩種性是不能改變的,只有“中性之民”由于“情”的程度居中,因此不教化就為惡,教化就為善;而韓愈認為,“情”由“性”定,性品決定情品。“性”“情”無所謂善惡,“性”為天生,“情”為后天所成,這樣就將董仲舒的“性”“情”對立的人性觀轉化為“性”“情”統一的人性觀。
韓愈主張儒學正統,他將“性”定義為“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這五者都是儒家的道德法則,這樣人性就是由先天的道德決定,而其“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以“仁”為上品之本的標準無疑是吸收了孟子“性善論”的思想。而“情”包括“喜、怒、哀、懼、愛、惡、欲”,其三品的劃分標準是“中”,這就使其具有宋明理學的意味。
由“性三品說”韓愈提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明確了教化的重要。心性論在韓愈之后成為儒家學者反擊佛教的主要武器。到了宋明時期,心性論已經成為宋明理學各派論述的核心內容。宋明理學各派關于心性的論述不同程度地受到韓愈的影響。例如:張載的對“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劃分。他說:“行而后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認為人成之為人后的兼具善惡的“氣質之性”隨之而來,如果能夠去除“氣質之性”對自己的侵害,那么先天的至善的“天地之性”就會繼續存于己身。在這里,張載修正了韓愈的“性三品”說,將韓愈不能共存于一身的上下兩品之性共存于一身,在另一段話中,張載明確了如何去除“氣質之性”而保留“天地之性”的方法,那就是學習:“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由上可以看出,為了儒學的復興,韓愈提出“道統論”,使儒學的發展有了一條明確的主線;重提儒家人性論,將“仁義”充實于“道”中,重新使儒學從政治回歸到了道德范疇;給“性情”以重新定義,使“性情”問題成為理學的主題,對宋明理學的產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還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明確了儒學的境界,這樣韓愈的心性論體系就基本建成了。總之,韓愈作為漢唐經學向宋明理學轉變的關鍵人物,提出了心性論上的幾個重要方面。在經過宋明理學的繼承和發展后,儒家文化作為社會政治文化的主體地位重新確定了下來。
G64
A
1673-0046(2010)2-01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