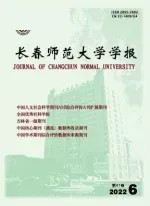釋“格義”:佛經翻譯策略之辨
劉桂杰
(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外國語學院,河南鄭州 450011)
佛經翻譯在中國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東漢時期,自《法句經序》始有翻譯理論著述。從支謙到北宋贊寧,歷經千余年,產生了諸如“五失本,三不易”、“厥中論”、“五不翻”、“六例”等譯經方法和策略,經歷了從直譯到意譯,再到直意譯的圓滿調和的歷史過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佛教對自己“他者”地位的認同使得佛經翻譯開始附會中國傳統的道、儒、法等各家思想,以迎合中國統治者的喜好、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和適應中國文化。同時,本土譯者在“損異”而“善我”的譯經實踐中加速了這一進程。“格義”就是“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1]。佛教經典通過“格義”翻譯策略成為中國本土文化價值的附會者和迎合者,得以在中國傳揚,雖然其呈現的樣態“先舊格義,于理多違”,但是其與中國文化思想的雜合并融合促進了佛經翻譯中國化的進程,在哲學、語言、文化和翻譯策略等方面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內容,在翻譯史上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格義”探源①
(一)佛經翻譯中國化
隋唐以降,佛教在中國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佛教經典也成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組成部分。作為跨文化傳通,佛經翻譯也要逾越不同語言文化的界限所形成的天然鴻溝。為了在中文語境中建構佛教的話語系統,擴展佛教的域外世界,外籍僧人在努力地融入漢語語言文化系統的同時,漢地佛經譯家也在精研佛經的基礎上將其與中國文化融合,以適應漢語語言文化系統。究其精神實質而言,“格義”這種“附會中西之說”的策略推動了異質文化的融合與發展,使不同文化視閾趨同成為精神努力的方向,使佛教文化與儒、道文化共同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2]
佛教經典的翻譯,使佛教東漸有了文本支持。早期的佛經翻譯,以儒、道等的文化觀念來比附佛教觀念,以文化的雜合 (不是融合)來推動佛教的發展;道安提出“先舊格義,于理多違”,以儒、道的義理來比附佛教中的“事數”總是有違佛法本義的。但是任何一個宗教思想的發展,任何一個哲學的抽象,都不免有一個接受—繼承—創新的過程。佛教從漢末傳入,幾經劫難,不斷調適,與中國固有文化融匯,逐漸實現了中國化的轉型進程。因此,“格義”使得佛經翻譯走上了中國化即儒道化的不歸路。[1]
(二)“格義”探源及認知
據流傳甚廣的資料顯示,道安是把“格義”作為佛經翻譯策略的第一人。但是作為概念,“格義”最早見于梁代《高僧傳》:“時依雅門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康法郎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3]。由此看來,“格義”就是用人們所熟知的儒、道家經典中的義理、名詞概念等去比擬或配附佛教經典中的“事數”,使佛經中深奧的義理得以理解。“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即是用一種文化中的概念去比附另一種文化中的概念以達到視閾融合。“格義”不是“格”某物的“義”,而是兩種業已存在的“義”的類比。[3]道安及其之前的佛經譯家文體歸于古樸,“格義”之風使然也。
“格義”策略作為佛教傳入中國并希冀為中國文化接受的權宜之計,對于佛經翻譯中國化具有重要意義。以儒、道家的經典去比附佛教經典“事數”,本身就是一個“文化闡釋”的過程,是佛教為中國文化接受的必經階段。以中國文化為視角,以中國傳統文化為理據,佛教經典義理的傳通中難免會有意無意地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或偏見,會重重地染上中國文化的色彩;作為異質文化和“他者”地位的認同,在與中國文化的交流融合中,會失去自身,最終消融于中國語言文化語境之中,形成新的文化內涵。
二、現代視角下的闡釋
佛經翻譯時期“格義”作為一種翻譯策略,盡管“于理多違”,但卻適應了質樸之風,有天然之語趣,外籍僧人與中國譯經家都樂于用外典 (儒、道家的名詞概念)來翻譯佛經的概念、詞語。[4]“格義”在中國傳統文化和佛教文化雜和之途中的必要性、作用及其在佛經翻譯中國化中的意義,筆者以現代的視角,從哲學、文化和翻譯策略等方面對其理論闡發。
(一)哲學:二元悖論之自然選擇
佛教經典作為一種文化,具有文化的特征:文化是共享的、可習得的、動態的。佛經翻譯是跨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亦應具有文化交際的固有特征:接受、融合和創新。“格義”在面對本土文化和異質文化的二元選擇時,以中國傳統哲學的“本體論思維”,即以儒、道哲學去比附佛法精義,其實質是將中國固有的哲學概念 (主要是老莊哲學概念)和詞匯與佛教中的“事數”進行比附,借用中國原有哲學概念解釋佛法,以讓更多的人了解佛法精義。自漢至北宋,慧遠援引《莊子》疏解佛學的“實相”,以及以“無為”釋“涅般木”、以儒家“五常”配“五戒”,即以“仁義禮智信”比附“五禁”等,此種方法是不符合佛法本義的,由是失之牽強。它在佛教東漸、融會的早期,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終究不是長遠之計。伽達默爾認為,“任何帶有譯者本體思維的翻譯都是詮釋的,想要達到所謂的唯一的意義是不可能的”。在漢語語境中來理解佛教精義,“以‘道’來理解‘菩提’(bodhi)、以‘無’來指代‘空’(sunyata)、以‘無待’來代替‘涅’(nirvana)……”[5],都是本土文化對異質文化的強勢侵入和歸化。佛教中國化過程中的“格義”是以中國原有概念“格”佛學之“義”,哲學上要走出“格義”時代之說最起碼的要求,就是“通順”。走出“格義”時代,關鍵是要將原來“不通順”的解讀變成“通順”的,而不在于簡單變換格式。[6]此處“通順”,當然應有“不失本”之意。
(二)文化:相通、雜合之合理選擇
“格義”策略在佛經翻譯中一方面推動了文化間的交流融合,但同時似乎忽視了佛經讀者接受異質文化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證明了人類文化的精神相通性。如前所述,文化是可以習得的、動態的,不同地區和種族的文化具有特殊性亦具有類同性,這種類同表現在佛經翻譯中國化過程中的連類比附具有合理性,是文化間“趨同”現象的反映。高圣兵等 (2006)認為,“格義是實現思想交流與對話的無奈選擇,是雜合思想之化生的必然選擇”[2]。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當一種新的文化形態輸入國內時,國人會以文化間的相通、動態適應為認知預設,將本土文化的某些側面與之連類、比附、相配,以此詮釋新的文化樣態。
“格義”是以詮釋理解異域文化為認知指向,突顯了詮釋者 (譯經家)的主體和本土文化意識,以超越語言文化的天然鴻溝,達到不同文化間的視閾融合。從本義上來說,采用“格義”策略來溝通佛典中國化的道路,就是將中國儒、道等家的典籍同佛典中難以理解和接受的名詞概念“粗暴”地進行對等理解,使佛典精義中的文化異質與儒道合流,謂之文化雜合。在跨文化傳通和融入中國文化世界的目的前提下,佛教這種文化異質只能接受自己“他者”的地位。因此,這種比附格義的策略在當時是合理的選擇。
(三)翻譯策略:歸化異化之無奈選擇
佛經翻譯文體經歷了“文”“質”之爭,終以惠遠厥中之論“質文有體,義無所越”告一段落;翻譯方法經歷了“名”“實”之辨,繼道安、羅什之后,僧睿以“詳其義旨,審其文中,然后書之”[7]概之。名實之辨反映在翻譯策略上,在筆者看來就是歸化、異化如何選擇的問題。“只要異域文化進入本土文化,無論譯者采用歸化還是異化的翻譯策略,其不可避免地具有語言文化上的雜合”[8]。“格義”策略在佛經翻譯中的采用,以理解異域文化為指歸,以過度的歸化為導向,對佛典精義的曲解是難免的。作為跨文化交流,佛經翻譯也要有一個發送和接受信息的機制,這種機制要交際效度的制約。翻譯效度由趨同和趨異兩個因素影響,效度與趨同度成正比,與趨異度成反比。過分的趨同 (雜合)無法為目的語文化接受,過分趨異 (流散)則會曲解異域文化精要,引起文化僵化。在佛經翻譯中,“格義”方法就是以兩種業已存在“義”的類比來達到文化傳播的目的,顯然會有交際失敗的危險。從信息傳播的角度來說,佛教文化在向本土文化融合的過程中,其信道 (channel)必須是暢通的,但是由于語境、文化、思維、民族性等因素的影響,這種“理想之國”是難以實現的。
(四)身份認同:文化體現之歷史選擇
在翻譯實踐中,無論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還是某一特定領域的文化,識別文化身份可以突顯本民族的文化特點和潛質,保護本民族的核心文化價值不受破壞并得以彰顯。傳統中國文化觀念中的“自我中心論”和“中國本體論”形成了中國文化實體化和實質化的洪流。考察佛經東漸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格義”這種“中學”附會西學的策略是順應歷史潮流的必然選擇。但是,文化從來就是一個不斷發展的事物,文化身份的認同也就成了一個不斷建構的過程。文化多元性的現實告訴我們,所謂的文化“純潔性”已經成為文化開放和交流融合的桎梏。事實上,一個民族或文化實體本著原有的文化基質,按自己的意志去消化,吸收其他文化的成果并最終超越之,是現今各文化發展的共同歷程。因此,我們應該在保護本民族核心價值體系的同時,吸收異質文化,在“文化自我”和“他者文化”的交流中進步、發展。
文化身份從來就不是固定不變的,會因文化的雜異而存在,隨文化的雜合而變化。翻譯在以巨大的力量構建對異域文化再現的同時,也構建了本土文化[9],佛經翻譯尤其如此。考察譯經史,歸化和異化策略的爭辯就是“文化自我”和“他者文化”地位何為主、何為輔的歷史反照。
三、結語
一部中國翻譯史,有一半是佛經翻譯史。季羨林大師曾言:“中華文化的長河有兩次新水的注入,其中之一就是從印度來的水”。顯然,這“印度之水”就是佛經翻譯或曰西學東漸。在佛經翻譯中國化的過程中,“格義”策略影響了多位譯經大家,盡管“附會格義,于理多違”,但在佛經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通過對佛經翻譯的了解,我們可以發現譯經過程并未完全受制于宗教思想的藩籬,而是借鑒了中國傳統儒道之家的思想,使佛經翻譯深植于傳統文化土壤,以儒道來比附發揮佛典精義,使其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大系統。為維護自身文化的純潔性對外來文化一味地否定拒絕,是不可取的;而如果脫離了相關的語言文化語境,強作比附闡釋,亦會引起文化僵化甚或文化沖突。因此而言,“格義”在佛經翻譯時代,特別是中國化興盛的時代,是具有必然性的,也是必經的階段;以現代的視角,在文化多元和“超地域文化共核”共存的現實下,在接受外來文化上應保持一種開放的自信態度。“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通中,既有西方文化的東方化,也有東方文化的西方化,在共同性中尋找差異性,在差異性中尋找共同性”[10]。但這種差異、碰撞和沖突是可以調和的,會在發展中對話最終融合。
[注 釋]
①根據陳寅恪、湯用彤等的研究,“格義”比較完整的注解是在《高僧傳》第四卷。本文主要關注“格義”翻譯策略的現代闡釋和反思。對“格義”本義的詳解,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1]張申娜.從“格義”看佛教中國化[J].河池學院學報,2007(3):16-19.
[2]高圣兵,劉鶯.“格義”:思想雜合之途[J].外語研究,2006(4):52-56.
[3]張舜清.對“格義”作為言“道”方式的反思[J].學術論壇,2006(6):22-25.
[4]王克非.翻譯文化史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55-57.
[5]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396.
[6]張耀南.走出“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格義時代”[J].哲學研究,2005(6):56-61.
[7]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21.
[8]王東風.翻譯研究的后殖民視角[J].中國翻譯,2003(4):3-8.
[9]韋努蒂著,查正賢譯.翻譯與文化身份的塑造[C]//許寶強,袁偉.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359-360.
[10]劉登閣,周云芳.西學東漸與東學西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