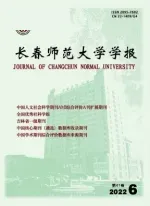錢大昕的目錄學(xué)思想及成就
鄭春穎,楊 萍
(長春師范學(xué)院,吉林長春 130032)
清乾嘉時期,學(xué)風(fēng)大變,由明朝的空疏泛言轉(zhuǎn)為重質(zhì)尚實。目錄學(xué)作為“學(xué)問之眉目”與考據(jù)的重要方法,被士人所推崇,當時學(xué)者出于學(xué)術(shù)研究的需要,開始自覺地對前代目錄書進行品評考證,整理研究。錢大昕曾對《漢書·藝文志》、《隋書·經(jīng)籍志》、《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等史志目錄做過考訂工作,對《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淵閣書目》、《竹堂書目》等官方、私家目錄亦頗有研究。
一
在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中收錄《漢書·藝文志》、《隋書·經(jīng)籍志》等五家史志目錄,考辨內(nèi)容多達二百三十三條。其中,文字校勘方面,糾正錯字、剔除衍字、增補脫字、指明異體字、辨析通假字,幾近百條,甚為精細。如卷五十八《舊唐書·經(jīng)籍志》第二條,梁簡文撰《長春秋義記》,錢大昕指明“春”為衍字[1]。卷七十三《宋史·藝文志》第二十一條,編年類《三十國春秋》原題作者蕭方,錢大昕加注“本名方等,脫‘等’字”。[1]資料搜集方面,錢大昕利用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法,細檢各書,往往能查漏補缺,如卷三十四《隋書·經(jīng)籍志》第十八條,他利用孔穎達《詩正義序》、賈公彥《儀禮疏》引文等資料,增補六藝經(jīng)緯類未錄之書二十八種。[1]第三十六條依據(jù)《隋書》列傳補充于仲文《漢書刊繁》、張沖《前漢書義》等史部書籍十六種。[1]考證辨析方面,錢大昕不但對目錄的作者、書名、卷次逐一考究,對書中的內(nèi)容,如官制、避諱、籍貫、地名等亦往往有精彩的論斷。如卷四十五《新唐書·藝文志》第二十五條,刑法類《開元后格》,原注云“禮部侍郎兼侍中宋”,錢大昕批注“侍郎當作尚書”[1];《宋史·藝文志》第二十三條,程正柔《大唐補記》三卷,錢大昕注云“本名匡柔,避諱改”。[1]
中國古代的目錄書肩負著“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的重任,作為指導(dǎo)治學(xué)的工具書,若書寫體例混亂,分類標準龐雜,勢必影響它的功用價值,因此目錄書在體例分類方面,往往都有嚴格的要求。體例分類合理與否不但是學(xué)者考究目錄書的重點內(nèi)容之一,同時也是衡量編修目錄者學(xué)術(shù)思想、綜合治學(xué)能力的重要參考因素之一。在《宋史·藝文志》第七條載錢大昕在朱熹《書說》下,加注提示“黃士毅集”四字應(yīng)該分注。[1]“分注”的目的是使條理更為清晰,方便檢索。凡各家目錄歸類有異議的書籍,他或是兩者并舉存疑,或是根據(jù)各方資料重新判定,糾正訛誤。如《宋史·藝文志》第五條楊簡《已易》,《宋史·藝文志》歸于易類,錢大昕注“《文獻通考》在儒家類”[1];《隋書·經(jīng)籍志》第十四條《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六卷,《隋書·經(jīng)籍志》將其附于《論語》之末,錢大昕分析“此書本為議禮而作”,應(yīng)當歸于“禮家”,或“儀注”目下,批評《隋書·經(jīng)籍志》的分類“失其倫”[1];《新唐書·藝文志》第四十七條,總集類司馬相如《上林賦》下,錢大昕注云“《上林賦》以下八部,不當入總集。”[1]
錢大昕格外關(guān)注一書重出現(xiàn)象,對目錄書中互著的分類方法頗有微詞。在《隋書·經(jīng)籍志》第十條,京相《春秋土地名》題目下,錢大昕按云:“志中一書而重出者,如京相《春秋土地名》三卷,一見春秋類,一見地理類;李概《戰(zhàn)國春秋》二十卷,一見古史類,一見霸史類……庾季才《地形志》,兩收于五行類,而前云八十七卷,后云八十卷,皆史臣粗疏之失。唐、宋而后,志藝文者,重復(fù)益甚矣。”[1]在《宋史·藝文志》第一條,錢大昕加按語“此志合《三朝》、《兩朝》、《四朝》、《中興國史》匯而為一。當時史臣無學(xué),不能博涉群書,考其同異,故部分乖剌,前后顛倒,較之前史,舛駁尤甚,有一書而兩三見者。如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三十卷,見經(jīng)解類,又見小學(xué)類。李涪《刊誤》二卷,見經(jīng)解類,又見傳記類。……后有鐘輅《感定錄》一卷,疑為一書也。”[1]此條摘錄《宋史·藝文志》中一百余部存在重出現(xiàn)象的書籍。此外,在《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十三《文獻通考》一文中,錢大昕又進一步論及重出問題,其云:
予讀唐宋史藝文志,往往一書而重見,以為史局不出一手之弊。若馬貴輿《經(jīng)籍考》,系一人所編輯,所采者不過晁、陳兩家之說,乃亦有重出者。如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三十卷,見卷百八十五“經(jīng)解類”,又見卷百九十“小學(xué)類”;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五卷,見卷二百一“故事類”,又見卷二百十六“小說類”;郭茂倩《樂府詩集》一百卷,見卷百八十六“樂類”,又見卷二百四十八“總集類”……[2]
以上這些評斷表明錢大昕基本對一書重見現(xiàn)象持否定態(tài)度。其實,在錢大昕羅列的諸條重出書目中,根據(jù)產(chǎn)生原因不同,可以將其分成三小類:
第二類,錯誤。如《宋史·藝文志》第三十三條,傳記類劉諫《國朝傳記》三卷,錢大昕按:“《唐志》小說家有劉讠柬《傳記》三卷,注云:‘一作《國史異纂》。’則《異纂》與《傳記》本是一書。此志小說家既有劉《傳記》三卷,而傳記類又有劉《國史異纂》三卷,已為重出,又不知‘諫’、‘纟柬’皆‘’字之訛,而更出之,益可笑矣。”[1]此例是由編修目錄者學(xué)識淺薄所造成的錯誤。
錢大昕分析產(chǎn)生一書重出現(xiàn)象的原因,要么是“史臣粗疏”,要么是“史臣無學(xué)”,要么是“史局不出一手之弊”,這幾點原因作為第一、二類重出狀況產(chǎn)生的內(nèi)因較為準確,但是,第三類與前兩者不同。第三類分類方法在目錄學(xué)中被稱為“互著”,此名詞由章學(xué)誠提出,后演變成為目錄學(xué)家常用的一種編排書籍的方法,此法便于讀者即類求書,因書究學(xué)。錢大昕籠統(tǒng)地將“失誤”、“錯誤”與“無誤”混為一談,未免不妥。但是,錢大昕作為杰出的文獻學(xué)家,他對于此現(xiàn)象的否定也并非毫無意義。此種否定一方面表面錢大昕認為凡是書籍,無論內(nèi)容多么龐雜,橫跨多少學(xué)科,總會有一定的傾向性,而此傾向性恰恰是可歸之類;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對目錄書價值的定位與普通目錄學(xué)家不同,他可能更看重的是目錄書是否能給學(xué)者提供最有學(xué)術(shù)價值的參考書籍,而不是簡單地將各類書籍煩冗堆砌。這二點體現(xiàn)了一個學(xué)術(shù)大家的獨特視角。
錢大昕對前代目錄書的研究工作,除了校勘考證文字內(nèi)容、辨析分類體例外,對各種目錄書的版本源流亦頗為重視。如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是宋代著名的私家目錄。錢大昕曾于《十駕齋養(yǎng)心錄》卷十四,對其各種版本的優(yōu)劣及源流詳加考證。首先他指明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宋時有兩個版本,然后對此兩本基本情況加以介紹,其云:“袁州本僅四卷,淳佑庚戌番陽黎安朝知袁州刊之郡齋,又取趙希弁家藏書續(xù)之,謂之《附志》。衢州本二十卷,則晁之門人姚應(yīng)績所編,醇佑已酉南充游鈞知衢州所刊。”進而從兩本內(nèi)容入手比較此二書優(yōu)劣,云:“兩書卷數(shù)不同,所收書則衢本幾倍之。”之后又以趙希弁、馬端臨對此兩版本的取舍作為旁證,得出衢本好于袁本的結(jié)論,并為“今世是通行本皆依袁本翻刻。予婿瞿生中溶購得鈔白衢本,惜無好事者刊行之”[2]的現(xiàn)狀感慨不盡。
目錄書是治學(xué)的啟蒙讀物,如果目錄書在文字、分類、內(nèi)容上存在訛誤,無疑會將初學(xué)者引入歧途。錢大昕將各類前代目錄書作為研究對象,或校勘,或考證,辨析版本,探究真相,此項工作有益于后學(xué)之士,并能真正展示目錄書的價值,有利于目錄學(xué)的發(fā)展。
二
錢大昕作為乾嘉時期最著名的考據(jù)學(xué)家之一,利用目錄書考訂文字,考辨史實真?zhèn)?是其最常用的一種方法。在錢大昕眾多的考證實例中,目錄學(xué)研究方法總是處于比較重要的地位。同時,目錄學(xué)與版本學(xué)、校勘學(xué)、輯佚學(xué)、辨?zhèn)螌W(xué)等相關(guān)學(xué)科研究方法的相互結(jié)合又是錢大昕歷史考證方法的另一特色。
錢大昕的考證,有繁有簡,簡單者僅使用一種方法,寥寥數(shù)語,卻論斷明確。如《廿二史考異》卷七十三《宋史·藝文志》第三條,載有《易口訣義》,《宋史·藝文志》題作者為史文徽。錢大昕按云:“《崇文總目》云:‘河南史證撰。’晁氏云:‘唐史證撰抄注疏,以便講習(xí),田氏以為魏鄭公撰,誤也。’陳振孫亦云:‘避諱做“證”字。’則此志‘徽’字當作‘徵’之訛。”[1]第五十二條,馬融《忠經(jīng)》,《宋史·藝文志》題一卷。錢大昕云:“隋、唐《志》俱無此書,蓋宋人偽托。”[1]第五十八條,法林《辨正論》,《宋史·藝文志》題陳子良作。錢大昕按:“法林《辨正論》八卷,又見于《破邪論》之下,此訛‘琳’為‘林’,實一書也。晁氏云:‘穎水陳良序。’《唐志》云:‘陳子良注。’此以為子良作,亦誤。”[1]以上三例,錢大昕通過不同目錄之間的比較,或是發(fā)現(xiàn)訛字,或是揭露偽書的真實面目,或是指明作者真身。大體上《廿二史考異》中諸書的考證多簡短,《十駕齋養(yǎng)新錄》、《潛研堂文集》中的考證相比則豐沛許多,這些考證更能體現(xiàn)錢大昕的目錄學(xué)思想。
如《星經(jīng)》一書,流傳已久。雖前人已懷疑它的真實性,但尚無系統(tǒng)考辨之說。明清以來,受西學(xué)的影響,許多學(xué)者開始關(guān)注天文歷法方面的專門知識,錢大昕亦是其中一人。他在天文、歷算方面的造詣,為他考證此書提供了可能。在《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十四《星經(jīng)》[2]、《潛研堂文集》卷三十《跋星經(jīng)》[3]中他詳細地論證了《星經(jīng)》的偽書性質(zhì)。首先,錢大昕考辨《星經(jīng)》著錄之源,其云“不知何人偽撰,大約采晉、隋二志成之”,又云“《續(xù)漢志·天文志》注引《星經(jīng)》五六百言,今本皆無之,是劉昭所見之《星經(jīng)》久失其傳矣”。其次,他進一步指出“甘石書不見于班史。阮孝緒《七錄》云,甘公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有《天文》八卷,今皆不可見矣”。再次,他又從《星經(jīng)》的文辭特點分析“今《星經(jīng)》詞意淺近”,判定此書“非先秦書也”,在此基礎(chǔ)上又引明人《漢魏叢書》中的評價“漢甘公。石申,皆在戰(zhàn)國時,非漢人也”作為補充。錢大昕考證此書所用的主要方法是以各代目錄書的著錄為綱,文辭特點及前人相關(guān)評價為目,綱舉目張,以目補綱,使書籍真?zhèn)尾谎宰云啤?/p>
再如《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十三《吳越備史》[2]、卷十四《嚴州重修圖經(jīng)》[2]二書。《吳越備史》原書卷首題武勝軍節(jié)度掌書記范、武勝軍節(jié)度巡官林禹撰。錢大昕首引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觀點“錢儼所作,托名林、范”。又引《宋史·藝文志》的記載“霸史類載此書,十五卷,亦云錢儼作,托名范、林禹撰”。初步判定該書作者是錢儼,而非托名的林、范二人。此外,又別考錢儼《備史遺事》一書,先指明此書“今世所傳乃明錢德洪刻本”,在介紹該書體例及記載內(nèi)容時間起訖之后,指出此書“與史志卷數(shù)不合”。又引書末題跋引出撰者“中孚”之名,此后依據(jù)程俱《北山小集》考證“中孚”是“中吳軍節(jié)度使元之曾孫,於武肅為四代孫也”。又引錢岱序謂“范、林二記室撰《備史》五卷,至十九世孫緒山公命門人馬藎臣補忠懿遺事,合六卷,刻之姑蘇。”進而考證云:“今考藎臣所撰,唯《吳越世家疑辨》一卷,德洪序中初不言補遺出其手,岱蓋考之未審矣。”又引錢遵王家藏本補證,云此本“止四卷,又稱忠懿為今元帥,吳越國王,自乾戊申至端拱戊子,終始歷然,何緣更有補遺?”最后判定此書“顯系明人妄改”。
對于《嚴州重修圖經(jīng)》,錢大昕先指明其所見版本為淳熙重刻本,僅存首三卷。次提及卷首有“紹興己未正月知軍州事董序,及淳熙丙午正月州學(xué)教授劉文富序”,進而初步推斷“文富蓋承郡守陳公亮之命訂正是書者也”。又云“卷首載建隆元年,太宗皇帝初領(lǐng)防御使詔;宣和三年,太上皇帝初授節(jié)度使制,及敕書、榜文二道”,進而解釋“太上”稱謂,緣由“淳熙丙午之歲,高宗尚在德壽宮”。之后,考辨此書云:“董初創(chuàng)此志,本題《嚴州圖經(jīng)》,陳公亮重修,亦仍其名;而王氏《輿地記勝》、陳氏《直齋書錄》、馬氏《文獻通考》皆作為《新定志》。蓋宋人州志多用郡名標題,續(xù)志載書籍,亦但有《新定志》,初無《圖經(jīng)》之目,名目雖異,實非有兩本也”。
此兩例反映,錢大昕在考證書籍時思維方式具有發(fā)散性的特點,他考辨的內(nèi)容不僅包括此書的作者、卷數(shù)、題跋、時間,還包括本書作者撰寫的其他著作,或是與此書相關(guān)聯(lián)的各類書籍。錢大昕考證的方法是以目錄書著錄的內(nèi)容為中樞,用目錄中的內(nèi)容來組織安排整個考證過程,目錄著錄的內(nèi)容無論置于何處,開端、中段或是結(jié)尾,因其在整個考辨進程中的核心地位,往往令人矚目。同時,錢大昕又不被目錄的記載所囿,將版本學(xué)、辨?zhèn)螌W(xué)與目錄學(xué)知識相結(jié)合,努力探究致誤之因。
判定一書之真?zhèn)尾⒎且资?錢大昕對于那些可以判定的書籍,往往詳細地考證,并給出清晰的結(jié)論,以免后學(xué)誤入歧途,對于那些尚難判定者,他也會將種種疑問羅列于一處,以待后生定奪。如《周成雜字》[2]一書,錢大昕首先提及此書元應(yīng)《一切經(jīng)音義》、李善《文選注》屢有引用。進而考論《隋書·經(jīng)籍志》小學(xué)類,發(fā)現(xiàn)有《雜字解詁》四卷,提名為魏掖庭右丞周氏撰。又有《解文字》七卷,提名周成撰,此書已經(jīng)亡佚。他認為周氏與周成不是同一個人。錢大昕又查《唐書·藝文志》有周成《解文字》七卷,而無周氏書。因此推論“兩志所載周成書,俱無雜字之名,未知即此書否。”其后,又對官職考辨云:“掖庭左右丞,漢制皆宦者為之。魏承漢制,則周氏亦必宦者。如注《爾雅》之李巡,亦中黃門也。”(見《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卷十三)此推論雖無定論,但其考證對人們了解這部書的基本情況有一定的幫助,此例體現(xiàn)了錢大昕求實的治學(xué)態(tài)度,同時也體現(xiàn)了他一貫的治學(xué)方法。
史學(xué)考證是集提問、求證、推理于一體的學(xué)術(shù)研究工作。考證過程往往是多個學(xué)科、多門知識的協(xié)同作戰(zhàn)。錢大昕的考證多是以諸家目錄校勘比對為始,通過目錄的對校,發(fā)現(xiàn)問題,再進一步追查根源,補充相關(guān)信息,最后辨證疑誤,正本清源。在其考證過程中,目錄學(xué)研究方法,往往處于核心地位,同時錢大昕又注意將目錄與版本、校勘、輯佚、辨?zhèn)蔚认嚓P(guān)學(xué)科的研究方法相結(jié)合,多角度、全方位地對某部古籍及其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內(nèi)容加以考辨。目錄書被應(yīng)用于考證工作是由目錄學(xué)“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的性質(zhì)所決定的,同時,它也說明了錢大昕對于目錄書的性質(zhì)有著清晰的認識:目錄是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的良好途徑。錢大昕的考證實踐活動為后世學(xué)者提供了寶貴的治學(xué)經(jīng)驗。
三
如在《元史·藝文志》經(jīng)部著錄的十二種圖書分類中,易類、春秋類,及論語、孟子、大學(xué)、中庸四類著作非常多,它反映了元代學(xué)界春秋學(xué)、理學(xué)興盛的情況。又如史部編年類著錄數(shù)量頗多,代表的有:楊云翼等《續(xù)資治通鑒》,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釋文辨誤》,尹起莘《通鑒綱目發(fā)明》,王幼學(xué)《通鑒綱目集覽》,劉友益《通鑒綱目書法》,徐昭文《通鑒綱目考證》,張?zhí)亓ⅰ稓v代系事紀》,胡一桂《歷代編年》,察罕《帝王紀年纂要》,蘇天爵《金紀年》等。這些圖書資料說明元代通鑒之學(xué)、編年類體裁備受學(xué)者關(guān)注。
錢大昕在網(wǎng)羅舊籍的基礎(chǔ)上,根據(jù)元代特定的學(xué)術(shù)背景及當時書籍的保存現(xiàn)狀,對目錄子目的設(shè)定等問題進行了有益的嘗試。這使《補元史藝文志》在同類補作中顯得頗為別致。
首先,錢大昕取消了在《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等目錄書中常見的子目。這些子目取消的原因,有的是因為流傳下來的典籍數(shù)目較少,如史部中的紀事本末、時令、別史、載記等目;有的是因為原有子目名與其收錄書籍有出入,名實不符。如經(jīng)部中的五經(jīng)總義、四書二目,往往收書超越五經(jīng)、四書總論,甚為龐雜。此兩目的撤消體現(xiàn)了錢大昕學(xué)術(shù)思想的嚴謹;有的則是錢大昕對于某類書籍性質(zhì)重新評定的結(jié)果,它反映的是錢大昕學(xué)術(shù)思想的獨特性。如史部制誥一類,各家目錄多將其置于詔令奏議子目中,錢大昕則不設(shè)此目,將其處于實錄之下。實錄是中國封建時代記載皇帝在位期間重要史實的資料性編年體史冊。制誥是皇帝發(fā)布的一系列公文,每一份公文無不與某一件歷史事件存在某種必然聯(lián)系。錢大昕此目的處理方式,表明他對于制誥性質(zhì)的認識較其他目錄家更為深邃。
其次,錢大昕增加了一些前代目錄書中未見的新目。如經(jīng)部中譯語目,此目收錄的是翻譯成遼國語、金國語、蒙古語的儒家經(jīng)典。其中,遼語的有《五代史》、《貞觀政要》、《通歷》等;金國語的有《易經(jīng)》、《書經(jīng)》、《孝經(jīng)》、《論語》、《孟子》、《國語》、《新唐書》等;蒙古文的有《孝經(jīng)》、《大學(xué)衍義》、《貞觀政要》、《帝范》等。此目的出現(xiàn)與當時統(tǒng)治階級的少數(shù)民族身份有關(guān),它反映了遼、金、元三代儒家經(jīng)典在社會主流思想中的流行情況,也反映了錢大昕對于儒家思想在元代社會地位的關(guān)注。清末學(xué)者文廷式曾稱贊此舉“體例最善,深得“隋志之意”。再如子部中的經(jīng)濟目,此目下收錄遼、金、元三朝各類經(jīng)國濟民之書,共42種。此類書籍不是對前代統(tǒng)治經(jīng)驗的總結(jié),就是針對現(xiàn)實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提供的解決方法。此目反映了錢大昕經(jīng)世致用的思想。錢大昕提倡“文以貫道,言以匡時”,認為“儒林經(jīng)濟非兩事,根柢深厚枝葉榮,……文章須有裨名教,經(jīng)史自可致治平”。錢大昕不是鉆進故紙堆里,為了考據(jù)而考據(jù)的學(xué)者,在他考據(jù)的背后,隱含的是從古學(xué)中總結(jié)為政之道,以為當世所用的動機與熱情。所以,當其他目錄家將這些經(jīng)世濟民的良策泛泛地歸于儒家一類時,錢大昕卻將此目獨立出來,以示明鑒。再如,集部中的科舉目,此目收錄了大量的有關(guān)科舉考試指導(dǎo)方面的典籍,如各類試卷匯編等。此目的設(shè)立突出了目錄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工具書職能。
再次,錢大昕并不遵循目錄編修中的一些慣例。從最初的《七略》,至《四庫全書總目》,類目的劃分漸趨精細,由二級類目到三級類目的出現(xiàn),代表的是當時目錄學(xué)發(fā)展的總趨勢。錢大昕卻化繁為簡,雖分經(jīng)、史、子、集四部,但子目數(shù)量比其他同類目錄少,并且在子目下,不再設(shè)細目。此種分類方法最大的好處是方便學(xué)者查找資料,它體現(xiàn)了錢大昕對于目錄書功用價值的重視。無論《隋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等史志目錄,還是《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私家目錄,或是《四庫全書總目》等官方目錄,往往史部刑法 (或法令、政書)目與子部法家目并舉,因?qū)Χ叩膮^(qū)別不甚明晰,經(jīng)常張冠李戴。錢大昕則根據(jù)元代無法家著作的現(xiàn)實情況,取消了子部中的法家類,將《唐律疏義釋文》、《刑統(tǒng)》、《無冤錄》等刑律、辦案匯編類的典籍收入刑法目,此分類科學(xué)地反映這類書籍的性質(zhì)。錢大昕關(guān)注刑法類書籍與他“德主刑輔”的政治理想有關(guān),他曾經(jīng)對《宋史·刑法志》有一定的研究,他維護法律的嚴肅性,主張“法當殺而故出之,是之謂縱;法當宥而故入之,是之謂濫。天子之不可以縱奸,而士師之不可以濫殺也。”錢大昕在法律方面的修為,有助于他對刑法類書籍范圍的界定,也使目錄的分類更為客觀。
錢大昕除編修了《補元史藝文志》外,還編修了《范氏天一閣碑目》、《道藏闕經(jīng)目錄》等目錄書。錢大昕在金石學(xué)方面頗有造詣,其考史補史工作經(jīng)常以金石學(xué)方面的資料作為重要依據(jù)。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他來到寧波范氏的天一閣,將范氏子弟未嘗重視的碑刻資料清理出來,編為《范氏天一閣碑目》,收拓片580余通。這部關(guān)于碑刻的專題目錄,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它體現(xiàn)了錢大昕對于金石資料的重視,同時,也說明他將目錄編修作為整理資料的一種方法。錢大昕早年聽惠松提及道藏中多儒書古本,歸田后廣為收集,先后求得朝天宮本、玄妙觀本等版本,又得袁又愷協(xié)力,成書八百余卷,多為儒生必讀之書。在《道藏闕經(jīng)目錄》的跋文中,他說“宋《藏經(jīng)目錄》失傳,此冊乃元人所記,和之今傳者,可以得宋藏之梗概”。恢復(fù)宋藏之原貌,可謂功不可沒。
綜上所述,錢大昕注重目錄學(xué)在文獻整理工作中的實際運用價值。他對前代諸家目錄或有評價,或有考證,時推善本,以企流惠后學(xué)。目錄學(xué)研究方法是其歷史考證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他將目錄與版本、校勘、輯佚、辨?zhèn)蔚裙ぷ飨嘟Y(jié)合,形成了具有其個人特色的考辨系統(tǒng)。錢大昕學(xué)識淵博,橫跨經(jīng)史,兼修各家,具有良好的學(xué)術(shù)修養(yǎng),這使他比普通的目錄家更能認清書籍的本質(zhì)。錢大昕不是鉆進象牙塔不問世事的學(xué)者,他一直強調(diào)學(xué)術(shù)的現(xiàn)實意義,強調(diào)經(jīng)世致用,因此他所編修的目錄書從形式到內(nèi)容,都具有獨特的學(xué)術(shù)氣息。
[1]錢大昕.廿二史考異[M]//陳文和.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1139,1378,738,740,945,1378,1376,1376,737,948,736,1369,1373,1380,1375,1382,1383.
[2]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M]//陳文和.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360,397,383,349,369,343.
[3]錢大昕.潛研堂文集[M]//陳文和.嘉定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506.